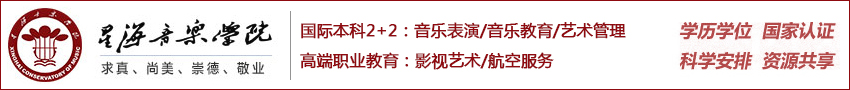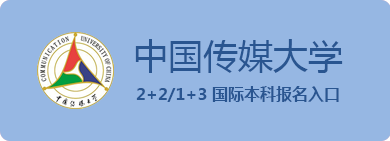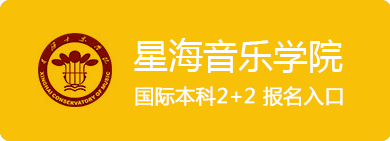音乐图像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刍议
【内容提要】音乐图像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型艺术文化学科,其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要靠科学发展观和科学的实践体系的有机结合。通过对该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简要的回顾总结与思考展望,深感今后必须加强外联构筑学科网络体系、内部挖潜完善学科教研体系、突出特色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初步设想与目标定位。希望学界同仁对此予以关注,共同开创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关 键 词】音乐学/图像学/艺术学/文化学
【作者简介】李荣有(1956~),男,杭州师范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音乐艺术学院教授。
一、学科形成与发展简况
音乐图像学(Musical Iconography)是由音乐学和图像学两个不同意义的现代学科结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从其字面意义看,就意味着要对以音乐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研究。而实质上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则必须和艺术本体之外的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密切的联系,吸收多学科知识的源泉,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方能完成本学科的预定计划任务,实现本学科的最终目的。如同西方其他诸多术语的产生,“图像研究”(Iconography)和“图像学”(Iconology)由希腊语组合而成,最初它仅仅用于研究古代纹章、图案与钱币考据,后来逐步扩展到对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题材艺术图像的文化学意义阐释研究等领域,并渐渐地形成了诸多新的交叉学科[1] (p. 196)①。
将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学科提出,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国家,最初只是零星的发表了一些论文,之后又相继涌现了一大批音乐图像学研究的论著,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体系。和音乐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一样,一些德语国家的学者率先作了诸多开拓性工作,发表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如德国学者G·金斯基(G. Kinsky)出版于1930年的《图片音乐史》[3],对于音乐图像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音乐图像学在艺术史研究的推动下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重要的著作有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4]、科马(Karl Micheal Komma)的《图片音乐史》[5]、F. 勒苏尔(Francois Lesure)的《音乐、美术与社会》[6],美国学者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术中的乐器及其象征意义》[7] 等。
1961年以来,由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音乐史中的图像》[8] 系列,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包容范围最广的音乐图像学著作。这套大型图片丛书分为民族音乐、远古音乐、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近现代四大系列,每一系列再分为10卷,每卷由一位学者编辑和撰写说明文字,全套丛书共40卷,为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图像资料,使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说这套丛书的每一卷都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特别可贵之处是它完全摆脱了西方过去此类著作以欧洲为主线的方法,把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到了同等的地位,非欧洲音乐史和传统与民间音乐的图片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各国学者对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这一时期以乐器为主题的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术中的乐器及其象征意义》[7],R. 查尔斯(R. Charles)的《油画中的乐器》[9] 等。温特尼茨的著作没有停留在对乐器本身的描绘和展示上,而是在乐器本体阐释的基础上,进而集中探索了音乐图像中乐器的象征性,特别是象征意义问题,从而使研究工作更具有文化史的深度。即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音乐图像学逐步把音乐图像扩大到整个艺术史、社会文化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和阐释,形成了具有系统学科理论和丰硕研究成果的学科发展氛围和学科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霍华德·梅尔(Howard Mayer)、琼·拉塞尔(Joan Lascelle)所著《音乐图像学》[10],则对音乐图像学研究成果文献进行收集、梳理和分类编目、著录,为国际音乐学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随着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确立和发展,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广大学者之间很快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在经过了有序的互动与酝酿之后,最终达成一种共识,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全面推动和繁荣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事业。1971年国际音乐图像学学会在瑞士正式成立[11],它标志着世界性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的诞生,而且在之后的国际间学术交流与传播、学术创新与发展等方面,确确实实起到了核心、调控与协调等多种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图像学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时间里,国际音乐图像学学会就成功地组织举办了8次国际会议[2] (第5页),标志着其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飞速发展。简况如下:
第一次:1986年6月9日——6月14日,由荷兰海牙市博物馆承办,主要议题是“在民俗学和非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音乐图像学的方法”。有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国家学者参会。
第二次:1988年5月举行,由意大利波伦亚大学赞助举办,主要议题是“视觉艺术中的北地中海民间音乐”,参会者多来自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葡萄牙、德国、美国等。
第三次:1990年5月举行,由希腊萨洛尼卡大学主持召开,主要议题为“古希腊艺术中的希腊音乐精神”,与会者主要来自法国、德国、希腊、瑞士、美国等。
第四次:1991年9月在乌兹别克举行,由乌兹别克作曲家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承办,主要议题为“中亚视觉艺术中的音乐”,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阿塞拜疆、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国家的学者。
第五次:1993年8月在德国海因里希·许茨纪念馆举行,主要议题为“形象与实在:对音乐的列队行进之描绘,1600~1775”,与会学者多来自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
第六次:1994年12月30日至1995年1月3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拉马特甘召开,由巴兰大学与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下设的音乐考古学会联合举办,主要议题为“音乐形象与圣经”,与会学者多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第七次:1995年6月在奥地利召开,由因斯布鲁克大学与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下属的舞蹈学会联合举办。主要议题为“在舞蹈图像里的形象与实在”,与会学者多来自亚美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德国、希腊、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日本、美国等。
第八次:1996年5月在西班牙巴里阿德大学举行,主要议题为“在大众节日与贵族节日的图像中的乐器,南欧,1500~1750”,与会学者来自奥地利、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2] (第6页)。
由上可见,最初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性例会,后由于多种需要改为一年一次,会议议题多以主办国周边区域内的音乐图像研究为主,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只有其中的一次参加了会议。
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促进音乐图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等的发展完善,加强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介绍与推广新的研究成果,探讨更为科学的分析、阐释的方法体系,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以及推进主办国该领域研究等方面贡献卓著。由于音乐图像学是一门多领域交叉的学科,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方学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由此也吸引了众多音乐学家、艺术史学家、文艺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博物馆管理者等参加了以上会议和研讨。
二、中国学界的探研历程
作为音乐图像学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明显迟于西方国家数十年时间,而中国学界对于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的历史,却可追溯到北宋年间的金石学兴起阶段(中国考古学的滥觞阶段),当时主要以遗存或出土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上的图像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我们权且把这一历史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早期发现阶段。北宋时期肇创的“金石学”,开启了专书著述的历史。所见较有代表性的有欧阳修成书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集古录》[12],赵明诚的《金石录》[13],开始直接记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地面上的画像石资料(参见[14],第17页),涉及内容虽然不多,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洪适的《隶释》[15]、《隶续》[15] 则记录了四川夹江杨宗阙、梓潼贾公阙等的画像(参见[14],第17页)。这一时期金石学发展较快,其研究方法有著录、摹写、考释、评述等方面。
最早集中出现音乐类画像的《金石学》著作,当属吕大临完成于元祐七年(1092年)的《考古图》[16],后又有《续考古图》[16] 共10卷,首次分门别类的收录了少量传世和出土的钟、磬、鎛、錞于等乐器画像,精心摹绘图形、铭文,记录尺寸、重量等,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杰作,并由此开启了汉画像及其他各类音乐图像收集与研究的历史。
除金石学家之外,一些科学家也对此有所关注。如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其成书于元祐年间(1086—1093)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并对古代编钟的形制与音响之间的关系作过探讨,发现“古编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补笔谈》)[17] (卷1)。之后又有王黼等人的《博古图》(1123年)[18],薛尚功《历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法贴》(1144年)[19] 两部金石学著作,收录古代乐器资料较多。
元、明时期,由于政治观念等的原因,学风渐变为恶实学,轻考证,金石之学难以为继,著述甚少,出现了一个冷落的时期。
清代,金石学又趋于繁盛,并形成了乾嘉时期的所谓“乾嘉学派”。当时据清宫所藏铜(乐)器“御纂”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合称《乾隆四鉴》[20]。乾嘉学派的兴起,为汉画像的发现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以至于武氏祠画像得以重见天日(1786年秋),发现者时任济宁运和同知的浙江人黄易,被誉为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参见[14],第18页)。
清光绪年间,汉画砖也相继被发现。公元1877年,在四川成都新繁县出土了八方画像砖,由此也开启了收集和研究汉画像砖的历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各种图像的收集整理工作,其搜集的范围也由地上扩大到地下墓室,大量不同品类、不同内容和风格的音乐图像资料得以相继问世,并受到广大学人的高度重视,鲁迅先生就曾多次托请各地学人,代为寻访拓印如游猎、卤簿、乐舞、宴飨等可见两汉风俗的石(砖)画像,目的是在国外发表,以扩大影响(参见[21],第30-31页)。
1935年10月10日,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南阳,我国首座专门展放汉画像石的“南阳汉画馆”落成典礼,为这些稀世珍宝安置了立身之所(参见[14],第30页)。故自吕氏《考古图》(1092)[16] 的问世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广大学人自发自愿地对进行图像资料的收集梳理,向世人初步介绍图像音乐文物的阶段,可称其为图像类音乐文物发现与研究的早期阶段。
2、科学开发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代历史文物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政府的计划之中,建立了各级、各类专门的文物考古与研究机构,使各类音乐文物的开发研究也逐步由无序变为有序,科学地发掘与考证研究工作稳步进行,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随着大量珍贵的墓葬图像音乐文物的出土,为古代音乐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数十年来,对于出土音乐图像学术价值的开发研究与利用,许多学者已投注了大量心力,并不失时机地将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如在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上、1981下)[22],吴钊、刘东升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略》(1983)[23] 等音乐史学论著中,均使用了大批出土古代乐舞艺术图像,作为一种有形的音乐史料,有效地改变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无形、无声的局限。
在资料的收集梳理与研究方面,中国音乐研究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及时地把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图像分门别类编辑成册,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间出版《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24] 九辑,其中除各类音乐图像外,还附有专论和说明文字。事实上,这些文字说明,亦属于图像学研究之专论。至80年代初,中国音乐研究所资料室已收藏图像2万余幅,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音乐图像的宝库。1985年,德国著名音乐图像学家维尔纳·巴赫曼先生访华,首次把西方音乐图像学的学科理论及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当他参观了中国音研所陈列室后,深有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是那么绚丽多彩,你们是巨人,我们欧洲只是侏儒。”(转引自[11],第8页)故此阶段堪称为中国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科学开发的阶段。
3、专题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极左思潮的清除,科研机构的迅速恢复和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国外各种学术思潮如音乐社会学、音乐民俗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民族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相继传入国内,为学术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观念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创建相关学科体系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在学科建设方面,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体系较早孕育成熟。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初设音乐考古专业硕士点,它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培养音乐考古专业高等专门人才的条件和能力,标志着这一学科的诞生。自1985年开始正规招生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硕士、博士等高级专门人才。1989年,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设音乐考古本科专业,后又招收硕士生,与此同时,西安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考古学的古乐器学课程以及招收研究生,从而形成了遥相呼应的犄角之势并逐步结成网络体系,使这一学科初步形成了阶梯式形态,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属性。之后又有部分学者零星地招收培养了音乐图像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武汉音乐学院2002年以来还为本科生开设了音乐图像学普修课程,使这种学科发展的氛围日趋浓烈,并为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成立于1990年的中国汉画学会(国家一级学会),是一个汇集了文博考古界、文化艺术界及自然科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学者,形成了图像学研究领域群英荟萃的庞大学术研究阵地,反映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与相互借鉴协作已成为一种时代学术精神的象征和发展趋势。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组织和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其突出优长是能更加及时、直接地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中,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进展,提升学术研究工作的价值,同时也从另一侧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理论的孕育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进展。
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汇聚到音乐图像学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途径和角度考据论证,著书立说,各类学术论著相继面世,如牛龙菲《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1981)[25],庄壮《敦煌石窟音乐》(1984)[26],牛龙菲《古乐发隐——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乐器考证新一版》(1985)[27],中央民族学院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6)[28],刘东升等编著《中国乐器图志》(1987)[29],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中国音乐史图鉴》(1988)[30],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1989)[31],《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1989)[32],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991)[33],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1991)[34],赵沨主编《中国乐器》(1991)[35],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中国乐器图鉴》(1992)[36],周到《汉画与戏曲文物》(1992)[37],黄翔鹏、王子初总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996-陆续出版)[38],董锡玖、刘峻骧《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1997)[39],应有勤《中国民族乐器图卷》(1997)[40],吴钊《追寻失去的音乐足迹——图说中国音乐史》(1999)[41],冯双白等《图说中国舞蹈史》(2001)[42],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2001)[14],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2002)[43],李丽芳、杨海涛《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像学的构架与审美阐释》(2002)[2] 等。这些学术专著的问世,为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奠定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由上可见,音乐图像学的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国家孕育诞生,但中国学者对音乐图像的学术性研究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北宋时期以来,历代都有音乐图像研究的经验积累和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音乐图像的藏量和质量均优于西方国家,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研究潜在着巨大的发展活力。
三、新起点与新的思路
随着学术观念的不断改变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音乐图像学研究已逐步成为中国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为弥补古代音乐史记载的严重不足,探究音乐文化艺术发生与发展规律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有幸的是,由于杭州师范学院在汉画艺术研究的不同侧面,如音乐学、美术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群体团队,并已圆满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个,推出批量学术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2003年度《艺术学》二级学科一举获得国家批准,艺术(音乐)图像研究作为学科第一专业方向开始招生,它标志着一个相对持久、稳定的综合性艺术教育与音乐图像学研究之路的开启,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目标和要求。在新的起点下,我们的初步想法如下:
1、加强外联,构筑学科网络体系。学科机制的建立,无异于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和空间。然而,如前所述,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一直处于潜学科地位,其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多属于部分学者个体性行为,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交叉学科,其学科的教研工作尚处在初始阶段,面临着构筑与完善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功能结构体系、教育教研体系、学术机制体系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又由于其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怎样准确地把握它的学科性质和意义,怎样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学科关系,怎样才能使其快速进入正确的发展轨道等,目前尚无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供借鉴,而这单靠我们一个学科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外联与合作,多渠道、多途径的吸纳与联合国内外高层次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以便于更加及时快捷地全面吸收利用先进的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和优秀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要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一个学术机制共建、学术资源共享的网络体系,使学科的发展具有前瞻性,计划性,避免盲目性。
据此,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国际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动态,纵向吸收与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音乐图像学学科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成果,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和近期发展的目标,具体可采取利用互联网广泛的收集各种信息,开展长短期学术性互动互访,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翻译引入国际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把它国它民族的优长和精华全面吸收利用到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中来。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学术界更加深入系统的互动与联合,横向借鉴周边相关学科的理念精华和优质成果,如采用人才的活性引进与聘任、学科共建、合作开展科研攻关、共同编写教材以及通过创办学术刊物等多种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学术研讨与学术推介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逐步实现学术资源与学术成果共享互为的现代学术机制,让不同地域、不同学科归属的广大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汇集到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的阵营之中,共同打造本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再者,从其表象上看,音乐图像学是由音乐学与图像学两个学科体系交叉融合而成的音乐理论学科,而由于音乐艺术是社会历史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不同文化艺术的体系之间又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所见的古代乐舞艺术图像中也多非孤立地表现音乐本体的内容,而是集中、精炼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概况和精神风貌,即使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各个艺术学科门类之间,这种与之俱来的固有关系依然十分密切,特别是对古代音乐文化的考证研究,若仅仅局限于目前划分的音乐学科内的知识范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鉴和利用相关文化艺术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方能获得该学科的生存价值和实际意义。故从其现代意义上讲,特别是在艺术学学科的框架之下,则进一步赋予了该学科更加广泛的文化含义。因此,就音乐图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既可以仍然把之归属于音乐学、音乐史学等学科的分支学科,又应根据其广袤的学理意义及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性文化场中的普遍意义,把之看成是一个新兴的横跨音乐学、美术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前沿人文艺术学科,只有这样突破原有学科框架理念的束缚,根据该学科全新的学理性质与意义,重新确定其适宜的发展目标,才能确立其正确的发展定位,才能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取得最为理想的学科发展效益。
2、内部挖潜,完善学科教研体系。由于音乐图像学研究不仅要对图像中音乐艺术表现的内容及细节进行音乐本体意义上的梳理研究,而且要对其图像或符号作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意义上的解读,这就需要从事该项研究的人必须学习和掌握以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音乐图像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人文艺术学科,特有的宗旨目的决定着其必须根据其实际需求重组其课程结构,以扩大学生的知识层面和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对艺术作宏观了解和整体把握的能力,使学生具备全面的艺术素质和从事综合性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基础条件。
从此意义上讲,以多学科、综合性为其主要特征的高师院校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学科基础,这应看成是一种天然的优势所在。因为较长时期以来,由于我国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一个本来完整完善的学科被切割成七零八落的块状或线条,学科与学科之间又逐步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小型堡垒,缺乏应有的互通与往来,从而造成了学科基础的薄弱和人才知识结构的单一贫乏。而高师院校具有学科齐全、人才集中的特点,各路人马很容易汇集于一体,拧成一股绳,就可形成一种强大的学术合力,攻克一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这也是目前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推动综合性学科的发展,提高综合性学术研究能力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目前情况来看,我校虽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交叉性质的学科基础骨架,但从学科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仅仅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起点,还有更加艰辛的路程和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我们去努力开拓。
首先必须进一步改变施教者的教育理念,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我校艺术(音乐)图像研究方向是置于艺术学学科框架之下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肌体之中,从其表象上似乎离开了音乐学的学科母体,甚至于有人戏称其是一种“大杂烩”、“无主体”,而实际上在这更具包容性的博大学术空间里,表面上展现的是多学科知识百川交汇的奇异壮观和魅力,而由于其研究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并没有因此而更张易辙,故最终仍将赋予音乐学本体研究更加深刻的哲理性和更加强劲的生命力。在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现场,不少人在谈论关于“厦大教育模式”问题,按照周畅教授的说法“厦大有着四面环海的自然优势,难道说还用到游泳池里去游泳吗?”(大意)即指厦门大学自1999年以来在音乐学研究生教育中,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自然优势,广开教路,集优组合,倡导“四环”教育理念,引导学生冲破原有学科的界限,到博大无垠的知识的海洋里吸取营养,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之所以被称之为“厦大模式”,就是因为厦大人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并率先跨出了单一学科门槛的一步,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丰收的喜悦。
因此,我们要通过学科理念、教育观念等的调整,根据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的现状,根据我校已有的学科基础、人力资源等条件,不断扩展研究的领域和层面,对教育与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进行调整,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在课程内容的总体安排上,可适当减少音乐学本体的课程与课时,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选开一些诸如艺术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古汉语、文献学、目录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艺术基础性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修养与学术视野,为升华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音乐图像学研究具有“强调对图像的观看、观察,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功能,激发人们更多的使用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以使人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可以不经过概念群的运转、至深而玄的思辨、绞尽脑汁的分析、判断等过程,而直接与信息源相合,用知觉去体察和领悟,从而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维,以启发人的灵性、灵感,有效地摆脱纯理论研究的枯燥和让人殚精竭虑的苦恼”[11] (第11页)等丰富多彩的古代遗留之乐舞图像资料,又具有直观、形象和优于其他文字信息的功能,通过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可以揭示许多典籍史料中语焉不详的细节,可以证史、补史,最终达到梳理全部乐史脉络的目的。”[11] (第10页)故我们既要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尝试运用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等现代科学原理,敢于直接、简单地认识和把握对象,敢于确立全新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又要严格固守遵循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规范,要充分重视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过程中每一步骤、每一环节的合理性,时刻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调适,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性、盲目性,逐步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学科教育与研究的秩序规范,在理论与实践的交织运转中,逐步完善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体系。
3、突出特色,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常言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它说明了对人实施全面的文化素质教育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也反映出建立与健全学科可持续发展体系的重要性意义。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从单一到多元,各学科门类之间既有其个性特点又有其共性特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当今国际学界把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借鉴与交融提到很高的位置,并已经对世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明较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学科分立的极限状态已经或正在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多学科之间的交融交汇亦将成为未来学校高等教育及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点。从学科发展的层面上讲,音乐图像学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新兴学科,自然有其独特的学理性质和社会学、文化学意义,特别是置于综合性院校的艺术学学科宏观构架之中,在学科的结构关系上则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厚重感,在人力、物力和设备等教育资源的配备上也有着很大的优越性,在音乐图像的学术研究方面则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地吸收借鉴相关文化艺术学科的经验、方法和成果,应该说,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特色,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极好条件。
从其学理性质上看,音乐图像研究讲求实证,是一种对遗存各种有关音乐图像(含绘画、雕塑、文字符号等)中的内容、形式、题材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专门学问,通过这些手段达到认识、了解、恢复古代音乐活动的具体状态,使现代人对古代音乐的认识超越文字描述的不足等目的。如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会长蒂尔曼·塞巴斯(Tilman Sebass)先生所言:“音乐图像研究(Musical Iconography)意味着对以音乐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研究。音乐图像研究是研究音乐的,但是,是研究图像中的音乐现象,或者更广义地说,是研究与视觉证据有关的音乐现象,这就不同于其他的研究资料,例如,录音音乐、记谱音乐、译谱、乐器、收藏或文字记载。音乐图像学致力于研究音乐的图像资料,任何使音乐具象或抽象的视觉化的图像资料,从最具象的照片直到抽象和象征艺术都是音乐图像研究者感兴趣的对象。它所涉及的媒介包括绘画、雕塑、照片或者任何其他诸如此类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能够反映出艺术家对音乐的认识,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1] (p. 196)② 总而言之,音乐图像学试图对人类遗存的各种音乐图像或符号做音乐文化学意义、社会学意义和人类学等意义上的综合性解读与阐释,并为相关艺术文化学科的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和参考依据。
由上可见,从其学理意义上讲,音乐图像学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现代前沿学科,而从学科的属性上讲,它又是一个可以挂靠于许多传统学科名下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的分布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刚刚起步,处在具有勃勃生机的发展阶段,也正由于它所具有的这种多元的品性特征,才使得这一学科具有更加强劲的发展潜力。再从我校的基本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基础,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同时我校学科齐全,人才集中,便于调控,极易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加之作为后来者,我们有条件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优长和精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使学科的发展逐步走向良性循环。
然而,如前所述,一个学科教育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靠长期持续的实践磨砺与积累总结,方能逐步走向一条必然的发展之路。那么,我们目前要努力去做的,一是要继续保持和扩大已有的良好基础和成果,稳步有序地开展正常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二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理论、管理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深层研究,建立与健全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信息管理、学科管理、学术规范、学科发展等的长效管理机制。再就是要继续依托汉画艺术多层面、全方位研究的特色优势,与时俱进,继续攻关,努力打造人才工程、品牌工程。总之,要充分重视学科发展过程中每一步骤、每一环节的合理性,时刻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调适,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性、盲目性发展状态,逐步建立起新的学科秩序、学科目标和学术规范,一旦完成了这一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音乐图像学学科可持续发展之路就会更加宽阔通畅。
注释:
①②转引自[2],第2页。
【参考文献】
[1]Seebass, Tilman. Imago Musica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Musical iconography vol. ix/xii. Libreria Musicaie IyaIiana, 1992-1995.
[2]李丽芳、杨海涛. 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像学得构架与审美阐释[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Kinsky, G. . History of Music in Pictures [M].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30.
[4]Panofsky, Erwin. Studies in Iconology [M]. London: Oxford, 1939.
[5]Komma, Karl Micheal.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 [M]. Stuttgart: Alfred Kroner, 1961.
[6]Lesure, Francois. Musik und Gesellschaft im Bild [M]. Cassel: Barenreiter, 1966.
[7]Winternitz, Emanuel.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their Symbolism in Western Art [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8]Bachmann, Werner.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M]. VEB Deutscher Verlag fur Musik Leipzig, 1961—1984.
[9]Charles, Sydney R. and David Boyden. Musical Instruments in Paintings [M]. mimeographe Berkeley, Calif, 1961.
[10]Mayer, Howard and Joan Lascelle. Musical Iconography[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2.
[11]刘东升. 杨荫浏与音乐图像研究[J]. 北京:中国音乐学,2000,(1):5-15.
[12][宋]欧阳修. 集古录[M]. 石刻史料新编(第24册)[M]. 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13](宋)赵明诚编撰金石录(一函八册)(嘉业堂丛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82.
[14]李荣有. 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15](宋)洪适. 隶释、隶续(古代字书辑刊)[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16](宋)吕大临,赵九成(撰). 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胡道静. 补笔谈·卷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宋]王黼. 博古图[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19][宋]薛尚功.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1144).
[20]刘雨. 乾隆四鉴综理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王建中. 汉代画像石通论[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22]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上);1981(下).
[23]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24]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M](9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4-1964.
[25]牛龙菲.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6]庄壮.敦煌石窟音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27]牛龙菲.古乐发隐——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乐器考证(新一版)[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8]中央民族学院(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6.
[29]刘东升等.中国乐器图志[M].北京:轻音乐出版社,1987.
[30]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中国音乐史图鉴[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31]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2]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33]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4]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M].敦煌出版社,1991.
[35]赵沨(主编).中国乐器[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1.
[36]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中国乐器图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37]周到.汉画与戏曲文物[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8]黄翔鹏,王子初(总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陆续出版).
[39]董锡玖,刘峻骧.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40]应有勤.中国民族乐器图卷[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41]吴钊.追寻失去的音乐足迹——图说中国音乐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42]冯双白等.图说中国舞蹈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43]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