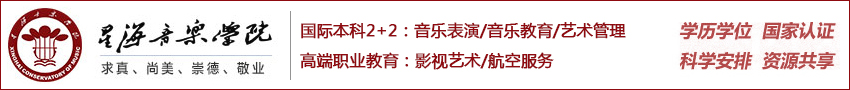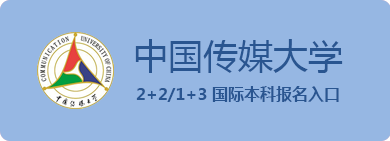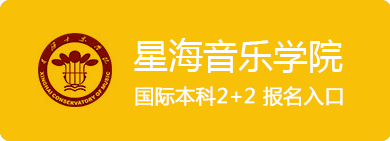音乐的“现代性”转型
——“现代性”在20世纪前期中西音乐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反思
【内容提要】文章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参照20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中国音乐在20世纪前期的现代性转型进行了思辨性的考察,并对这种转型的历史意义和深层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总结。作者认为,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是出于回应外力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音乐的影响)而产生的突变性转折,从中催生了现代音乐艺术的理念形成、西方音乐的大面积引入以及音乐中的民族性意识兴起等重要后果,并对后来的中国音乐的实践运作与意识构成和产生了重大的深远影响。
【关 键 词】现代性/音乐文化研究/中国音乐/西方音乐/中西音乐比较/20世纪音乐
【作者简介】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副院长(上海 200031);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为E—研究院依托高校。
一、问题设置:“现代性”概念与音乐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文化思想界出现所谓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① 国内也从90年代开始用“后现代”的眼光和角度审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② 然而,提出所谓“后现代”概念,必然涉及对“现代”概念的重新认识。因此,“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日益成为知识、文化界在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关注焦点。③ 音乐界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了有关“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热烈争论。④ 尽管这场争论的肇始和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理路,但也与这一阶段中知识界、文化界关注“现代性”的整体思想氛围有内在关联。
所谓“现代性”问题,即对“现代现象”的本质诘问。“现代”一词,在此不仅是时间年代上的阶段描述概念,而且更是一种与“古代”形成对比的性质划分术语。根据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的观点,⑤“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改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思想、意识形态、艺术风格)的结构转变。而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比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于是,“现代性”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外在形态的变革,而且更是文化、艺术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意识的转变,是人的心灵、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结构的转变。正所谓现代性的转型“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⑥
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我们对20世纪中西音乐的考察也许会获得完全不同的视角。因为音乐文化属于人的精神体验表现和心态结构范畴,所以,现代性的转型不仅必然反映到音乐中来,而且也驱使音乐与其他人文艺术活动驶入同一条轨道。可以认为,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和裂变在20世纪前期表现得极其剧烈。本文拟从宏观角度集中讨论20世纪前期的音乐现代性转型问题,其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这个时间段中,世界范围内兴起所谓现代主义(modernism),领域不仅涉及艺术、文化等精神领域,而且也涉及诸如科学、政治和社会等方面。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可被看作是“现代性”表达的突出体现,显示了“现代人”在观察世界和认识自我时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转折。如绘画中抛弃具象写实而走向抽象表现的“立体主义”;物理学中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从而彻底改变人类思考时空关系的重大突破;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功能的革命性论断,等等。其二,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在这一时段中表现得较为集中。可以说,音乐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经历了整个音乐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其意义之深远和阵痛之剧烈都远远超过了以往音乐史中其他时段的风格转折(仅以西方音乐而论,如17世纪初的“巴罗克的诞生”,18世纪中下叶古典风格的成型,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兴起等等,这些风格转变所产生的震荡都不如20世纪前期的“现代音乐”的冲击来得强烈)。因此,以这段时间为观察焦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在现代性转型的整体进程中,音乐文化和音乐艺术的基本构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其三,在这一时段中,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质和面貌,但同时仍具有内在的学理关联。如果说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是出于西方整体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已进入近现代(按:在西文中,近代和现代为同一词汇:modern)的一种逻辑继续和渐进转变,则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更多是出于回应外力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音乐的影响)而产生的突变性转折。因此,与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相比,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显得更为紧张、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这一阶段中西音乐彼此的现代性转型的内涵和性质,实际上就抓住了整个音乐现代性转型的根本关键,从而有助于我们通过认识这个音乐文化中的重大问题,对我们今后的音乐文化的具体实践和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二、西方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音乐的现代性转型,不妨先从西方的“现代音乐”着手进行思考。从时间的顺序来看,西方现代音乐在20世纪前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两个明显有别的阶段。这在音乐学界已经构成一般共识。⑦ 下面通过思辨性的历史梳理,阐述笔者个人对这两个时段中西方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基本看法。
“世纪末”转折至一次大战,可以被称为西方音乐“现代性”转型的萌发期。此时,欧洲处于“世纪末”的焦灼和混乱之中,传统的观念和标准风雨飘摇,文艺思潮空前活跃。音乐在经历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冲刷后,正在发生深刻的裂变。统治西方音乐近三百年的传统建构(不仅包括调性语言这样的具体技术手段,而且也包括体裁惯例、社会建制等一系列更为隐蔽的支撑系统)开始土崩瓦解,德奥音乐的支配地位趋于丧失。至一次大战爆发之前,音乐世界呈现出风格剧烈动荡的局面:传统的审美理念仍然“死而不僵”,但新潮的音响和技法已在形成。后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原始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各种音乐流派和音乐思潮层出不穷,相互重叠。作曲家们依据各自对传统和未来的理解,在创作中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和技法。在这其中,马勒和德彪西这两位与旧时代仍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代表性人物,通过对人类在进入现代性社会时的心态境遇的出色音响刻画,成为最有意义的音乐上的现代性导师。而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等音乐上真正的现代性代表,此时正在发育和成长,也已经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
西方音乐“现代性”转型的第二阶段是两次大战之间,此时音乐上的“现代性”转型基本完成。这其中的内涵是,一方面巩固现代性的分化和创新原则,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审美原则的扬弃和整合。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音乐状况比世纪之交的情形显得较为稳健,可被称作是西方现代音乐的“古典期”。此时,浪漫主义对音乐的美学规定遭到全面抵制,传统的调性语言被大多数作曲家所抛弃,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运动成为这一时段在音乐上的突出事件。世纪初在音乐上的全面探索和激进试验此时让位于较为稳定、成熟的音乐语言建构。尽管此时并没有出现所有人都认可的统一风格和技法体系,但几乎所有重要的作曲家都倾向于有节制的、理智不惑的、着重音乐本体意义的表述方式。“回到巴赫”是当时一句著名的口号;有意识地回归古典、前古典乃至巴罗克的传统体裁和样式;“纯音乐”的理想以压倒优势支配创作的方向;“自由无调性”受到十二音技法的控制和规范,以符合音乐对逻辑和结构力的要求。大胆的实验和激进的突破仍时有所闻,但总的说来处于边缘地位。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和巴托克作为20世纪音乐最重要的经典大师,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但都取得了很高艺术成就的创作道路。
上述有关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现代性转型的轨迹表明,无论语言体制、思想意蕴,还是社会功能、价值诉求等各个方面,这时的音乐都体现出与以往相当不同的“现代性”特点。⑧ 更为重要的是,某些现代性特点在整个20世纪持续贯穿,至今未衰。进而,我们可以从20世纪西方音乐的总体进展中抽象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音乐现代性范畴。
其一,专业艺术音乐的创作从所谓“共性写作”完全转向“个性写作”。这个过程是19世纪以来音乐艺术追求个性风格发展的逻辑结果,但在20世纪则以更加极端和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1908年勋伯格抛弃调性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象征事件)。作曲家以完全不同的写作手段和技术语言表达对世界、人生的态度和看法,音乐在20世纪上半叶和随后所经历的观念创新和语言更迭,其程度之烈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音乐表现的疆域被推进到所能想象的极限。
其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在20世纪的不断成熟,音乐的品种开始明确分化为彼此有别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大种类:艺术音乐、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每个种类均存在自身的危机和问题,同时又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条件再细分为各种亚种(如爵士音乐,原来属于流行音乐品种,目前被认为介于艺术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几乎成为单列分开的一个特殊品种)。艺术音乐以专业作曲家的创作为中心,着力于具有深刻人文思想内涵和严肃审美意趣的开掘,在音乐表现上讲究创新意识和个性追求。但其严重的危机在于,其明确的社会功能趋于减弱,对社会的文化影响力趋于衰微。另一方面,听众与新创作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趣味趋向保守,由此造成日常音乐生活中传统的保留曲(剧)目占据支配地位。民间音乐在历史上源远流长,扎根于现代工业化文明影响之前的本地民族土壤,是人民大众世世代代通过口传心授凝结的集体创作,具有鲜明、浓烈的地方特色,但随着现代社会“全球化经济与文化”的到来,民间音乐的本土性快速丧失,宝贵的人文基因资源遭到威胁。流行音乐则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贴近世俗的日常生活,表现浅显的生命感叹,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和商业运作,在20世纪中得到高速发展,其影响力不可忽视。应该指出,流行音乐属于通俗的“快餐文化”,不免鱼龙混杂、良莠并存,其中虽然存在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纯商业化因素、以麻痹神经为目的的欺骗性成分和以宣泄感性本能为目的的破坏性倾向,但也有很多追求美好心愿和社会批判的积极因子,需要进行认真的鉴别。
其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开始对音乐产生影响,其作用在20世纪前半已经显露,但在20世纪后半达至高潮。音乐受惠于科技进步最直接的方面是音乐传播方式的变化和进步。广播的普及以及电视的发展,使音乐的传播真正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录音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录音工业的不断壮大,更使音乐的储存、传播和接受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从19世纪末第一次进行音乐录音,到1925年78转唱片问世;从1948年33转密纹慢转唱片公开发行,到1958年出现立体声;从1979年数字录音技术发明,到1983年激光唱片(CD)面世——唱片录音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都对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至此,音乐的音响本体彻底摆脱了“转瞬即逝”的命运,成为可以永久保存的产品。音乐生活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必须指出,上述的三个音乐上的现代性特征范畴,并非仅仅发生在西方国家,而是带有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因而是音乐现代性转型的总体表征。中国当然也不在例外。但是,这种带有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中国音乐生活中,已经是20世纪最后20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的事情了。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发生,我们必须再次将眼光移回至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期。
三、“现代性”转型视角下的中国音乐:20世纪初的历史轨迹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在20世纪的发展轨迹,由于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现代性”的转型上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与西方音乐同时代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不可比性。例如有极端意见说,与(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成就相比,20世纪前期的中国音乐在探讨音乐的现代性上“交了白卷”——主要原因是没有吸收西方同时代音乐的语言技法和思想内涵,因而在创作意念上与世界乐坛的潮流方向脱节。⑨ 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因为“现代性”的转型问题不仅表现在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中(在这方面,应该承认,20世纪初的中国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确实没有达到按照世界水平衡量的现代艺术的美学标准),而且更表现在艺术体制、社会功能和审美思想的整体性转型中。
在本节中,笔者将应用现代性转型的理论视角,对中国音乐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进程进行一次思辨性的梳理和阐述。
在中国的本土音乐文化中,整个20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单位,是中国音乐的“前现代”时段。⑩ 与此相应,自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中国音乐出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巨变,几乎是骤然被抛入“现代性”转型的阵痛之中。20世纪之前,虽然中国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演进和变化,但在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以一贯之的稳态结构。仅以音乐的类型划分而论,中国古代的传统音乐可以分为四个迥然有别但又相互联系的层次结构。(11) 其一,位于“官方”正统中心地位的政治性礼仪“雅乐”,受到历代皇宫高度重视,享有进入正史“乐志”的荣耀,但对宫廷之外的日常音乐生活影响甚微;其二,出于民间、溶于民俗、流传于广大民众之间的所谓“俗乐”(又可分为民歌、器乐、戏曲、曲艺、歌舞等几个重要的亚种),虽出身卑微,但鲜活灵动,与中国各地人民的语音语调、性格气质和风土人情密不可分;其三,与中国特有的“士大夫”现象具有不解之缘的“文人音乐”——以“琴乐”为标志性代表,讲究“中正平和”的情趣,追求“静远淡虚”的境界,精神内涵带有高度个人化的倾向;其四,与宗教目的密不可分、为礼拜仪式提供支撑的“圣乐”。根据宗教类型的不同,主要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和基督教音乐、伊斯兰教音乐等。由于中国社会的世俗性特征,宗教音乐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上述四种音乐类型结构之间,虽彼此之间产生过很多交流和影响,但在20世纪之前,文化上的不同功能划分和角色分担得到一贯维持。雅乐直接对应于宫廷政治的实用需要,俗乐对应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和娱乐实践,而琴乐则是文人墨客抒发个人情怀的有效通道,圣乐服务于各自宗教内部的礼仪崇拜程序。
上述音乐类型及其文化功能的稳态结构由于适应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前现代”性质,因而直至19世纪中下叶,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怀疑和冲击。但是,随着19世纪末中国因遭受西方列强的扩张和侵略而产生了越来越明确的维新改革意识,很多有识之士出于唤起民众、“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激情,开始投身于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音乐)的变革之中。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由此启动,并一发不可收。笔者不可能(也不需要)详细叙述这次转型的整个经过,在此仅想就该转型过程中的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和现象进行观察和阐述。
一般公认,20世纪初所谓的“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20世纪音乐的发展具有启蒙意义。这是一种特为当时的新式学堂所开设的音乐课而编创的简单歌谣,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得到很大发展,数量众多,获得了中国社会(主要在学校教育中)的广泛认同,并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建构中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文献从各个角度研究学堂乐歌的内涵和特征,(12) 但从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角度看,我们仍能从学堂乐歌这个特殊现象中读解出一些新的含义。笔者以为,学堂乐歌是中国音乐走向“现代性”的第一个预示性标志,尽管这种简单歌谣并不具备高深的艺术奢望和明确的审美主张。首先,学堂乐歌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上第一次使音乐成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并借此形成民族精神认同的有力工具,它所担当的文化功能和社会角色对于中国音乐而言可谓前所未有,因而它与中国古代音乐的所有类型在性质上都迥然有别。简言之,通过学堂乐歌,中国的音乐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在精神载体上的具体显现。(13) 而这一点将对中国音乐在以后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为了完成上述功能,学堂乐歌的作者们在词曲编创上以普适性和大众性为第一要义,力求做到歌词简明如话,曲调朗朗上口,乐句方正划一,节奏简单整齐,曲体简单易记,以利学生和大众学唱和传唱。显然,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的传统音乐中很少能找到符合上述要求的因素,因而尽管有一些学堂乐歌采用原有中国民歌进行改编,但绝大多数的学堂乐歌是借用西方(以及少量日本)具有明确大小调音阶结构的通俗歌调进行填词处理。由此,形成了音乐上的一个重要后继效应,相信当时的学堂乐歌作者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中国民众的音乐听觉接受意识由此被西方元素所浸染,这在客观上为大范围地接受西方音乐打下了潜在基础。西方音乐实际上很早就被引入中国(明确的史料可以追溯至16世纪晚期的明末),(14) 但为何直到20世纪西方音乐才产生了大面积的影响,上述解释也许可以提供一个特殊的角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皇权政治体制,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在政治层面上正式启动。紧接着出现了以“五四”为象征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即文化、思想和精神领域的“现代性”转型:其重要标志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西方文化思想的大范围涌入以及文学创作(特别是在小说和新诗领域)的全新成果,(15)“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成为此时中国的“时代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国的音乐文化回应着时代的大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动下,中国音乐的现代性社会空间逐步产生并进一步展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时任教育总长为蔡元培先生)在中小学的学制中将音乐明确列入正式课程之后,“官办”的音乐教育建制在中国大中城市普遍得以建立。通过普通学校教育,使音乐成为广大受教育阶层的日常活动之一,并由此带动准专业性质的音乐教育和活动的进一步展开,这为日后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铺设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其二,自“五四”以后,中国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和杭州等大城市)中,萌发了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生活,这包括组织成立各类音乐社团(有的偏重中国传统音乐的发扬,有的偏重西方音乐的引介),创办发行各类音乐期刊(和上述音乐社团的活动有密切关联),以及举行各类专业性和普及型的音乐会,等等。(16) 通过教育体制的革新和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搭建,音乐在中国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城市文化品种的地位开始萌发生根。(17)
正是在上述大潮中,1927年11月,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音乐艺术高等教育的专门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18) 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事实称为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奠基性事件和标志性路碑。当然,这是一种站在当下的远程视角回顾过去所给出的历史意义判断,或许这仅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尚没有在中国音乐界内达成共识。笔者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国立音乐院的创建绝非突如其来,它建筑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30余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和音乐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基础之上,因此,它顺应了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这种转型的必然结晶。第二,这一事件说明,音乐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自我身份的艺术品种和社会分工职业,在中国终于立稳脚跟,而且得到了官方政府的支持和知识/教育界的认同。创立音乐学院,专事培养专门的音乐艺术高级人才,出现这种社会行为的前提是,对待音乐的态度和意识已经具有现代性。第三,事后证明,这所学院确实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办学历程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音乐学府(后演变为上海国立音专和上海音乐学院,共近80年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所学府成为了中国现代音乐史发展的推动“母机”,不仅培养了最早几代中国现代音乐各方面的栋梁之材,而且对之后建立的其他中国音乐高等教育院校和系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四,虽然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音乐遭遇各种非常的外部条件的影响(包括战乱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但通过这所学府(以及其他音乐院校和艺术机构)的体制性支撑和保护,音乐的艺术品格和审美机理仍然得到维持和发扬。这不仅包括持续深入地引入西方艺术音乐的成就和训练,而且也包括对中国本土的传统音乐进行认真而科学的整理和吸收,以期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国现代音乐文化——而这是所有中国现代音乐家的至高理想。
由此,在社会建制、民众意识和学院建构等各方力量的合作推动下,自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中国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家”个人为创作主体的音乐创作理念,并获得了相当的创作成果。萧友梅、赵元任、黄自、黎锦晖、刘天华、青主、贺绿汀、聂耳、冼星海等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创作成就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一个前所未有的作品谱面文本的“作曲”(作为艺术创作)概念,独立于创作者并具有后续生命的“作品”(作为艺术产品)概念,在写作中将个人特征置入其中、并依靠作曲获取社会职业的“作曲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行当)概念,以及一个连续不断并超越个人的“创作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的历史积淀)概念——这样的概念意识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音乐中是不存在的,因而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意味。尽管作曲家这一艺术职业在中国的萌生与成长确乎是受到了西方艺术音乐输入的强烈影响,但必须看到,作曲家在中国社会中的定位,以及中国社会对作曲家所提出的要求,又显然不同于西方音乐中的情形(不论是与完成现代性转型之前的19世纪相比,还是与处在现代性转型之中的20世纪相比)。由于处在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特殊环境中,中国作曲家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从诞生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尖锐的悖谬矛盾,直至今日,这个矛盾依然是纠缠中国作曲家的关键问题:作曲作为一种职业化的艺术,其基础和技巧均来自西方,但如果中国作曲家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就必须摆脱这种“西方胎记”,在创作中凸现自己的中国身份与中国性格。于是,“中西矛盾”就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中的一条贯穿性“主导动机”,至今余音不散。(应该指出,在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发展中,中西矛盾的尖锐性表现得比在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美术中更为突出。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文学和中国美术的悠远传统中,已经具有坚实的个人创造的艺术基础,因而现代性转型的阵痛并不像在音乐中显得那样强烈。)
由上述可见,至30年代,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基本架构已经初见端倪。但这一历史进程随着30年代末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部分中断。正如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进程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打断一样。我们看到,不论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在20世纪前期确乎都经历了一次非常彻底的现代性转型,但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出于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非常特殊的具体内涵。
四、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后果及其反思
上一节从现代性转型的角度对中国音乐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思辨性的梳理。下面就上述历史现象中体现出来的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后果作进一步的理论反思和更加偏重“长时段”性质的总结。
其一,在20世纪前期,通过中国社会整体上的现代性转型,音乐作为一种独立艺术门类的地位和品格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确立。应该说,这是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最重要的成果。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作为政治性的传统“礼乐”范畴(主要体现为宫廷雅乐),还是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手段(“琴棋书画”之一),或是作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作为宗教礼拜的辅助因素,音乐作为一个精神因子和艺术门类,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被分化出来,基本处于依存地位,只具有附庸的品格。但随着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带动,随着音乐现代性空间的产生(以现代意义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教育体制的建立为代表)和音乐职业人(以职业作曲家为代表)的活动开展,音乐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分工活动的艺术行当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虽然,音乐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承担和社会角色在日后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仍然受到各种外在的影响(特别是在非常的政治条件下,受到极左意识形态的各种挤压),但其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地位和品格,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公认。这种大的趋势至少就目前来看,是不可逆转的。
其二,从20世纪初至今,西方音乐通过现代性转型的带动大面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和性格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这种影响显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意义。其积极的意义在于,西方音乐的引入对中国音乐而言,成为一种可以比照的、有别于中国本土音乐的对象客体,从而激发起中国音乐的自觉意识,使中国音乐产生了“突变”的内驱力,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进程。甚至可以说,西方音乐被置入中国音乐的文化语境中,这本身就是中国音乐产生现代性“裂变”在文化上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中国人的音乐意识由此产生重大转折,中国的音乐也由此开始步入全球性的运行轨道。从负面的角度看,由于西方音乐这样一个“他者”的闯入,造成中国音乐内部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导致中国音乐产生了与自身历史之间的断裂,价值体系的混乱和文化结构的震荡。这其中所产生的紧张至今尚未得到圆满解决。(19)
其三,音乐中的民族性意识作为“现代性”意识的一个方面,自20世纪初以后,成为推动中国音乐发展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推动力,其生命力至今未衰。民族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萌发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达到高潮的典型的现代性意识建构,(20) 它不仅极大地影响着现代性条件下的政治运作和社会构成,而且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文化身份建构与群体精神认同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西方,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工具,自19世纪开始就成为显现民族精神、构建民族认同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所谓“民族乐派”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1) 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民族性意识在音乐上的表露不仅非常强烈,而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作曲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非常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尝试各种手法营造音乐中的“中国性”,尽管成功的程度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并不均匀,但确实可以从中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而且是越来越明显的主导线索。几乎所有的20世纪中国音乐新作品都可以从追求“中国性”这一角度求得理解。(22) 换言之,理解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其中一个最有效的角度,就是观察中国作曲家如何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用音乐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中国。
* * *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中,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确实已在20世纪前期发生,而其后继影响是极其深远和极为深刻的。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全然不同,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的外在表象和内在含义均有相当的区别和差异。本文的重点是参照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进程,观察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的特点和意义,从中所凸现的一个明确结论是,现代性转型是一个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仍然具有自由意志改变这一进程的后果和性质。由于西方国家较早完成现代性转型,因而后继的国家民族不可否认会受到西方的影响。然而,正如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所显示的那样,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均有不同,这种现代性转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盘的“西方化”,而是在全新的条件下和语境中寻找一种并不丧失原有自我身份的新的方向定位。当然,这种转型往往充满了矛盾和难题,并伴随着不测和阵痛。但学者的责任也许就是,通过对矛盾和难题的剖析和理解,帮助我们在行动中查清不测,在实践中减轻阵痛。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所在。
注释:
①参见[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②参见易丹的“失败者的话语狂欢”(载《读书》,2001年第7期,第100~106页)中对中国文化界引进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③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④有关的讨论焦点问题请参见宋瑾:《音乐的“中西”关系讨论再度升温——“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人民音乐》,1999年第1期,第30~33页。
⑤关于舍勒对现代性问题的整体综述,参见刘小枫上引书,第15~20页。
⑥同③,第19页。
⑦参见Robert P. Morgan, Twenteith-Century Music, New York: Norton, 1991。也请参见[美]彼得·斯·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上、下),孟宪福中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1986。
⑧有关针对西方20世纪现代音乐的概括性描述和总结,请参见笔者为《十大音乐家——二十世纪世界名人丛书》(杨燕迪主编)所作的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18页。
⑨见李欧梵:《音乐语言的“反讽”和“反抗”》,载《音乐的遐思》,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第19页。另参见台湾作曲家许常惠先生对黄自先生没能将西方现代音乐的技术和语言及时引入中国的批评,转引自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台北:耀文事业有限公司,1998,第174~175页。
⑩目前的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布局也清楚地反映出这个事实。一般而言,“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科对象是自远古至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音乐,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更多涉及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发展(其中又有“中国当代音乐研究”涉及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音乐)。
(11)参见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特别是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
(12)权威著述为钱仁康先生的新著,《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13)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梁启超曾明确写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饮冰室诗话》第77节,载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第8页)。而李叔同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也是学堂乐歌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这样重量级的近代文化巨匠们直接参与学堂乐歌运动,这本身就说明了学堂乐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14)参见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5)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特别是第3~12页。
(16)据不完全统计,诸如钢琴家戈多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小提琴大师海菲茨(Jascha Heifetz)、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等世界乐坛的著名人物早在20年代就来过中国演出。见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二次修订版),第87~88页。
(17)参见汪毓和上引书,特别是第四章“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初期建设”(上);另参见夏滟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特别是第三章“‘五四’精神影响下的新兴音乐文化”。
(18)第一任院长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蔡元培先生,第二任院长为萧友梅先生,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享有崇高威望。这两任院长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分量具有内在的象征意义,特别从现代性转型的角度看,促人深思。
(19)参见韩锺恩:《何以驱动,并之所以断代——通过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逻辑》,载《音乐美学与历史》,洪叶文化公司,2003,第187~230页。该长文对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中所显露出来的“多重传统文化言路的中断”进行了思辨性的梳理。
(20)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1)参见Richard Taruskin, " Nationalism" , Grove Music Online(《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第七版),ed. L. Macy, 〈http: //www. grovemusic. com〉。
(22)有关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在各个体裁中的成果和成就,请参见汪毓和、陈聆群主编:《回首百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4。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