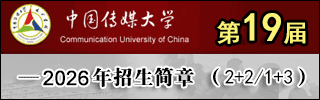直到今天,在陕西渭南韩城秧歌中还有“献饭”的民俗,通常在祭祀中表演。表演形式类似云南彝族的 “跳菜”,表演内容根据主人对故人的祭奠而定,有 “女儿献饭” “儿子献饭”“老婆献饭” “老汉献饭”等。2012年,民间艺人姚林山 (1932年出生)还表演过献饭的各种花式,动作由简至繁,从一个碗到九个碗,翻转托盘,再从平地到凳子上表演。类似民间舞的 “社会功能及专业性质”基本属于民俗学范畴,已然不需要置身艺术学范畴的职业民间舞者所 “扩展”。“上帝的事归上帝做,凯撒的事归凯撒做”,当民间舞华丽转身为舞台艺术时,民俗的 “献饭”及其技术显然不能 “重构一种带有典范意义的民间舞”;此外,这种 “宏观的民间舞”有已经具备了赖以支撑的 “绝活”———元素化教学 (“元素训练”),这是从事新型民间舞专业 “舞体”的立身之本,是由 “背景”而成为 “前景”的桥梁。
章节一
在当代中国民间舞的发展中,北京舞蹈学院领衔操作的 “元素化教学”是一个有预示性震颤的关键词,它关系到中国民间舞的一种新的机体产生、新的过程干预、新的资源分配、新的技术构成和新的效果显现。所谓其 “新”,从文化空间上讲,就是渐离乡土“民俗”、渐近艺术 “舞台”:“以许淑鮬、陈春绿、潘志涛、邱友仁、王立章、贾美娜为代表的一代专业民间舞教育者 们 将 ‘元素教学' 引 入了课堂,以’厚积薄发‘的理念,对原始性的民间舞教材进行 ’革命性‘的整理:从纯民间的风格、动态中提取了大量可以单独使用的大量素材,使其 ’元素化‘成为遣词、造句的语素。很显然,这个过程必然造就一个不同以往的结果,’民间舞‘被 ’肢解‘了,但民间舞的功能却被扩大了,虽然它看上去似乎离 ’民俗‘远了些,然而却离 ’舞台‘更近了。这是民众的意愿,时代的需求,民间舞的演变已成 ’大势所趋‘,绝非凭空臆造之事。”[1]
如此,职业民间舞者以理念为先展开了自己的实践。阿瑟·布鲁克斯以为,“理念决定现实”。虽然口头上总是挂着 “实践”二字,但从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来讲,职业民间舞身份群体从脱胎之时起,其实践活动都是基于理念的,这一理念优先原则潜在地伴随着其成长。
章节二
“民俗”是什么?民俗蕴含着自远古以来社会风俗的丰富文化信息,并保留了人类文明的记忆。不仅如此,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环境还会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是所谓“十里不同俗”。美国生态学家约瑟夫·格林内尔 1917年提出 “生态位”的重要概念,英国生态学家埃尔顿进一步把生态位看成是: “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作用”,[2](P103)强调物种与物种之间的营养关系即功能关系。民俗生成所依赖的资源关系即是民俗在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序位——— “简而言之,民俗的资源生态位表现的是民俗的生成与演化需要怎样的条件和背景。”
[3](P333)这些条件和背景产生了民间舞的观念、仪式和形式。就中国民俗而言,仅是汉族,节令观1观念、伦理观念、吉祥观念以及其中隐藏的神灵崇拜、祭祀祖先、求吉纳祥、辟邪禳灾、生殖繁衍等文化信息是民俗的 “核心价值观”,并且固化在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仪式当中。在形式上,春节有贴春联、挂年画、做面花、剪窗花等,用以消灾避邪、迎新纳福;元宵节有舞龙、舞狮、打太平鼓、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观灯等,用以寄托对团圆、添丁、祈福等生存意愿;清明节有扎制风筝和放风筝活动,内涵之一是把晦气放走;端午节的主题围绕驱除瘟疫、镇除五毒展开,有划龙舟、贴钟馗画、剪 “驱除五毒”剪纸,做艾叶糕、葫芦糕,给小孩穿绣有 “虎吃五毒”的兜兜和佩戴 “五色香囊”等形式。
这些形式的技艺化就是民间艺术。因此,民间艺术不是生活的机械翻版和简单演绎,也不是民间艺人即兴的个性发挥,而是民俗文化所呈现出的艺术形态,承载了民间的生存意愿和现实诉求。事实上,民俗是民间艺术的源头活水,没有它们 “在场”,包括民间舞在内的民间艺术将失去最本质的构成因素,或消解、或变异、或死亡。换言之,离开了社会与言辞语境,民间舞就会悄然离开 “本我”。因此,哪怕走上舞台,这些由生态位构成的语境也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呈现出来。
章节三
“舞台”是什么?舞台是独立的 “审美———表现结构”的展示空间,带着康德以来一切高等美学的 “纯艺术”色彩。这个空间的物理构成是专业的,生理构成也是专业的。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民间舞 “两类三层说”——— “广场→课堂→舞台”才有了物质对象。在这个舞台上,“非遗”民间舞的展示非其本义舞蹈场;杨丽萍带着一群农民表演的 《云南映象》是对这个艺术舞蹈场的反用;只有经过课堂元素教学训练过的身体才符合那一舞台条件,即经由 “革命性”整理后的职业民间舞的展示。
如果我们把 “民俗”作为民间舞的背景———无论是哪一身份群体所跳,那么就可以把 “舞台”喻为职业民间舞者独占鳌头的前景。二者间的关系应是互为犄角支援:“没有背景,则前景即不成其为前景。”
[4](P281)背景是保守的,其保守主义的东西之所以今天还有力量,不在于其批判性,而在于它揭示人类全面的自我理解,在于它提供人们自我解困的路径,这路径通往前景。前景是将保守主义的视野与价值转化为现代性的生成性力量,而且是内在的生成性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便不具备与背景对话的资格。舞台的前景中应该渗透出民俗背景的幽灵。今天,许多舞台民间舞呈现出来的语篇有许多已经远离背景,成为一种 “悖论式存在”。
赵宛华和冷茂弘都是新型民间舞群体初建时的骨干,他们的舞台创作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32年 11月 14日,我 (赵宛华)出生在云南昆明。1948年开始学舞蹈时,已是高中生了……1949年 4月,我进入华大三部。
当时 “三部”就是学文艺。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学舞蹈……吴晓邦老师教我们人体运动的自然法则,陈锦清老师教我们现代舞。直到 1952年 12月,分配到中央歌舞团。那时候在团里跳过 《荷花舞》 《跑驴》……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之前,有一个教员训练班……那时候跟着苏联专家学习,讲的都是戏剧理论那一套,例如戏剧结构、人物关系等等,然后自己去理解,去转变成舞蹈的方法……后来就正式成立了北京舞蹈学校,这帮人 (许淑鮬)等就都跟着当老师去了。1957年,我在中央歌舞团里既当演员,也当编导。那时候,我们一天到晚不睡觉地搞创作,最多的时候,大家一天搞 50个节目……1958年底的时候,为了搞创作,我们都下去采风……回到北京看见群众演出跳 《花伞舞》,甩鞭子的动作一下腰很好看。我就有了灵感,以这个动作为主题,1959年编了一个 《花伞舞》,我的作品往往就抓一个主题动作,像 《花伞舞》,一个动作就够了,其他动作都由此而来。后来比赛还得了奖。接着1960年,我又创作了 《大刀进行曲》。当时开始反帝国主义了……我觉得大刀是中国传统功夫……我在武术书里找到了大刀就地式翻滚的动态。我还在北京门头沟等地采访了一些人,从生活中得到了很多民间智慧。这个 《大刀进行曲》后来就成了中央歌舞团的保留剧目。
我 (冷茂弘)1938年出生在四川石纉,和舞蹈结缘是在 1951年。部队到我们学校招人,我就去了 181师,当了文艺兵。但当时并不知道要搞舞蹈,那时候的部队提倡一专三会八能,我唱歌、跳舞、也演戏。当时跳的舞就是苏联的红军舞、马车舞等。那时候接受了一些简单的训练,还学了打击乐……后来部队很培养我,还把我送到了昆明的西南军区艺训班学习……跟着部队进军四川凉山……我的作品 《快乐的?嗦》就是 1959年在凉山文工团的时候创作的。作品中那个甩手的动作,就是看到铁链被砸断后,乡民从山上跑下来的那个瞬间抓住的,成为作品的主要动态。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呼喊 “大军啊,大军啊,救救我!”所以砸断铁链、奔跑的动态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舞蹈中反复出现的摆手动作,原本是彝族的民间舞中没有的,是我看到他们生活中的动态创作出来的,也揉进去了一些彝族本身的动态…… 《快乐的?嗦》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 10周年的献礼作品。在四川演出时一下轰动了,然后被四川省歌舞团拿来排,请我去当排练老师。后来四川省歌舞团带着这个节目来北京演出,也大受欢迎。作品名称中的 “?嗦”指的就是彝族,彝族人称自己是 “?嗦”。舞蹈中的“?嗦”也是我感觉到的彝族形象……[5]《花伞舞》中 “甩鞭子的动作”、 《大刀进行曲》中的 “中国传统功夫”都是隐藏在舞台之后的背景性资源。《花伞舞》 《大刀进行曲》连同其编导赵宛华留在了当代中国舞蹈史册中,而 “甩鞭子的动作”和北京门头沟的无名氏民间艺人则被淡出。职业化的民间舞在前景的舞台上熠熠闪光,民间艺人的民间舞则作为背景在消解,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分化已成为 “大势所趋”。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民间舞者和舞蹈作为一个整体取向的集合概念,民众与精英、民俗与舞台,农民的《花伞舞》与赵宛华的 《花伞舞》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后者在事实上已是高高在上了。
作为国家舞蹈舞台,“它在保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时可能增加另一部分人的风险。”
[6](P41)《快乐的?嗦》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取得政治伦理上成功的同时,作为彝族民间舞,其主题动作 “原本是彝族的民间舞中没有的”,是编导 “创作出来的”。所以其民俗的元素几近于零。
严格地讲,赵宛华、冷茂弘等一批舞台民间舞的初创者还未经过元素化训练 (这种训练体系是北京舞蹈学校建立时与他们分道扬镳 “当老师去了”的那帮人建立的),所以其对于民俗的 “拿来”太过于直接,甚至拿来的是非民俗的东西。因此,在由 “背景”过渡到 “前景”的专业化流程中,职业民间舞身份群体还要经由元素化流程才能获得艺术上的独立。
章节四
“元素化”全称 “元素教学法”,是专业民间舞者代表人物许淑鮬在建构民间舞专业时提出的一个术语:“元素教学法”是一种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舞蹈训练方法,它蕴涵着东方哲学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变化原理,从根本上来说,它也是现代舞对舞蹈基本运动规律认识的具体运用。所谓的 “元素”,是一个最简单、被提炼出来的东西,它或许是一个律动、一个造型,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形的动作,而只是一个力量或气息的 “感受”,但在这个最简单的“元素”里面,却蕴含有一个舞蹈最核心的“信息”,它犹如生命之初的那个 “受精卵”,之后通过 “时、空、力”三方面的一步步衍化发展,就能成长为一个丰富、复杂、高难的舞蹈。
舞蹈是鲜活的有机体,而不是一堆动作的堆砌,它承载有深厚的文化情感信息,这就要求舞者必须做到内外一体、形神兼备,因此,舞蹈的学习就既不能是动作的不走样模仿,也不能是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元素教学法”,抓住舞蹈的 “空间形态” “节奏动律” “力效状态”三大基本要素推衍展开,既有利于初学者很快切入,也能保证动作的发展不跑 “范”,因此,“元素教学法”就是一种既科学系统,也不失舞蹈艺术性的教学方法。
舞蹈的教学,不是老师在前面带,学生在后面模仿那么简单,也不是动作冷冰冰分解之后的再合成。 “分解教学法”和 “元素教学法”,分别代表了舞蹈教学的两个层级:前者是外在的、无机的、针对具体动作的,体现着 “先分析解剖,后归纳合成”的西方科学思想;后者是内在的、有机的、深入舞蹈艺术核心的,它蕴含了东方文化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世界观,一个合格的舞蹈老师,是必须要同时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的。
; ①在此,一个从民俗背景到舞台前景的技术方法的桥梁被建构。尽管许淑鮬理想化地力图使这由技术构成的桥梁既体现 “西方科学思想”,又蕴含东方 “天人合一”,但在事实上它对民间舞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职业民间舞者踏上桥梁之际,即是脱开民俗之际;而当他们迈上舞台之际,又是可以“过河拆桥”之际。即便从纯粹的民间舞技术上讲,民间艺人身上的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 “元素教学法”的科学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事实———特别是当这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身份群体形成之后,其身份地位必然要使自身扩张,以取得利益的最大化,并在获取话语权时登上当代中国民间舞的塔尖。作为桥梁,“元素化教学”的建构活动的基础是解构。关于 “解构”,中国舞蹈界常以之为对传统的 “拆解” “发展” “创新”等。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则认为,建构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这样就形成不完整的圆的轨迹,经过省略的传统之圆,被突破 (删节)而又增添新素质的圆的轨迹,因而不再是初始状态的传统。他在 1997年 《一种坚果硬壳中的解构》中一文指出:“这既是解构的构成;它不是混合物,而是记忆、是对历史的忠实、是那些过去的历史遗迹与异质性、与那些全新的东西、与某种突破之间的张力运动。”
[7](P6)简而言之,解构是一种从传统中走出的建构、在出走的同时进行建构的活动。但在当代中国民间舞 “元素化”过程中,传统 “根元素”的 “圆的轨迹”很少再被提及,越来越少有人对安徽花鼓灯 “兰花亮相”或东北秧歌 “前踢步”的舞蹈身体语源及经验技术感兴趣。此时,“科学性训练”的技术已然成为了一个自足体、自主体:你不懂这些技术,就没资格讨论民间舞。民间舞的科学活动(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简化成了技术活动……“元素化教学”其后的走向,并非提出者所能掌控,许淑鮬在生前最后时段 (2011年1月 14日去世)的忧心忡忡和焦躁不安表明了这一点。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