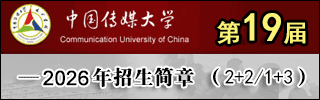内容提要
本论文主要由绪论、蒙古族萨满舞(博舞)的起源、蒙古族萨满舞的早期形态、蒙元以来萨满舞(博舞)的礼仪化、萨满舞(博舞)的佛教化、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传统萨满舞(博舞)的现代际遇六部分构成。以历史文化学的视角,考证并梳理了蒙古族萨满舞(博舞)的历史发生、转型、变迁及现代化改造的过程。同时对蒙古族博舞史做了一个小结性思考。将博舞进行挖掘、整理并研究,不仅丰富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的内容,而且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活态文化的一次抢救作业。
关键字: 蒙古族 萨满舞(博舞)历史文化 形态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six part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of Mongolian Shaman(Bo)dance, the original form of Mongolian Shaman(Bo)dance, the etiquette of Mongolian Shaman(Bo) dance after Yuan Dynasty of the Mongolia, the Buddhistization of Mongolian Shaman(Bo)danc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Shaman(Bo) dance in Keerqin. The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investigate and comb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beginning, transformatio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Mongolian Bo from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draws a thought-provoking conclusion to the history of Mongolian Bo dance. Therefore, the exploration,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Mongolian Bo dance can not only rich the content of dance history of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but also save the living culture of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Mongolia Shaman(Bo) dance History culture Form
蒙古族萨满舞(博舞)的历史变迁及其现代际遇
绪论
第一章 蒙古族萨满舞(博舞)的起源
一、蒙古族起源考
二、蒙古族萨满文化起源考
三、蒙古族早期萨满文化的形态
四、蒙古族萨满舞蹈起源考
第二章 蒙古族萨满舞(博舞)的早期形态
一、蒙古族早期萨满舞蹈(博舞)形态
二、蒙古族早期萨满舞蹈(博舞)特征
第三章 蒙元以来萨满舞(博舞)的礼仪化
一、蒙古族国家形成时期的礼仪化趋势
二、蒙古族国家形成时期的萨满舞蹈(博舞)的礼仪化
三、元帝国时期萨满文化的礼仪化改造
四、元帝国时期萨满舞蹈(博舞)的礼仪化改造
第四章 萨满舞(博舞)的佛教化
一、蒙元时期佛教对萨满舞蹈(博舞)的影响
二、北元以后佛教与萨满教的冲突
三、佛教文化对萨满舞蹈(博舞)的大规模改造
第五章 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传统萨满舞(博舞)的现代际遇
一、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传统萨满舞蹈(博舞)得以保持的历史原因分析
二、科尔沁地区蒙古族萨满舞蹈(博舞)的流传
三、蒙古族传统萨满舞蹈(博舞)的现代际遇
小结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绪 论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拥有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蒙古族及其先民长期笃信萨满教,这种信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和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在它的起源和发展中,宗教仪式与歌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同时由于蒙古民族豪爽乐观、能歌善舞,表现在萨满文化中的蒙古舞蹈更加富有特色,形成了蒙古族“博”舞(即萨满舞蹈)。这样一来,萨满文化中就保留了许多蒙古族的舞蹈形式。萨满文化和舞蹈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是具有珍贵文化价值的活化石。
博又被称为“孛额”,关于孛额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蒙古秘史》。蒙古族称男萨满为“博”,女萨满为“渥都干”。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其他文化影响的加剧,根据信仰的差异、行博方式以及职能方面的区别,博分为“世袭博”、“陶目勒博”(被博相中而成博,即非世袭博),“黑博”(坚持萨满教,与喇嘛教斗争的博)、“莱青”(喇嘛博)。此外,还有“牙斯必拉其博”(专门从事接骨、正骨的博)、“德木齐博”(专门从事接生的博)、“图勒格其博”或“莫日格其博”(专门从事占卜的博)。博的服饰分头饰和法裙。女博的头饰较为简单,只是把头发梳成3股大辫,在辫梢上系3个红缨穗。男博头饰有三种,一种是大红丝绸包头,第二种是用毡子制成的圆盅状帽盔,周围有一圈檐儿,顶端有帽疙瘩和红穗,第三种是用铜或铁制成的头盔。法裙包括“衬裙”和“罩裙”。衬裙为布质,分左、右两片,每片略呈上窄下宽,用一根布带连接。颜色有黑、黄、绿、红,镶有红色火焰图案。飘带很长,呈上窄下宽状,有些飘带的中间或末梢,分别缀有一只小铃铛和穗。罩裙由许多下垂的、宽宽的、围着腰的飘带组成。飘带有21条、23条、27条不等,颜色斑斓鲜艳,当博旋舞时,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科尔沁博在过“九道关”(包括“九根钢针”、“九个烙铁”、“九个铡刀”、“九个犁铧”、“九堆火”、“九根绳子”、“九个铜钱”、“九面铜镜”、“九条绒毛绳”)后,要穿新的法服和祖传的法服。另有一种盔甲服是科尔沁博莱青的服饰,由许多金属小片构成,后身片长。 博的法器有铜镜、博鼓、神鞭、宝剑、腰刀等。 科尔沁博作法时,师傅博带9到13面铜镜,徒弟博带8面,最少也带5面(常常是单数)。这些铜镜从小到大,用皮条穿系挂在腰间或前后胸,常达十几斤甚至几十斤。行博时,要不停地晃动,发出响亮而有节奏的撞击声。博鼓一般用铁圈蒙以皮革制成,其状如蒲扇,直径为30厘米,下有铁手柄,柄尾端拧成三个环,环上又挂9个直径相同的小铁环。作法时,且击且摇,发出“哗哗”的声响。还有“抓鼓”,无柄,装饰有作响的小铁环。腰刀为铁制,圆柄,长约10厘米,柄端饰以彩绸。宝剑,也叫七星宝剑,较腰刀短。作法时,供在神像旁边。 神鞭有四种,鸢鞭、铃鞭、布条缠裹的鞭、玩具小鞭。制神鞭须取河边的柳条为杆,缠以疯狗之皮(或用五彩布条),并缀以小铜镜、铃和穗。
博舞是蒙古族博在行博的过程中所跳的影响神灵、以祈福去灾颂神祭祖的舞蹈,这类舞蹈一般由感动神灵、神灵附体、神魔冲突、获得拯救、送神离开以及获得拯救后的狂欢等几个仪式化的动作部分组成。在行博的过程中,由主博来跳整个过程中主要的舞蹈,而辅博和其他人只是在博处于神灵刚刚附体的昏迷状态、需要共同赞美神和狂欢的阶段才会跳舞,这就决定了博舞主要是独舞,辅之以双人舞和群舞,不同于其他萨满教文化以女性萨满为主的传统,博舞大多数是以男性博为主,当然也有部分博的活动是以女性博为主,在蒙语中被称为“渥都干”,但数量比较少,其舞蹈结构与男性博所跳的大体相同,但动作和风格方面颇为不同,前者“腰部软舞多,还独有云部,移动步;迈三步转体闪身和迈三步转体将脚勾在另一条腿上顺向和逆向侧身击鼓的动作。”
博文化在蒙古各部落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阐释功能和社会规范功能。首先,无论是舞蹈、音乐,还是神话与诗歌,博文化都是蒙古文化的主要部分,并且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蒙古民族最基本的传统与习俗,人们不仅通过博文化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熟悉的、安全的关系,更由此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结构。其次,博文化相当系统地解释了世界的结构、自然的产生与演变、人类与蒙古民族的起源、人们日常生活、政治、历史以及生产等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博文化为蒙古民族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图示和确定自己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框架,指导着人们的日常实践。再者,作为祭祀、庆祝和祛灾的重要方式,博文化的象征符号也发挥着建构共同体和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它能够唤起人们对共同历史和共同祖先的记忆,这有效地增强了人们的共同体感,而包含在各种仪式中的规范则把一种秩序结构和观念有形无形地加于社会生活中,从而协调、规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博舞作为整个博文化中原初的、主要的部分,其所发挥功能与博文化是一样的。在博舞演变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两次来自异文化的冲击。一是始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后期才逐渐稳定下来的佛教文化的冲击,在这场长达近三百年的碰撞中,博舞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即分布区域和活动空间大为缩小、博舞形态中佛教因素大为增加;一是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现代文化的冲击,这次冲突尽管时间较短,但它对博舞的影响是更为深刻,几乎彻底地改变了博舞的神话内涵、社会基础、象征意义、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使之变成了徒具审美形式的一道文化奇观和博物馆中令人惊叹不已的文化遗迹,而作为具有重要社会文化价值的博文化和博舞则逐渐式微了。
尽管博舞在蒙古民族的文化中有如此重要价值,但有关博舞的研究现状却不尽如人意,这不仅体现在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静态的博舞形态分析,而缺少充分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这种静态的分析忽视了博舞的象征意义及其规范生活世界功能;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将一些舞者吸收博舞部分语言而创作、表演的舞蹈视为博舞的代表,然后从这一现代创作出发重建博舞的语言体系,再将后者作为所谓蒙古民族的舞蹈传统规范形式和本质特征,以此为研究框架去寻找、认识蒙古博舞的历史和特征。如我们在许多文章看到的将博舞与蒙古民族马上形象相联系,认为博舞表现了蒙古文化的尚武传统,按照这种尚武传统构建出的博舞形象自然也就主要表现为一种豪迈奔放的风格, 这种研究思路过于现代化,忽视了博舞的复杂性和历史过程中的丰富性,。
针对这种博舞研究中的非历史化、脱离文化语境的现象,本论文的研究从文化多元化的角度重新梳理博舞的历史流传及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系统地把握蒙古博舞历史特征与独特的命运。本论文的研究一方面采取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力图比较系统地描绘博舞历史过程、尽量以同情的态度阐释博舞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其社会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运用口述史的方法 ,采访尚存世的博、一些博文化研究专家、现代博舞的创作与表演者,了解他们与博舞发生的复杂的、历史的关系,并把他们与博舞的关系放在蒙古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审视现代化过程对博舞的多方面影响,突破主流的舞蹈史叙述神话现代化过程的偏向。 但是,由于现代文化对博舞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改造运动、现代科学与教育的传播、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蒙古人自我形象的改变等,需要专门的论述,而本论文又以博舞的历史变迁为主,因此,只能将博舞的现代际遇作为整个论文的一个部分做一简单的梳理,至于其具体的变化历史只好另文研究。
第一章 蒙古萨满舞(博舞)的起源
蒙古族萨满舞蹈是该民族历史的产物,也是蒙古高原萨满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要认识蒙古族萨满文化和萨满舞蹈必须先了解蒙古高原萨满文化的历史及其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但除个别研究者外,大多数研究者或者主要依据一些田野考察材料来认识萨满舞蹈,或者从文献中摘取部分信息,而没有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本章依据大量的文献,试图揭示萨满文化和萨满舞蹈与蒙古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 蒙古族起源
要讨论蒙古博舞的起源首先需要考证一下蒙古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关于蒙古族起源和其发源地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争论, 本文采用蒙古人源于东胡说。东胡人源于商周时代的北狄人,后为丁零人,始居阴山蒙古高原一带,其图腾为狼与鹿,曾与周朝发生冲突,《穆天子传》云“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次战争的失败后,丁零人分化为匈奴、东胡等。据《史记.匈奴列传》记“燕北有东胡、山戎”,服虔注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主要分布在潢水、老哈河、大凌河一带,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击破东胡,一部分东胡人居于乌桓山,一部分居于大鲜卑山,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端,后匈奴于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被汉击破,鲜卑人迁徙至匈奴故地,十余万匈奴人也自称鲜卑人,至此,拓跋鲜卑人完成了从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迁徙至呼伦湖地区,再向南迁徙至匈奴人居住的阴山北部一带。在许多鲜卑人南迁徙同时,还有部分鲜卑部落留居在大鲜卑山,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部众增多,势力逐渐扩大,成为室韦人,魏时与中原交往,《魏书》八十八卷载室韦人“好猎制”、“唯食猪鱼”、“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裤”,“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魏书·乌洛侯传》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这表明鲜卑人与室韦人和乌洛侯人之间的同源关系。室韦各部落分散而居,“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魏书.乌洛侯传》)《北史·室韦传》云室韦9部“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鳖。”在《隋书》没有关于乌洛侯记载,其《室韦传》关于南室韦部落的记载与《魏书.乌洛侯传》相似,可以推测室韦在隋时已被称为南室韦了,唐史上明确将乌洛侯列为南部室韦部落,从北魏到隋,室韦部落的畜牧业逐渐发展,《隋书.室韦传》载北室韦“雪深没马”、“牛畜多冻死”可为证,其时各部落之间依然“不相总一”,没有形成部落间的联盟。唐代室韦人分为五大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旧唐书.室韦传》载唐初室韦人开始“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这时候的室韦各部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部落,所谓“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聚落而居,或为小室,以皮覆上,时聚而居,至数十百家,”人们会参加一些集体生产和公共活动,“时聚弋猎,事毕而散”。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个时期的室韦分布比较广泛,其中大室韦有一支被称为蒙兀室韦,拒于大兴安岭,《旧唐书·北狄传》卷一九九下记载“其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健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又东经蒙兀室韦。” 唐时的望健河即今天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的额尔古纳河,俱轮泊指的是达赉湖。蒙兀室韦最初只有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的小部落,他们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区生息繁衍,大约经过四百年的时间形成了七十个斡巴黑(氏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字,其大体的位置在北至黑龙江上游,东抵额木尔山,西临生活在额尔古南河下游两岸的大室韦,南至大兴安岭北端,这七十个斡巴黑被称为“迭尔勒勤蒙古”,该部落大约在8世纪后期走出额尔古涅-昆一带,其中以孛尔帖赤那为首的若干部落西迁至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不儿罕合剌敦山(肯特山)一带,进入到游牧经济时代,因为从《唐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辽史》等文献资料看,这时候的室韦朝贡基本上都是羊、马、驼,而且数量较大,动辄是几百上千头。从孛尔帖赤那传承至朵奔篾尔干共十二代,他们自称为乞牙惕氏,朵奔篾尔干死后,阿兰.豁阿生三子,后三人分立合塔斤、撒列只兀惕、孛儿只斤三个氏族,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不同于一般的迭尔勒勤蒙古,尼伦蒙古和迭尔勒勤蒙古统称为“也克蒙古”,即大蒙古之意,其中的孛儿只斤氏后裔又繁衍十九个分支,各有名号,到十二世纪以后,室韦称呼已经被蒙古诸部的名称所代替,其后各支又继续繁衍,仅成吉思汗七世祖篾年土敦的七个儿子就各自形成一个十足,并繁衍成一个部落,而篾年土敦的五世孙屯必乃有九个儿子,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部落的始祖,成吉思汗为其中一个部落的后代,他在尼伦蒙古和迭尔勒勤蒙古基础上建立了蒙古国。这段历史期间,由于同中原、回纥、契丹之间的战争、交易和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室韦的生产力和文化都在在逐渐演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加剧,传统的氏族制逐渐解体,大约从9世纪蒙古开始向酋邦化的奴隶制过渡,到12世纪时建立了早期奴隶制国家,宋称之为“蒙古”,金时称之为“朦骨国”,有常备军队“秃鲁合黑”和相对完善的官僚制度,跨部落的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但这使得各部落还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重大的事情一般要通过各氏族的“那颜”们,即贵族们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决定。“总之,12世纪初,合不勒汗创建的蒙古国,是一个残存着浓厚的氏族制的军政合一的早期奴隶制国家。旧的氏族贵族变成了保守的奴隶主贵族集团,成为统治阶级。”
二、蒙古族萨满文化起源考
以上我们简述了蒙古民族的早期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人是发源于并主要生活在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一带,是从东胡经鲜卑再经室韦演化而来,在其演化过程又同匈奴、柔然、突厥、契丹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逐步从以渔猎、采集等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以部落为中心的原始共同体为主过渡到以游牧和部落联盟为主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大规模的迁徙过程,有不少其他民族融入到蒙古的先民中,这些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决定了蒙古族早期文化必然要广泛地受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并与这一地域的其他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早期的东胡人还是后来的鲜卑人及更后的室韦人,他们都曾生活在我国北方蒙古高原的阴山、大兴安岭这一带,从世界文化的分布来看,这一地域的文化中最主要、最普遍的文化形态是萨满教文化,这种宗教以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为基础,通过一个能通神灵的主祭者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化活动,来影响神灵,进而影响自然和社会。在我国历代史书上有大量的关于北方民族祖先,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民族的宗教活动的记载,如《史记.匈奴传》记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汉书.匈奴传》云匈奴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 《魏书.高车传》载高车“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羚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币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佗,则为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币,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周书.突厥传》 云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
从族源历史的角度来说,蒙古族的先祖东胡、鲜卑、室韦都属于萨满文化区,在他们的神话世界中,动植物、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祖先等,凡是在人们的经验范围中出现过的事物都有其自己的神灵,人们通过相应的仪式来祭祀它们,以求它们或者帮助人类,或者不要给人类带来危险、灾难等。《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贷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这表明乌桓、鲜卑有祖先和自然深崇拜,在其重大仪式活动中,歌舞都有重要的作用。《旧唐书.北狄传》说室韦之俗与突厥同,《隋书.北狄传》云突厥之俗“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可见在室韦文化传统中,人们也颇为重视死亡祭祀:首先,人们将死亡与种族延续和家族生产联系起来;其次,常常通过手段将死者形象和战争事迹加以表现、演绎;再者,祭祀死者的活动颇为疯狂和神秘;最后,常将尸体置于树上,表明其文化与树有神秘的关系。
从上述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蒙古民族生活的地区和其原始族源的文化都具有典型的萨满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关系到整个民族、部落当前的行止、休咎、祸福,以及将来的绵衍、兴盛的神圣祭坛。……意味深长的是,众多的萨满教神灵,是通过激励中的萨满五道——通神的具体形态,再现于祭坛上。”
三 、蒙古族早期萨满文化的形态
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民间记忆、考古发现和散布在北方的岩画可以推测萨满神灵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各种自然神,这是萨满教中最古老的神灵,他们一般都是同人们生产和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神灵,其中不少是各民族实践活动直接作用的对象,萨满通过模仿这些自然物的形象、活动方式并对之施加各种仪式化的动作可以产生影响、支配甚至获取这些自然物的象征性结果,在我国北方“岩画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散布之密,作画之早,延续时间之长,为世所罕见。” 其中相当一部分岩画是萨满活动对象和仪式,如内蒙古大兴安岭阿娘尼岩画就是一个通过萨满活动影响动物以帮助狩猎的场面,绘有驼鹿、驯鹿、犬、人等,还绘制了一面萨满鼓,在岩画外面的树上挂有许多陈旧朽烂的布条等,考古学界认为这幅岩画是一千多年前的室韦人或者颚温克人萨满生活的写照,在蒙古、黑龙江和西伯利亚等地有不少岩画直接反映萨满活动,如黑龙江沿岸发现的岩画中就有不少或者是一个萨满拿着一面神鼓在活动,或者是主祭萨满和助神人拿着神鼓共同舞蹈的情景,或者是萨满和氏族成员共祭的场面,许多人的手中都持有神鼓。
一类是图腾神,当人类演化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不再仅仅依靠自然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再匍匐在所有的自然力量面前,而是感受到某些自然力量与自己有更密切的关系和更伟大的能力,他们感到拥有这类自然力量的护佑就可以更安全、也更能影响自然,于是乎开始将这类自然力量在整个自然神谱系中突出出来并使之为本氏族或部落的长期固定供祭的神灵,在一些固定的时节、重大活动或各种重要的时刻都会举行一定的仪式来祭祀这位神灵,而且,人们还常常将图腾神与本族群的起源联系起来,以表明本族群的神圣性。《周书.突厥传》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魏书》卷九十一记高车“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这两侧史料表明匈奴和突厥都把狼与本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而匈奴王的女儿配与狼的传说无疑是该民族将狼视为神并以最好的方式祭祀它的传统的体现。
一类是已经高度抽象的、人格化的神和祖先神。人类在其生产和生活过程,逐渐超越了自己活动的经验范围,开始在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人类活动之间建立联系,在这种建构活动中,人们一方面认为有一些超越人类之外的普遍性力量在支配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力量具有人一般的意志,因此,他们常常将各种自然力量人格化并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创造与被创造等一系列的关系,这时候已经开始建立神的谱系,天和太阳等在整个神的结构中居于相当高的地位。如阴山岩画中就有用树皮制作的太阳神偶像图案,这类太阳神常由人格化的人面和代表太阳光线的射线构成,内蒙古乌海桌子山岩刻中的太阳神更是口鼻耳俱全,这种偶像与萨满教仪式中所使用太阳神偶像非常相似,阴山岩画中还有萨满祭日的图像。事实上,在不少北方民族的传说中,有相当多的人格化的关于人类的起源、宇宙的结构、各种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故事以及先民祭祀神灵的仪式的记载,如蒙古萨满教中有一个“吉雅奇”的神灵,有一首请神歌云吉雅奇“乘坐一辆无轮车/驾起两只罕达 /你飞驰在山岭间/……犍牛角内是神堂/挂进毡车停前方/保佑子孙自久长。”作为一个狩猎守护神,吉雅奇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自然神,不仅具有人类的行为特征,而且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已经成为整个山林世界和狩猎活动支配性力量。还有一类是祖先神,《隋书.北狄传》载室韦“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我们在上文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大量的材料,以图简单地梳理蒙古形成以前的历史过程、文化传承和萨满文化的主要特点。如果这种传承关系和文化形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断言蒙古萨满文化正是从东胡、经鲜卑再到室韦传承而下的萨满文化的后裔,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又受到匈奴、突厥、契丹、女真等生活在北方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传世的文献和民间记忆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蒙古文化与上述民族文化之间连续性的例证。如在上述的一些文献记载中都表明在北方民族中“树”这一意象常常具有神圣的意义,人们通过将树本身视为神或者将祖先的灵魂安置在树上,从而将树转化成本民族祭拜的对象,通过绕树而舞获将祭品供在树下以表达自己的崇拜,其中一个著名的风俗就是将布条系在树上,这种在树上挂布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蒙古时代,《多桑蒙古史》说忽图剌汗“英勇著名当时,进击篾尔乞部时,在道上曾祷于树下。设若胜敌,将以美布饰此树上。后果胜敌,以布饰树,率其士卒,绕树而舞。” 再如狼作为一种图腾是部分匈奴和突厥民族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人们对这一图腾的记忆到蒙古时代还常常见到,《蒙古秘史》载“当初元朝人的祖,是一个天生的苍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下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蒙古源流》卷四记载:“岁次丁亥三月十八日,兵行唐古特之便,于杭爱之地方设围,汗以神机降旨曰:今围中有一郭斡玛喇勒,有一布尔特克沁绰诺,出此二者勿杀。” “郭斡玛喇勒”即草黄母鹿,“布尔特克沁绰诺”即苍色狼。 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萨满文化中的最高神“腾格里”的来源于突厥文化有密切联系,在蒙古博的祭天的祷词中常说:“上天有九十九尊腾格里,下界有地母七十七层阶梯。……我东方的四十四尊腾格里,我西方的五十五尊腾格里,我北方的三尊腾格里。” 这个腾格里神的名称早在公元716年-734年的突厥部落的毗加可汗就已经出现,当时的突厥人把自己的兴盛看成是“腾格里、乌弥和神圣的地-水”赐予的,而蒙古人敬仰的女神乌玛同突厥神乌弥也有影响的关系。 当然通过蒙古萨满在早期重大祭祀中的活动,也可以应证萨满文化与其始源民族之间的萨满文化之间的关系。《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北方诸民族祭天活动颇为详细,“(夫余)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高句丽)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祭鬼神,又祠灵星、社稷。……(秽)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会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马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园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据《史集》记成吉思汗登记命名仪式上,萨满阔阔出代表天神宣布“最高的主让你统治大地”“最高的著名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 《蒙古秘史》也说萨满豁尔赤当中宣称“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铁木真做。”而《元史》72卷《祭祀志》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其祭祀活动都是由萨满主持。
四 、蒙古族萨满舞蹈起源考
如果说蒙古的萨满文化与其先民的萨满文化之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那么,萨满舞与其始源民族的萨满舞蹈之间应当能够建立直接的传承关系。我们可以在绕树而舞这一习俗中找到明证,《史记 .匈奴传》记匈奴人“秋,马肥,大会蹛林。”(蹛:音带。服虔注云:“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正义颜师古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魏书.高车传》在高车人在地震发生后的秋日,马肥之时,会回到发生地震之地,人持一束柳桋,人们骑马绕之,并举行盛大的祭祀或娱乐活动。《金书》志十六云金拜天仪式后“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这里固然不再绕树而舞,但在其以树为中心而进行的比赛中依然可以看到树在这些民族萨满传统中曾占据的地位。辽为契丹人所建立,而契丹又是鲜卑人的一支,室韦人也是鲜卑的后裔,其风俗当有同一之处,而且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内蒙古大兴安岭阿娘尼岩画外的树上所系的许多布条和室韦人在父母死后将其尸体置于树上三年的风俗,表明了树在室韦人心目崇高地位,而如果我们认同文献所说的室韦人与匈奴、突厥同俗的说法,那么,室韦在安葬其父母时也必然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其中当然包括将其父母之尸体置于树上和将之从树上取下来时所进行的仪式性活动,而舞蹈肯定是这仪式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作为室韦人直接后裔的蒙古人也继承了这种绕树而发生的仪式性活动,包括舞蹈活动,在《蒙古秘史》中也有记载,忽图剌被推选为可汗时,蒙古部众“在繁茂的树荫下,跳舞,欢宴,把杂草踏烂,地皮也踏破了。”这段文字另有译文为“绕蓬松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人也
有绕树而舞的习俗。按蒙古旧俗,产生新可汗都需要由萨满宣布并由其主持相应的仪式性活动,这里的绕树而舞当为整个仪式性活动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次世俗性的欢庆舞蹈。从上述历史源流关系中,蒙古族萨满舞不只是蒙古人对自己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直接反应的产物,更是从更为原初的先民那里继承发展的结果。
第二章 蒙古博舞(萨满舞)的早期形态
上文分析了蒙古萨满舞蹈的起源以及其与其他民族萨满文化的关系,因此,要了解蒙古萨满舞的原始形态,就需要认真地对待蒙古族人从其先民那里继承来的文化遗产,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这一方面的系统研究几乎还没有展开,但蒙古地区岩画的发现为研究原始萨满舞蹈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章将依据当代考古发现的材料系统描述早期萨满舞蹈的形态。
一、 蒙古族早期萨满舞蹈(博舞)形态
从蒙古先民的分布来看,其活动范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到阴山,北到贝加尔湖。其中阴山、巴丹吉林沙漠、锡林郭勒草原的苏尼特草原等地是北狄、东胡、匈奴、鲜卑、乌桓、契丹等民族活动的区域,《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可见胡人在战国时代活动在阴山一带。《汉书·匈奴传》“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间,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匈奴人在阴山一带活动之盛可见一斑。《魏书·世祖纪上》记载北魏鲜卑歌手斛律金作《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表明这一时代活动在阴山地区主要是鲜卑人。巴丹吉林沙漠地区在“春秋时代为北狄牧地。战国至秦为月氏居地。西汉为匈奴右贤王牧地。东汉至三国时代,是羌、乌桓、鲜卑、匈奴等族的牧地。西晋时,秃发、鲜卑牧于贺兰山西部;匈奴铁弗部和鲜卑拓跋部由起出没于阿拉善旗东部。北朝时期,……阿拉善东部和北部为柔然游牧地;西南部为秃发、鲜卑牧区。” 而锡林郭勒草原的苏尼特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等地“自战国至秦汉为东胡居地;东汉至五胡十六国为乌桓、鲜卑所居;北朝至隋唐维突厥、回纥地;辽金为契丹、女真活动之地。” 这些地区广泛地分布着岩画和壁画,它们直观地反映这些民族历史的材料,“内蒙古岩画,从整体和本质上看,具有鲜明的萨满教性质。……从作画功能上看,岩画的功能尽管是多功能的,然而在诸种功能中,通过作画对动物野性施加巫术;通过媚神娱神的岩画舞蹈,敬祭神灵,以实现原始宗教在生活上的作用;通过刻制众多的以面具为载体的神灵岩画,以宣泄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对众神灵的顶礼膜拜,并通过祭拜偶像对祖先和自然物进行崇拜。” 。这些民族又都是与蒙古民族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因此,从阴山等地岩画的萨满活动和舞蹈活动中可以推测蒙古先民萨满活动中舞蹈的形态和特征。
在蒙古地区的岩画中,有不少是表现萨满通过舞蹈祭祀、祈祷神灵的画面,有单人的、双人的、三人的和群体的各种场面,萨满的舞蹈动作也是丰富多样的。在单人祈祷祭神岩画中,被祭祀的神灵主要是自然神、祖先神、动物神和人格化的神灵。有一幅祭拜太阳岩画,萨满虔诚地站立在大地上,双臂上举,双手合十过顶,上身挺直,腿较短,并向内弯,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还有一幅以舞蹈祭祀动物神的岩画,一个舞者托举一头山羊,双手上举,上臂与肩平,小臂略向内倾斜,上身挺直,作马步,整个舞姿给人以力量感,在其右下角有一柱状物,估计为萨满法器;或者娱神,一幅描绘的是一个女萨满,头戴冠帽,着长袍,上肢平抬弯曲至两肋,双腿较短,左腿稍弯,右腿后蹬,整个体态婀娜多姿,表现了女萨满娱神、媚神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巴丹吉林德布敦苏海有一幅岩画,画面上一个舞者头部装扮成鸟头形,扭向一边,长喙,双臂非常长,向外扬,如同鸟飞翔之状,五指张开,如同鸟爪,收腹,腿较短,做蹲状,脚尖朝外,舞姿颇像鸟儿飞翔。在锡林郭勒盟的哈登布兹有一幅岩画,画面左下方有一舞者,身体向右下角大幅度倾斜,上肢平伸,也向右倾斜,两腿大幅度叉开,脚尖朝外,系尾饰,上身动感较明显,舞者右肩上方有神秘的符号,方向与身体大体一致,画面的左上较有一巨大的神秘符号,横放着,画面的中部有圆形符号,估计为动物足迹,在其右上角有一头骆驼。双人祈祷的舞蹈也颇为常见,舞者的形象与单人舞略有不同,就所见到的几幅岩画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每幅岩画中的两个舞者的动作大体相同,身体方向也一致;一是每幅岩画中的舞者图案都是一大一小,靠近祭祀对象的舞者形象比较大,远离祭祀对象的舞者形象比较小,这种形象比例应当是萨满在祭祀活动中主次地位的反映;三是几乎所有的双人祭祀祈祷的萨满舞蹈都是站立的,没有见到作马步的形象;四是所有双人舞蹈或是利用身体倾斜、或是利用腰部扭动、或是利用腿部曲弓、或是利用挺胸收腹、或是利用双臂摆动、或是利用手的开合和手腕抖动,给人造成了运动感强、舞姿婀娜的印象,不同于单人舞颇多对称、平衡、严肃的舞姿;五是舞蹈动作以三类动作为主,一类是上肢平伸,至肘部向上折,或手掌相对或举一可影响神灵的器物,一类动作是上肢与腿向同一方向摆动,上身和腰部有明显的运动,或者上肢平伸至肘下垂,上身比较挺直,腿前后叉开。三人舞蹈岩画的舞蹈形态明显不同于两人舞蹈的一致性。在每幅三人祭祀岩画中,舞者动作各不相同,它们或者通过头部颈部的运、或者通过腰部臀部的扭动、或者通过四肢姿态的变化表现出丰富多姿的舞蹈形态。在阴山额勒斯台有一幅三人祈祷的岩画,最上面的一个舞者头顶上有一动物图案,头向右微倾,上身直挺,双手合并于胸前,两眼平视,上身与大腿构成直角,两腿下蹲成环状,大腿向外撇,几乎构成一条直线,双脚踮起,脚跟相触,脚尖朝外;左下方的舞者头上有两支鹿角,头向左倾,颈部上抬,双手叉腰,收腹,上身和大腿构成一钝角,双腿弯曲成环状,大腿向前,两脚之间有一定距离,脚踮起,脚尖朝外;右下角舞者舞姿与上方的相似,但其戴一面具,周身长带环绕,顶部有三个饰物,站在几上,右边有一棵树状物,各舞者的饰物、动作和使用的神器各不相同,但可以推测的是舞者的饰物和神器在舞蹈过程一定发挥着具体的作用。群舞祭神的岩画也比较常见,在哈日拉地区的岩画中有一幅群舞岩画,画面上的舞者几乎全为正面,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双臂上举,有的双臂平伸,两腿或外撇或侧身作弓步,其中一个舞者体形较大,头戴犄角状饰物,有面具,头顶上方有一奇异之物,当为具有神力的象征物,双手叉腰,双腿外撇,有尾饰,颇有气势,估计为整个祭祀活动的主持萨满,在众舞者中间有一圆形符号和一些动物,前者应当为萨满活动中使用的鼓。从笔者看到的萨满岩画来看,这些萨满舞蹈应当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早期的萨满舞蹈可能并不要求有法服、法器,而主要是通过舞蹈动作和祭品来影响神灵,而且动作也以庄严肃穆为主,但后来就逐渐增加了法服和法器,而且越来越复杂,同时舞蹈动作也比较多样,有祈祷的庄严、娱神的婀娜、受神灵影响时的狂热等。从其舞蹈动作来看,萨满舞蹈或者表现了天、人、自然之间的象征性联系,或者表现了萨满通过模仿神灵的动作、娱乐神灵等来影响神灵的观念、或者表现了人在神灵面前的敬畏情感,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内蒙古地区现存的岩画可以看出,萨满在狩猎活动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在阴山的几公海勒斯有一幅出猎岩画,画面上方有四支北山羊,中间两支山羊相互顶角,右下方有一骑马猎人,弓拉满月,面朝左前方,背朝北山羊,正策马前行,岩画的左下角有一舞者,处于画面最大的北山羊的腹部正下方,正面,头戴顶饰,双手叉腰,两腿张开,脚跟着地,脚尖朝上,系尾饰,舞姿矫健有力。从画面中骑者的神态来看,这幅画应当表现了狩猎之前萨满通过舞蹈祈祷神灵、影响动物以帮助猎人的。在大兴安岭额尔古纳右旗的阿娘尼岩画。画面由驼鹿、驯鹿、猎犬、人、猎人、萨满和萨满鼓构成,画面非常疏朗,仿佛各个事物之间互不相干,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猎物分布在画面的上下两端,有两个猎人有人形线条来表示,四个猎人分布在画面中部的左右两侧,猎人都面向左边、作奔跑追赶状,每人的姿势各不相同,整个空旷的画面中间只有一萨满图形,用轮廓线表示其形象,一手平伸,五指张开,指向猎人奔跑的方向,在画面的右下角有一萨满鼓,中间有“十”字形,有意思的是整个画面没有弓箭,因此,这幅岩画当是表现了人们希望通过萨满活动赋予猎人以力量,而猎人随着萨满的指示而舞蹈的情形。在阴山乞伦浩套有一幅庆丰收的岩画,画面的中右部是一头体形非常大的鹿,画面的左边有一细颈舞者,头插三根羽毛状饰物,面向麋鹿,肩部平放一细长物体,右手上举,手持弓箭状的东西,系一长长的尾饰,双腿前后叉开,左脚跟提起、脚尖着地,右脚跟着地、脚尖朝上,载歌载舞,在鹿的左边,有一舞者,体形较小,左手向后平伸,右手向前平伸至肘部上折,左脚着地,右脚提起,整个舞姿给人以轻盈欢快之感。在克什克腾旗的白岔河有一幅岩画,画面最上端是一只手 ,五指大展,其下是前后而行的三只野猪,猪的脚下是一条之下而上的断断续续的斜线,斜线的右下方是以模糊图像,当为部落的保护神之类的存在物,在野猪的上下是许多裸体而舞的人,大部分都是平伸双臂,叉开两腿,但形态各异,有一舞者头上方有一野猪,右手提一物,其舞姿颇似甲骨卜辞的“舞”字,从其所处的与众不同的位置、舞姿和手持物应当是一位萨满,下端三位舞者连臂而舞 ,右下角有一奔鹿。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萨满活动在整个狩猎活动过程都存在着,萨满通过舞蹈影响神灵以作用动物、赋予猎人以神力或者为其指示狩猎的方向、欢庆狩猎的成功等,其舞蹈场面中一般都有猎人,这些猎人或者随萨满翩翩起舞,或者接受萨满赋予的神圣力量,而舞蹈动作有些是模仿动物的行动,有些是模仿猎人的狩猎活动,有些只是具有祈祷姿势的神圣感,而有些则是非常优美的动作,这表明萨满舞蹈动作也是丰富多样的。
萨满舞蹈对游牧生活的影响也在岩画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夏拉玛山有一幅岩画,上部为一条蛇,蛇身上有各种抽象符号,当为民族图腾神。在蛇的右下方有三种图案,从上往下依次为一个由椭圆、圆和方形构成的图案,一个上部和右下部都有柄状物的圆形图案和一个圆形图案,尽管无法判断三个图案具体的象征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与图腾物之间有神秘的联系。在三个图案的右边、为这三个图案所包围的是一个带着面具的萨满,这个萨满面向东边,脚踏一个动物。图案的左边为一人牵着一符号化的动物,动物身上有一条横线,似乎表示该动物将被肢解,再往右是一些羊、狗和动物足印,它们的朝向与萨满的面向正好相反。岩画的最右边是一个人骑在马上,马很大,人非常小,不成比例,表明在整个岩画中,马上牧人对动物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这不同于一般的游牧岩画牧人会占有合理比例的情形。岩画的下边是一个人面对这一条狗,人的方向与萨满同,动作也与萨满一样。在这幅图画中,萨满身体略向前倾,从头部到腿弯基本构成一条直线,给人一种绷紧力量的感觉,右手叉腰,腰部挺直有力,左臂抬起与肩平,小臂上弯,手掌平伸,与小臂构成近乎九十度角,双腿前后岔开,右脚登地,小腿与大腿构成一定弧度的前弯,左腿伸直。这明显的不是一般的祈祷动作,而是要通过舞蹈来娱神。值得注意的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和科尔沁游牧岩画中萨满的动作颇有相似性,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双手向下合在胸前,构成一个圆形,双腿也盘成圆形,一类是双手上举,或者是上臂与肩齐,小臂上举与上臂构成直角,五指展开朝天,或者是双手上举过头顶,构成一圆形。这两类祈祷动作形式在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具有代表性。
二、蒙古族早期萨满舞蹈(博舞)特征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萨满舞蹈的几个特点。首先,萨满舞蹈语言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不同舞者的舞蹈语言各有特点,而且萨满在整个巫术活动的过程中的舞蹈语言也是变化多姿的,但无论是双人还是三人或者多人舞蹈,这其中必然有一个主要负责祭神的萨满,他的舞蹈动作在画面中占中心的地位,也更有特点。在萨满舞蹈中,头部的表现形式比较鲜明,可以通过头饰、面具、头部动作和眼睛来表现萨满与神交接时的精神状况,其中头饰主要为羽毛和鹿角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原始社会中都具有某些通神的神秘色彩,而不是简单的装饰物;面具在萨满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一般分为动物面具、神灵面具和图腾面具,通过这些面具可以影响面具所代表的神灵,而在舞蹈过程中使用面具不仅可以使整个舞蹈活动具有神秘的色彩, 而且可以增加舞蹈的表现力;萨满舞蹈的头部动作比较多,有摇头、抬头、仰首、左右侧首、俯首等,让人可以感到其运动节奏。萨满舞者的腰部动作也有较多变化,有些挺直上身,有些通过抬头、挺胸、收腹、弯腰、体臀、曲腿等形成优美的身体曲线,其物资或给人以刚健有力之感,或让人产生妩媚动人之叹。萨满舞蹈的手势变化细微,臂、掌、腕、指个部分都得到充分利用,就臂部动作来说,或叉手于腰,或双臂外扬,或平伸,或合于胸前,或双臂上举作环状,或一手叉腰一臂下垂,姿势变化无穷,或庄严肃穆,或变化曲折,而手指也有弹、收、展、握、开、转腕等不同的变化,富有节奏,动感强烈。萨满舞者的双腿或内弯或外伸或作马步或两腿大跨或弯成曲环,造型多变,这些变化反映了人们已经能够通过腿部站立、跳跃、弹跳、抬腿、屈膝、勾、踢等表现不同的动率。总之,萨满舞通过头、上肢、腰、手、腿的配合,完成了既具有节奏感又具有丰富意义的舞蹈造型,创造了与狩猎游牧民族生活与原始信仰密切联系的舞蹈形态。就萨满舞蹈的参与者来说,大体上有几种情形,一是由萨满单独完成的舞蹈,一是由主祭萨满与助手共同完成的,一是在萨满的引导下部落中的许多成员集体完成的。参与者的不同,萨满舞蹈的形态似乎也有所不同。具体说,由萨满单独完成的舞蹈更偏向于严肃风格;而双人完成的舞蹈则主次分明,动作整齐而富于变化;而集体完成的舞蹈则更具功利色彩,一般直接与狩猎、游牧、种族繁衍等场面相关,舞蹈动作有明显的娱神色彩。从看到的岩画分析,萨满舞蹈基本上还是在部落公共空间、狩猎和游牧现场中举行,这些空间决定了萨满舞蹈不仅是部落成员可以集体参与,而且可以直接起到神灵以作用于各种活动的对象的作用。
其次,萨满舞的类型。岩画中萨满舞蹈的类型相当丰富,大体说来表现在如下几种:(1)单人舞(2)双人舞(3)三人舞(4)群舞。
单人舞蹈就是由萨满来跳,舞动动作尽管有些变化,但是整体风格比较庄严肃穆,多为正面图案,上身常常挺直,双臂或平伸或上举或在胸前环绕,保持平衡的体态,双腿或展开或作马步,稳健有力;
双人舞是一个萨满领舞,另有一个舞者或者辅助萨满配合,后者动作模仿前者,就笔者所接触的材料来看,双人舞动作比较单人舞动作要丰富、灵活、富于变化、颇有动律,而两人一起舞蹈也增加了节奏感,估计主要是娱乐神灵的舞蹈;
三人舞蹈是由主祭萨满带领祭祀活动的参与者一起共舞的场景,从舞者动作不一致的情形可以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不都是训练有素的萨满,正因为如此,整个岩画上的舞蹈动作就相当丰富多样,头部、腰部、臀部、四肢和手脚的动作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三人舞蹈是明显的娱神舞蹈;
从目前情况看,群舞的动作比较简单,画面尽管舞者很多,但动作变化不多,大多与祈祷动作相似,舞者围绕主祭萨满或者神物而舞,场面壮观,动作整齐有力,颇有气势。群舞参加者并不都是萨满,而其动作竟这样的整齐,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一是全民皆好巫,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具有与神相通的能力,但大家都掌握了祭神舞蹈的一般动作。这与历史资料的记载有一致之处,史书多次提到胡巫,其盛行之势与南方的巫可谓旗鼓相当,《国语·楚语》说楚国是“人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一是这些动作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部落或氏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具有影响神灵的作用,人们通过这些符号祈求神灵的帮助,因此,一旦有祈求神灵或娱乐神灵的需要,人们就会集体表演这些舞蹈动作。 这种由单人、双人、三人和多人舞蹈构成整个祭祀活动的岩画在广西和中亚巫术岩画中分布的比较广泛。从这种意义上说,萨满舞蹈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和信仰的表达,而是要通过一个完整的叙事来讲述神灵如何与人类发生关系并进而赋予人类神力以战胜对立性力量的过程,
第三,在整个祭祀活动中,萨满的舞蹈动作具有神秘的象征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语言、神话和艺术有共同的神话母体,是一种隐喻性思维,这种思维将简单的感性体验中心化和强化,具有将生命和世界形式化的审美性结构法则。 萨满舞蹈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式,它通过具体的饰物、面具、动作等模仿世界,以此影响世界上的存在物,进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隐喻性思维,它的每一个语言都指向了天地人神物的整体关系,都明确地要将神的力量转移到人的身上、以对动物等发生作用,这种特点使它与科学思维区别开来,科学思维要将世界分析综合、加以逻辑推演的方式,要追求单一性和清晰性,以及其语言对象的可观察性或可推理性。萨满作为北方民族中主持起到祭祀神灵活动的人,其舞蹈的主要功能在于影响神灵,因此,无论是其舞蹈动作、舞蹈过程所使用的器物,还是其所佩戴的饰物和舞蹈场面都应当具有能够通神的作用。这里仅就萨满舞蹈动作来谈谈其象征意义。在萨满祭神舞蹈中有几种动作非常普遍,一种是上身挺直、双臂平伸、双腿叉开,一种是双臂上举成环状、双腿叉开,一种是双手叉腰、双腿叉开,这些动作给人一种脚踩着大地、头顶着天空、能够通天地人神的感觉。这些舞姿非常像甲骨卜辞和篆书中的“大”“人”“天”“巫”“示”等字形,而后者在我国古典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它们都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神话式的理解。许慎《说文解字》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觋,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巫”字的原型,就是模拟一个人两袖作舞的样子,意思就是以舞蹈沟通人神的人,这个字形与两手叉腰的舞姿颇为相似,《说文解字》释“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上从三,垂明星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可见“示”意味着人与天象之间的祭祀性关系,而这种祭祀活动在中国原始文化是通过巫来完成的,巫即祝,《说文解字》:“祝,祭主赞词者。”甲骨文“祝”字从“示”从“兄”,亦是神主,象人跪于神主之前有所祷告之形。因此,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巫是一个能将天地人神物联系起来、建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存在者,张光直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征。” 实际上,在萨满舞蹈岩画中就有这种天地人神物通过萨满活动联结起来的画面,在阴山德和尚德有一幅岩画,画面相当壮观,最上面是是一个抽象符号,左上角有一个骑者,图形比较小,向右下一点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有动物、猎人等,左边是三个翩翩起舞的舞者,有的系尾饰,有的持牛尾,第二个舞者的腋下有一个“人”形的饰物,当为牛尾舞饰,这一情景颇似《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左下有两头羊和一些柱状物,在羊的下方是一男一女两个舞者,手合于胸前,臀部向后翘起,右腿作弓形,左腿跪地,整个身体向前倾斜,以上内容在整个岩画的上部,约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下部四分之三区域分布大量的动物、神灵面具、猎人、骑者、舞者、放射状人形和人形面具,其中的神灵面具有太阳、星星、月亮和一些动物,在人面和兽面之间有一个萨满,头的比例比较大,有头饰,戴面具,左手展开上折,手掌上托有一物,右手下垂,持有鼓状物,身体有点像动物,其左侧有两个舞者,都系有长长的尾饰,随着舞者的动作在晃动,在整个画面的最低端有一舞者,身体向右倾斜,左肩有一物,似乎为一动物,估计为祭祀中的用来贡献神灵的祭品。这个画面非常形象地表现了以萨满活动为中心的世界,它把各种自然神、动物神、人格神以及人类自我形象等结合在一起,并用舞蹈来祈祷、娱乐神灵,在这里天地人神物是没有分离的,任何语言、包括舞蹈动作都意在把这些存在物联系起来,并建立起它们相互影响的关系。
第四,萨满舞蹈具有原始的公共性和功利性。1、萨满活动和萨满舞蹈的参与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部族成员可以按照整个萨满活动的规范要求自由地参与到整个萨满舞蹈中去,不受身份与阶级限制,不仅在舞蹈岩画中看不到明显的阶级差别,而且在有关蒙古族的早期历史记载中也没有这种差别,从《蒙古秘史》所记载的几个关于部落成员绕树而舞的场面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几乎是全体参与到舞蹈活动中,或者娱乐神灵或者感激神灵,不一而足;2、萨满活动和萨满舞蹈主要是在具有万神殿性质的自然空间中举行,如树下、被神话化的某一地方、与部落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空间等,这种空间具有广场的性质,没有太多的建立在社会等级差别基础上的规范,这种规范会限制人们进入某一空间中,而广场则是人们可以进入并参与到正在举行的活动中空间,根据上文关于蒙古先民岩画的描述,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萨满活动都是在这种具有神圣性的自然空间中举行的,很少看到是在一定程度已经彻底人化的空间中——如寺庙、宫廷等——举行的萨满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岩画中,笔者目前所见的只有一幅岩画中的舞蹈是在一个屋子里举行的;3、萨满舞蹈固然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象征意义、相对固定的语言程式及与神灵之间神圣关系,但这种程式化只是神人之间的一种固定关系,而不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等级化建构,这种萨满活动一般都是关乎集体命运,因此,它不拒绝部族成员在萨满的引导下平等地进入到程式化活动中,相反它需要部族成员的广泛进入,以保证神的权威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这在许多连臂舞或其他集体舞蹈中可以见到,尤其是一些关于狩猎和游牧的萨满活动中,更是常常见到普通部族成员随萨满而舞的画面。4、从上文描述的萨满舞蹈岩画中可以看到,原始形态的萨满舞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舞者或者直接模仿生产动作、生产过程或生产对象,或者在生产生活空间中举行,即使是祭祀天、日等神灵,萨满舞蹈也通过面具、动作、偶像等使其与部落生产生活联系起来。
在谈到中国古代的面具时,周林生说:“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狩猎面具、图腾面具、傩仪面具、随葬面具、征战面具和百戏娱乐面具等六大类。若将面具的功能和形式延伸,还可以列出一类带有图腾意味或宗教色彩供奉面具(如‘吞口’)。如果将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面具收聚在一起,我们会看到人类怎样代代相袭并且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面孔,从蒙昧时代的荒山野岭走来,走过危机四伏、多灾多难的泥沼,直达到文明社会彼岸,……实质上,面具是深受压力、深感自卑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面目或属性,变‘我’为‘非我’的一种自卫、逃遁或进攻的手段,一种调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交际手段,一种纯精神的万能武器。” 如果将这里的面具说明来解释萨满舞蹈,无疑也是正确的。以萨满为中心的原始巫文化在蒙古族生活中应当如同在其他民族生活中一样,扮演着为这个民族提供一套世界结构模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精神寄托、为人们的多种需要提供着象征性的解释。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