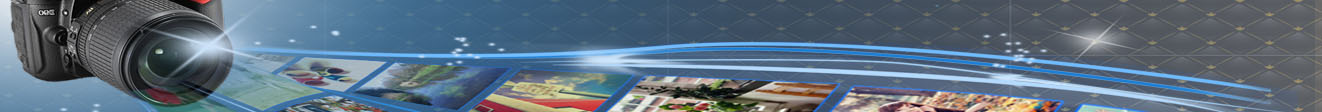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
不久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几次不同的重要场合,郑重提出了要重视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并提出在这个领域力求“创新”的要求,引起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受到极大鼓舞。一个国家、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终究离不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翅膀,否则就很难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未来的腾飞。
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它的任务是在理论和历史这两个层面上对音乐这门艺术进行多方位、多侧面的思考和探究。关于这门学科对于我国音乐文化整体发展的意义,我在十年前为一部音乐学文集撰写的一篇序言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一位伟大的先哲曾经高屋建瓶地讲过这样一句深刻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反杜林论》序言)这句话或许能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整体的高度发展,恐怕也是不能离开音乐理论思维的深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在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整体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对音乐文化的人文思考,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辉煌灿烂的成果。但当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随着音乐文化的蓬勃发展,对音乐文化的学术研究也有了迅速的发展,终于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音乐学“学科”时,由于种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在这方面却逐渐落在了后面。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作为近代意义上的“音乐学”学科才在第一代音乐学者王光祈、萧友梅等人的努力之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而它真正的发展则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在这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学科终于逐渐形成,它体现在:音乐学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的教学基地从草创到最后建立,一支专业性的学术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大规模的民族民间音乐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陆续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二十多年来,学科的建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各音乐院校中的音乐学专业陆续普遍建立并逐步成熟,一大批不同年龄段的音乐学工作者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上,音乐学子学科各自得到发展,各子学科的学会纷纷建立并有力地推动了音乐学术的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先后建立了诸如中外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声学和律学,以及近期已经起步的世界民族音乐、音乐声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等一系列子学科。这些子学科虽然在形成的历史、研究力量,以及研究的深度和成果方面尚不平衡,但一个学科体系的框架毕竟已经形成。这一切都已经为中国音乐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比较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音乐学,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已经登堂入室。
然而,对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来说,面前是一个艰辛的路程。应该承认,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中国的音乐学还很年轻。在这个学科的一些领域,我们同当代西方音乐学的最高成就相比,是有距离的。特别是在“创新”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考虑到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长远建设,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关注: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
一、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
音乐学这门学科本身是一个多门类的音乐知识系统,如前所述,其内部已经形成一个由一系列子学科诸如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技法理论等等构成的学科体系结构,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与此同时,音乐学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它又与本学科之外的一系列诸如哲学、史学、美学、艺术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数学、音响学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密切联系。
发源于西方的近代音乐学,其所以能从诸多人文学科中独立出来,并能最终形成由上述分门别类的诸多子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西方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科学领域长期形成的长于缜密分析的思维方式。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显露其自身的局限。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这种思维方式对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这种相对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被培根和洛克移用到哲学领域来以后的消极的一面:“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恩格斯的这些话,对我们当今推动和深化音乐学学科建设,很有启示。
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实现学术上的互补和相互渗透,意识到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这对我国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和深化,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与音乐学相关的一系列人文学科迅速发展、音乐学子学科相继形成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学术视野的狭窄特别表现在:音乐学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之间、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甚至子学科的内部相互疏离甚至隔绝的现象相当普遍。仅以我比较熟悉的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领域为例,音乐史学缺乏对整个当代中外史学理论的关注;在对中国的和西方的音乐历史研究之间缺乏相互沟通,甚至在中国的或西方的音乐历史研究中,将古代和近现代相互分割、忽视整体性研究,而相似的情况,在音乐美学领域中,在不同程度上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在其他子学科中恐怕也同样值得关注和审视。这种局面,对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和深化,显然是非常不利的。音乐学学科本身,特别是其一系列子学科本身,在性质上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和交叉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扩大自身的学术视野,忽视甚至放弃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缘和交叉点上寻找学术的生长点,那么,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恐怕是很难实现的。这是一件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需要长期扎实坚韧的探索,容不得半点草率,学术上没有任何省事的“捷径”可走。
在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时,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问题。这一向是个敏感的问题。我认为,一是要具有一种敢于大胆吸取人类思想领域中一切优秀成果的勇气和能容纳百川的宽阔心胸。我始终认为,一般说来一种深刻、严肃的学术成果都不大可能是全无价值、一无是处,其中总有某些值得我们思考甚至借鉴的东西。二是要在认真研读、真正弄清各种学说实质的前提下,保持一种冷静的分析、鉴别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作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不久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组织翻译力量与一家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十部西方音乐学界有定评的学术专著,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重温鲁迅先生杂文《拿来主义》中的一席话,至今仍是不无教益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二、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
如前所述,音乐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本来就是一门既从理论的、又从历史的层面对音乐文化整体进行多方位、多侧面研究的学科。这门学科的性质本身就要求我们不宜将理论和历史这两个层面机械地隔绝开来,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相互渗透,使我们的音乐学研究既有充分的理论深度,又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音乐学这门学科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
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那段话,更使我们意识到在音乐学研究中理论中思维的重要性,理论思维的贫乏恐怕是很难使我们登上这门学科的高峰的。以子学科音乐史学研究为例,它的任务当然是要发现、梳理、研究音乐发展的各种具体史实、事件,并在此基础上作清晰的整体描述,形成一个具体、完整的音乐历史景观。然而,这还不是音乐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音乐历史同整个人类历史一样,其发展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为使研究能从令人眼花缭乱的、曲折的种种事实和偶然现象中脱身,进入探索规律的层次,就只能依靠理论的、逻辑的思维。其实,民族音乐学研究也好,世界音乐研究也好,何尝不是如此?现象、事实的收集和罗列,难道就是这些学科的更高要求和最终目的吗?一位音乐史学家,如果完全同相关的哲学、史学理论、艺术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等理论层面疏离,甚至不屑一顾,那么,要使中国的音乐史学(不论是中史,还是外史)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重大的突破,恐怕是相当困难的。
音乐学既然是一种人文学科,它就不能不关注历史,强化自身的历史意识。马克思主义极端重视历史,认为历史有两种,即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且认为 “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并宣称:“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关于历史与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关系,他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必须重新研究全部。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