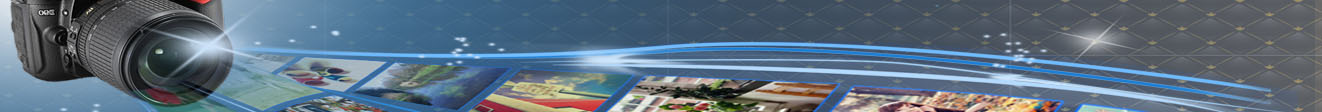音乐是有声的思想: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建设问题
应该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定义清晰的“中国音乐思想史”学科,然而却不能说没有音乐思想的研究,近代以来,有许多人对古代音乐思想发生过兴趣、产生出认识、写作过不少文章,甚至出版了某一方面如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专著,但无可怀疑的是,这些零星的研究和个别领域的成果并不能构成中国音乐思想之“历史”的全貌,也没有形成中国音乐思想史之“学科”的确立。所谓“史”者,必有事实之前后关系,有观念之内在理路,更有整体之精神面貌,中国音乐思想史必须展开中国人音乐观念的历史发展逻辑,必须说明中国人音乐思想的社会根源,必须描述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思想的精神特征。所谓“科”者,则一定要有专门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形成本学科的知识系统,创造特有之学科观念,包括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体系,中国音乐思想的基本架构,中国音乐思想的理论范式等。本文主要谈中国音乐思想范畴问题、音乐思想史学科架构问题和理论解释范式问题。中国音乐思想史所涉及的其他重要问题还不少,如中国音乐思想的史料学、中国音乐的构成观念、中国音乐观念的起源、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方法论等,这里都暂不言及。
(一)音乐思想史的范畴问题研究,是不能忽视的。范畴,是思想的刚性骨架,抽去概念或范畴的思想是没有内涵的思想,甚至不是思想。中国音乐思想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以及范畴体系,其间凝聚着中国人对音乐的深刻思考和切己体认,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这些范畴包括“一般范畴”(如“道”、“理”、“气”)、“特殊范畴”(如“声”、“音”、“乐”)、“抽象范畴”(如“雅”、“中”、“韵”)、“具体范畴”(如“燥”、“静”、“淡”)、“价值范畴”(如“美 ”、“善”、“和”)、“操作范畴”(如“脆”、“滑”、“溜”)等,每一个范畴类型当然不止这里例举的几个概念,而特别须指出的是,这些范畴类型共同形成了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体系,或者说思想骨架。中国音乐思想范畴显然还有自己独特的构成特点,如“德乐”与“乐德”这样的正反表达式,它们也都是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但其内涵不同,性质不同,前者相对具体,后者相对抽象;如“道”、“气”和“理”这样的超越表达式,它们含有远超出音乐思想的内容,既是音乐思想范畴,也不是音乐思想范畴,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高位范畴或元范畴,也即最基本的观念预设,离此则难以解释许多音乐文化现象。还有一些中国音乐思想特有的范畴,如“中”,既是具体范畴(如“中声”),也有抽象性质(如“中和”),有时暗含在方法论中而体现出“执其两端用其中”的原则(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道之用(“中庸”),即无过无不及;有时是对宇宙人生根本道理的体悟而表达为“中道”的哲学原理(如“非有非无、非无非有”),是用之道(“ 中论”),即不着边见,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强调持中。这样一些范畴类型不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吗?上述各式范畴类型,又都不是孤立的,它们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所谓道器圆成,情理无间,体用不二。范畴概念之间的联系,可能构成思想史的线索和结构。这样一些认识,是我们研究中国音乐思想最须注意的。梳理这些范畴,解释这些范畴,建立中国音乐思想的范畴体系,是音乐思想史的重要任务。
(二)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整体架构自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此尤其涉及到本学科的对象问题,没有确定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不能成立;当然,没有对一般中国思想史之认识以及一般思想史与音乐思想史之合理关系的建设,也难以有科学的音乐思想史,因为音乐思想史是一般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深一层说,若不能清晰地认识一般思想和音乐思想的发展逻辑、线索及其相互关系,则可能遮蔽思想历史的真实而昧于不明之中。
按学术界的通识,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发展史,思想者的思想是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思想文化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思想,是最为重要、最为恒久、最为精华的精神文化。思想是对现实的抽象,反映思想者的社会存在,是思想者的抽象存在方式。思想常常表达为概念、范畴以及诸概念和诸范畴间的有机联系,也常常潜藏在产生这些概念和范畴的方法论之中,还反映在思想者对现实的价值立场、应对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技巧里。以此度之,则中国音乐思想即是中国音乐现实的抽象,反映音乐思想者的社会存在,既有文化精英们的音乐理性,也民间艺人的音乐智慧,还有潜隐在中国音乐里的思想观念种子。
而什么是思想史,则常常取决于它把什么东西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思想史研究的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造成了智力或文化的进步”,广义的思想史被认为接近一种“追溯知识的社会学”(C.Brinton,1972),布林顿此意即是说,思想史应当以知识、智力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原因——思想和思想的社会土壤为研究对象,恰如英国学者梅尔茨所说,思想是隐蔽的世界,“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J.T.Merz,1923)。思想总是在现象的后面,但却是现象的原因。因此,仅仅把现象(所谓“人世表象”)当作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它把“结果”当成了“原因”,把对“原因”的思考篡改为对“结果”的观察。
当代中国思想史界对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不同观点。有人把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对象确定为理论化的历代精英的思想,因为他们最可能产生对现实的抽象,产生思想成果,他们有记录和传播思想的条件,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思想特色并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也许就是先贤所谓“大思想”,即:来自大多数人、影响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有人把思想史的对象扩大到一般民间生活和历代仪式礼俗,以为在这些行为化的文化中深含思想的种子,远的如国学大师钱穆,近的如新锐学者葛兆光,都有此主张。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1955)中不惟强调文化精英的思想之重要,同时也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不当专从书本文字语言论辩求,乃当于行为中求。中国传统思想乃包藏孕育于行为中,包藏孕育于广大群众之行为中,包藏孕育于往古相延之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之陈陈相因中。”在他看来,群众的行为是圣人思想的发生土壤。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1998)中,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对以往那些以精英和经典构成思想史,“描述了思想家的序列就等于描述了思想的历史”的现象颇表怀疑,因此倡言重写中国思想史。他认为:“如果思想史只是写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是一个悬浮在思想表层的历史,如果思想史只是一次次地重复确认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思想史就真的是一个‘层层积累’的历史了。”他进一步说,“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而存在……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持与此类似的观点者也属不少,有人指出:“生活,是思想史观念之源”,服食器用、礼俗祭仪、劳动生活等,都可以提炼出观念和思想;反对与此类似观点者同样也不少,有人认为,把思想和生活,把思想和思想的产生土壤混为一谈,不只是思想没有抽象性、思想不是思想的问题,甚至也颇带过去那种“工农兵哲学”的影子,思想固无所不在,但造成思想无所不在者却并非都是思想。
俾以为,对一般中国思想史研究现状的了解和认识,是研究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必备条件,因为,中国音乐思想史是一般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对中国思想史有全面的知识掌握和观念批判,则对中国音乐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同时中国音乐思想又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特殊性,揭示此一特殊性、描述此一特殊性、解释此一特殊性,是中国音乐思想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一般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可以根据音乐思想史的特殊性作特别的处理,一方面,历代文化精英的音乐思想仍然是音乐思想史的主体,历代经典记载的音乐思想还必然是音乐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理由是:这些思想正是所谓影响社会大多数人的、历久弥深、化为一般音乐观念的中国思想精华,正是钱穆所谓“大思想”,余英时所谓“大传统”,焉可忽视、焉可不研究?另一方面,按思想的一般定义和音乐思想的逻辑规定性,可以把古代礼俗祭仪中的音乐活动和民间音乐生活中暗藏的准音乐思想处理为中国音乐思想史的“前历史”,因为它还没有脱离“事实”、缺乏“抽象”、没有“观念化”,如古代音乐神话中包藏的音乐思想的种子、上古礼俗祭仪中音乐活动的文化结构后面所带有的观念因素。再一方面,还可以把中国音乐特有的操作方式、行为方式、音乐结构方式等现象中潜蕴着的思想观念种子,作为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潜历史”,所谓“潜”者,是说它有思想的某些性质,却没.......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