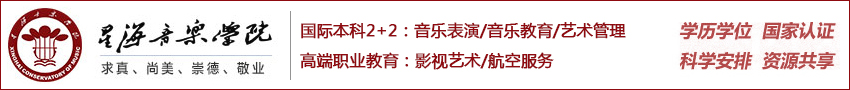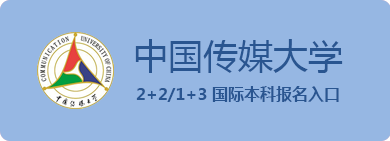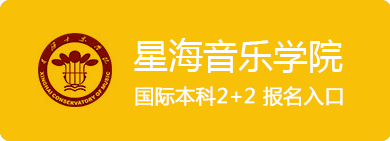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
【内容提要】音乐文化学的兴起,标志着民族音乐学研究视野的拓展。然而,与音乐文化学理论所阐释的研究内容与目标相比,其实际研究成果显得很不相称。不少文章难免因贪大求全不敷应对而处处捉襟见肘,理论上难有建树,关系上鲜有认识。我们只有将有限的个人精力关注于音乐文化学的某一特定领域,才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各个击破的“单项”对应研究仍然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音乐文化学研究。避开音乐本位研究或漠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成果,作为音乐文化学家只能说是先天不足或主客体错位的表现。
【关 键 词】音乐文化学/跨学科研究/研究方法/田野考察
【作者简介】蒲亨建,华南师大音乐教授。
近十年来,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中,呈现出由音乐本体的研究向更广领域拓展的态势,因此,“音乐文化学”理念的强调与运作受到特别的推崇与关注。此派包括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为口号进行研究之学人,均名异而实同,即强调研究音乐的文化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文化学的兴起,标志着民族音乐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也是民族音乐学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状况所由使然[1]。事实上,在当今的民族音乐学界,音乐文化学不仅被赋予了研究观念与领域上更为丰富的学科内涵,音乐本体的研究,虽然功力专深、家产雄厚,但仍有拓宽视野与领域的必要。因此,在音乐文化学的猎猎旗帜感召下,以此题进行研究的文论声势正劲。
然而,与音乐文化学理论所阐释的研究内容与目标相比,其实际研究成果显得很不相称,其实际运力显得非常虚弱——成果数量不少,却多呈泡沫状,蓬松绵软、入口无味。不少文章虽广泛涉猎民俗、语言、历史、社会、心理等学科知识与内容,摆开大兵团作战架势,八面出击,却难免因贪大求全、不敷应对而处处捉襟见肘:或理论现成照搬、论说粗浅飘浮,或描述家长里短、婆婆妈妈。这种理论上难有建树,关系上鲜有认识,现象描述不如基层音乐工作者来得实在,说起来声洪气壮却人人都能摸一把的“挠痒”式搞法,实际上也大大贬低了音乐文化学的声誉。
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固然与该学科所需要的“跨文化”的广博的知识要求、该学科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等客观条件有关,但十余年来国内一大批学者于此项研究的高投入与其成果事实的极不相称提醒我们,在自我宽慰的同时,也有必要对音乐文化学的研究现状做重新的审视与思考。
关于“音乐文化学”的含义,学者赵宋光认为是“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在这认识中,文化形态与文化内涵处于辨证的统一之中,客体方面(音乐作品,它的形态、手段、技术构成等)与主体方面(社会文化心理、社会群体的生产方式、语言、习俗、信仰,包括生产方式的地理特征,生产方式与语言习俗的历史源流,人口的迁徙等)是联结为整体的,是彼此不可分割而且能相互说明的”[2] (第233页)。“达到对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构成的全息描述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2] (第235页)
从以上音乐文化学的定义来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1. 局部关系上看,音乐文化学的研究,具有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联姻特征,如音乐本体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音乐本体与习俗的关系等等。但在这些“跨学科”的关系中,音乐占有核心地位。所谓音乐文化学,是指关于“音乐”的文化学。虽然它与其他文化因素“是彼此不可分割而且能相互说明的”,但从“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的认识目的出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音乐与其他诸因素的联系来更深入地阐释音乐,而非说明其他。因此,在这种“跨学科”的联姻关系中,诸因素的地位并非等量齐观,应有主次之分。
2. 从整体关系上看,音乐文化学是“对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构成的全息描述”。即音乐文化学包含了音乐与其他文化因素的全方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音乐文化学不能仅限于局部、个别的对应关系研究,而必须对音乐与其他诸文化因素的对应关系作全面的认识与把握,才能称之为完整或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文化学。
从以上理解出发,让我们来看一下我国有关音乐文化学的基本研究情况。
先看第一层含义。
首先必须对“跨学科”概念做一个说明。所谓“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提法,至少在音乐学界至今仍比较时髦。然而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早有其历史传统,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就音乐形态学这个所谓单一的技术性理论学科来说,我们对其通常描述的协调性、平衡对称性及其各种形态构成状态,无不与美学、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相关联。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舍弃了这些关联,音乐形态学将濒临失语,无从进行下去。
音乐形态学的这种“学科渗透”式的跨学科特征,反映了学科之间大量存在着的自然的、不刻意的浸润、沟通与交融现象,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和置换一样。这种沟通与交融,一般说来并不改变主体学科的属性。虽其与音乐社会学、音乐民俗学、音乐地理学等“学科横移”式特征分属不同的跨学科模式[3],但其间的“跨学科”基本内涵却是一致的。
因此,所谓“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其实质内容来说并不新鲜,新鲜之处在于其理性的观念描述。很多新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已有现象的发现与体认,并非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此看来,我们需确立一个前提观念:音乐形态学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在与其他文化因素进行“跨学科”展开研究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音乐本体的子系统特征作出深入认识,由此确立该研究对象丰富的可研究价值。试想,如果对所要阐释的音乐本体的形态特征都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认识,了解甚浅,那么,我们广泛求助外援、凭借他力的“文化学”手段用途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解释一些粗浅表层的音乐现象?牛刀难道只是用来杀鸡?
然而,我们的不少音乐文化学者往往视音乐本体研究蔑如,音乐本体意识极度淡化。在不少研究文章中,很少谈音乐本身,或只是将其视为“文化学”研究的陪衬材料。试想,当我们左寻右找了大量“文化学”佐证材料,蓄势待发,却面对空城,无处下手,岂非滑稽?看来,我们音乐学家进入文化学研究领域,不能忘却自己的独特身份,否则,若一味以文化学家的口吻说道,到头来恐怕不过是一个蹩脚的文化学家,弄不好还砸了自己的饭碗。
综观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音乐文化学的抽象方法论叙述外,在具体涉及实际音乐品种的文化学研究中,很少有音乐与文化之关联的具体、新鲜发现。对诸文化因素的描述,除了转述、照搬文化学领域的新老理论外,不外游记式的所见所闻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文化学论文,洋洋万言,几乎全是某一地区民俗活动的全程实录,从早上一直到夜晚,从人口数量、服饰穿戴、民俗风情、饮食起居、路途景观、地理特征、天气状况等等等等,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对音乐的穿插描述也多以对其表演过程、场景、曲目、曲例的介绍、罗列为通行套路,乍看来似乎音乐已与其他文化事象混融一体,仿佛“音乐文化”之理念在如此张罗经营中已昭然若揭,然而事实上我们除了看到诸文化事象五花八门的拼凑之外,鲜有其中内在关联的启发。这种平铺直叙、流水作业式的观察实在是有观无察,更遑论对其中关系有何新鲜的感受与见解了。说是写论文倒更像说故事,而故事的内容与形式又令人索然乏味——因为音乐文化学者毕竟缺乏说书者的专业兴趣与水平。既然是学术论文,就来不得嬉皮笑脸,于是,不时硬插一段半生不熟的说教,最后再生拉活扯一则令人费解的高论,就算拉倒,就算理论与实践两不误,文章的文化学品味似乎也就十足了。
关于上述诸文化背景因素的“说书式描述”,也许音乐文化学者另有一番思考,即音乐文化学研究必须首先以对音乐的诸文化背景因素做全面、细致的实际田野考察为研究条件,否则便是纸上谈兵。此话不谬。但作为音乐文化学者,难道不需要思考:你对该调查的目的与方法有何预设?这些调查材料用来做什么?如何对调查材料做出取舍?其中哪些材料蕴含着相关的音乐文化学信息?这些问题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而要让读者来猜测其中的“蒙娜丽莎笑意”,就未免有点故弄玄虚了。
显然,作为音乐文化学研究,即使是田野考察阶段,也应渗透音乐文化学的思考与见识。我们虽然不主张这种思考与见识以正襟危坐的面孔出现,但它可以自然地渗透于对调查材料的分析与认识之中。此外,材料的取舍也体现了作者的相关思考。否则,某些看起来亲躬亲历、不厌其烦、似乎是花了大工夫的调查取证,实际上倒反映了一种思维的懒惰。田野调查中的劳动价值及其获得信息量的大小不仅仅靠获得材料的数量来衡量,更取决于我们对五花八门材料中有价值信息的捕捉能力的锤炼与有关的“文化学”敏锐思考。这也是一个音乐文化学者不同于其他学者,更不同于芸芸众生的必备功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音乐文化学研究者的构成主体大多是从其他学科改行,或虽受过长期音乐教育但兴趣较为广泛或志在他域的音乐学者,这也是他们不愿涉猎音乐本体研究或显示出勉强态度的客观原因。他们可能不愿或不屑于与音乐形态学专门研究者联合攻关,因此,其文章中一旦涉及关键的有关音乐与文化的关联问题时,便要么撇开不顾,要么浮光掠影地应付。这样一来,出现拼凑与贴标签痕迹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看第二层含义。
由于从概念的整体内涵来说,音乐文化学是“对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构成的全息描述”,因此人们往往会认为局部关系的研究难以称为音乐文化学研究,或觉得即使具有音乐文化学的成分,也显得小家子气,于是形成研究中贪大求全的思想,试图将研究对象的有关音乐文化信息、材料尽可能统统摄入。在一些针对具体地区乐种的论文中,广泛涉猎社会文化心理、社会群体的生产方式、语言、习俗、信仰,包括生产方式的地理特征,生产方式与语言习俗的历史源流,人口的迁徙等文化学背景资料,似乎十分全面又显得眼界高远,却难免生拉硬扯、以空对空之嫌。实际上,其中很多材料难说有多少实在的具体针对性,除了引用一些大文化理论起兴压阵之外,这些背景因素中究竟哪些东西真正散发着浓郁的音乐文化气息,作者自主的感官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仅仅从文章对这些文化因素按部就班、购置家具式的拼贴搭配中便不难看出已经迹近机器人操作,音乐文化学所需要的“跨学科”丰富联想与发现功能已经大大萎缩了。
此外,我们还需认识到,音乐文化学是一个复合的整体概念,任何人不可能独立地进行该学科的全方位研究,只有群体或个人在各门子学科上的各个击破,才能推进音乐文化学的整体进程。亦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独作出“对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构成的全息描述”,只有各门子学科的整体合成才能完成这项使命。在比较文学界,关于此域已经提出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否有可能不满足于把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学术实践定位为个体行为,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学科的机制”[4]对音乐文化学,我们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从个人独立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将音乐文化学的整体内容当作研究对象。因为微观层面上:各个子学科均有其特殊“跨学科”对应关系,仅此一项研究已非易事;中观层面上:各个子学科之间是否有关系、关系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宏观层面上:我们任何个人不可能具备整个音乐文化学的丰富的知识建构,特别是在纵横扩展的现代知识结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只有将有限的个人精力专注于音乐文化学的某一特定领域,才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如音乐民俗学研究、音乐语言学研究、音乐地理学研究……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音乐文化学”研究,就其实质内容来说并不新鲜。这方面研究的实例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已经出现。
杨匡民先生的三音腔理论和湖北民歌五大色彩区的研究实践正是立足于音乐形态学的深入分析,并有机借鉴结合了地理学、方言声调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使其研究真正将音乐现象与相关文化背景的真实关系予以揭示,加以联系,从而既扩大了音乐研究的文化视野,又丝毫不失音乐学的主体地位。这是音乐文化学研究的成功实例:既看得见音乐,又联系到文化中的某些相关因子及其因果关系。这种从解决音乐问题的实际出发的研究,虽然没有高标文化学理论口号,其潜在的音乐文化学内涵已经昭然若揭。
蒲亨强在早期致力的苗族民歌研究方面提出的问题是:同样处于杂居状况,而且文化背景的很多因子都相同或相似,为何有些社区的苗歌至今仍保存着鲜明的本族特质,而另一些社区则丧失殆尽了呢?其文化学的相关思考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变化,往往并不决定于它本身,……看来必须从苗歌所根植的文化生态环境或民俗活动中去探幽析微”[5] (第231页)。他特别注意到:“(苗族)婚制的共同特征是,都没有越出“民族内部”的范围,这就使苗族进入地缘联系后,其血缘联系、民族联系并末被割断。因而苗族的民族意识在婚俗中体现最为强烈,很多杂居社区尽管其他民族文化已然汉化,但往往在婚俗上仍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婚俗活动成为一个维护民族纯洁性的坚强堡垒。平时可以说汉语,穿汉服,但在婚礼中则必须穿苗服,说苗语,唱苗歌。……所以通婚制非常突出地强化和维护民族特质,在婚俗中外来因素遭到排斥,所唱民歌都是本族古老曲调。难怪凡保持了“民族内婚制”苗区,其民歌必然具有本族特质,绝无例外”[5] (第233页)。最后得出结论:“婚俗是苗歌传承的重要生态环境”[5] (第235页)。
乔建中先生则着力从民间音乐与地理环境的对应关系方面做了音乐文化学的深入研究。在他的《甘肃、青海“花儿会”历史成因初探》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总结性论述:
(对花儿会址分布的密集性)我们特别注意到,92处歌会几乎都是在称为“山”“滩”“岩”“崖”“沟”“洞”“庙”“寺”“庵”的地方举行的。……这说明,“花儿会”的会址,不是名山,就是古刹,都离不开依山傍水、风景宜人之地。很明显人们既然出于憩息、娱乐的目的,必然要选择能真正让他们放情山水、以求慰藉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名山古刹正是可以让人们忘记尘世、寄情自然的理想之地。所以,说到底,会址的密集与借助于山水,其根源仍在人们在生产方式中产生的那种自发要求。……我们还注意到,类似的自然景现在“三临”地区特别多,这也是“花儿会”集中于这一带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往西,进入青海后,类似的景色逐渐减少,“花儿会”也呈稀疏的分布状态。总之,笔者以为,农村和山川景致为“花儿会”时空分布的高度密集提供了前提,并成为形成“花儿会”的主导因素[6] (第98、99页)。
此外,乔先生在《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一文中,从表层关系——环境对(民间音乐)体裁的“选择”、深层关系——地理因素所造成的民间音乐风格区、储存关系——作为保护传统文化自然屏障的地理环境等不同层面集中探讨了“作为文化现象的民间音乐在空间分布、风格形成、历史蟺变方面”与自然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关系,其“民间音乐的空间分布状态同它赖以形成、传播的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的“诸多联系”命题得以实在而深刻的揭示[6] (第264、269、276页)。
显然,上述各个击破的“单项”对应研究,仍然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音乐文化学研究;音乐文化学观念落实在具体研究上,也恐怕只能实打实的一个一个地来。否则,意欲将音乐文化学的诸多因素全盘涉猎、一网打尽,则难免隔靴搔痒、流于空谈。
综上所述,音乐文化学研究,首先必须树立音乐学家的本位意识。我们丝毫也不能忘记,我们不是文化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音乐学家,我们是以音乐学家的身份介入此项研究。我们所做的研究,不管应用什么材料、方法、观念、途径、手段,固然需要也应该能与其他文化构成要素“相互说明”,但其中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借助其他文化要素以阐释音乐本身之其然与所以然。所以,一个音乐文化学家,首先应该锤炼相应的音乐本行功底,或者与音乐本体研究的行家联起手来。避开音乐本体研究或漠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成果,对一个文化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来说,我们无话可说,但作为音乐文化学家,则只能说是先天不足或主客体错位的表现。如果一个音乐学家不能就音乐本身的问题提出专深见解,反倒将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拿过来作为其音乐学论著的主体内容津津乐道,那么我们究竟指望从他们的宏论中读到什么有见地的内容呢?充其量从中可获得一些转手的他学科信息吧。如果真是这样,即当一个音乐文化学家的著作中没有了音乐,或者只是附加一些浅显初级的音乐常态描述,那么我们直接选择文化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的书来读,岂不是更简单有效吗?
在音乐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系把握上,我们还应当锤炼敏锐地识别与发现其中蕴含的音乐文化信息的观察能力。也就是说,调查过程与材料的搜集中,应渗透研究者相应的文化学思考与选择,而不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这些材料与音乐的关系怎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应尽可能有所见识、有所抉择,而不能图省力,一股脑儿堆出来,搞成产品大批发,这样的商品只有不求质量的贪图便宜者才会买,缺乏创造性思维的产品也不可能得到买者的珍视。
最后,一个人的精力与知识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在音乐文化学研究领域,要求个人成为“对音乐文化的多层有机构成的全息描述”的全能者,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泛泛而谈,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设想让五人兼事五门学科,或者让五人各从事其中一门学科,可以想象,前五人知识的重复量必然远远大于后五人,其知识的总量必然远远低于后五人,因此,后者对学科知识发展的推动力势必更大。这是一个无需验证的简单结论。
【参考文献】
[1]蒲亨建. 中西音乐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J],北京:中国音乐,2002,(4):1-3.
[2]赵宋光. 音乐文化的分区各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A]. 赵宋光文集[C].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鲁枢元. 略论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J]. 北京:人文杂志,2004,(2):94-101.
[4]孙歌. 跨学科的悖论[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2003,(6):5-6.
[5]蒲亨强,苗族婚俗对苗歌特质之影响[A]. 寻千年楚声遗韵[C]. 成都:巴蜀书社,2005.
[6]乔建中. 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A].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C].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