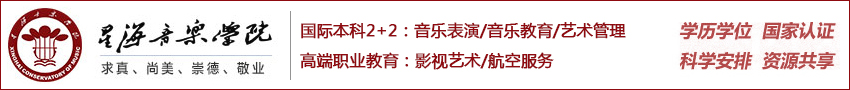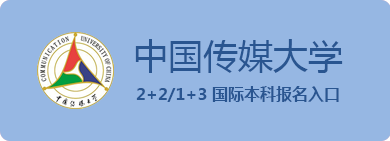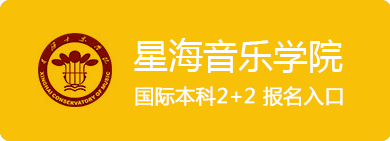对于民间乐舞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来源:未知 编辑:中国艺考网
对于民间乐舞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景颇族是一个典型的跨界民族③。据统计,景颇族人口约100万人,主要居住在缅甸克钦邦、掸邦,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印度北部阿萨姆邦等地区。我国的景颇族主要分布在德宏州各县,有景颇、载瓦、勒期、浪峨、波拉等五个支系,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称为景颇族。本文选择景颇族作为个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景颇族人民喜好音乐、舞蹈,千百年来创造了丰富的且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乐舞文化———目瑙纵歌,是景颇族传统文化的综合汇演;第二,景颇族一般居住在海拔1000———2000米的山区,与外来文化交往受到限制,歌舞文化及其功能相对原始、古朴,该个案具有代表性;第三,民族主体在境外④,对景颇族国家认同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构成潜在威胁,凸显了研究的现实意义;第四,与中国境内景颇族聚居区毗邻的缅甸克钦邦长期与政府军对峙,这种复杂的形势和跨界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应该引起关注。目瑙纵歌,源于景颇族“万物有灵”原始宗教的盛大祭典,是景颇族最大最具特色的祭祀活动,又是景颇族人民的集体歌舞活动。历史上,目瑙纵歌在不同支系有不同称谓:景颇支称为“目瑙”,载瓦支称为“纵歌”,浪峨支和博拉支统称为“占”,勒期支称“装”。虽称谓不同,但都有欢聚歌舞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景颇族各支系统一了舞蹈名称,称为“目瑙纵歌”。“目瑙”是景颇族景颇支语,“纵歌”是景颇族载瓦支语,意思都是“大家一起跳舞”[4](P133)。据景颇族创世史诗《目脑斋瓦》记载,人类最初是不会跳目瑙的,只有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一次,太阳王邀请地球万物去太阳宫参加“目瑙纵歌”盛会,而地球上只有鸟雀可以飞往太阳宫参加。盛会结束后,鸟雀们从太阳宫返回地球的途中休息时,看到黄果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很高兴,为分享果实,举行了地球上第一次鸟类“目瑙纵歌”盛会。景颇族的祖先看到了这场盛会,被百鸟热烈优美的歌舞所陶醉,于是模仿鸟雀的舞步舞姿,选择一块宽阔平坦的场地树立起“目瑙纵歌”标志———目瑙士栋,在正月中旬时举行了人间第一次“目瑙纵歌”盛会。据传说,人们学会跳“目瑙纵歌”后,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那以后,为表达不同意愿,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目瑙纵歌,不同场合的目瑙均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后,目瑙纵歌从一种原始宗教集体祭祀活动演变成为景颇族最大的传统节日,其传统宗教意义被淡化,转变为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表达社会进步、诉说人民幸福,祈愿民族得到外界认可的一次景颇族传统文化的综合汇演,在民族文化认同别异中展示出特殊的作用与价值。现代的目瑙纵歌,也不纯粹是“大家一起跳舞”的乐舞狂欢节,它仍然保持着宗教仪式的严肃性。据瑞丽市勐秀乡景颇族的大董萨⑤讲,“目瑙士栋”是目瑙纵歌的标志,以前每年都要重新立起,因此在目瑙举行前一个月,董萨们就要住进“木代房”⑥制作“目瑙士栋”,并做复杂的法事活动以祈求神鬼、祖先保佑活动顺利进行;如今大型目瑙纵歌场上的“目瑙士栋”则由钢筋混凝土铸造而成,可重复利用,不需要董萨提前一个月前往场地准备。但是按传统习俗,每次跳目瑙的前一天都离不开骠牛祭拜天地、祖先的活动,这一先期仪式“赋予了合乎民众期许的神性色彩,让这个活动得以在民众的心目中获得庄严的合理性,这会让参与者在认识上获得一种神圣性,从而让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的姿态积极参与进去”[5]。一切祭祀仪式结束后,目瑙纵歌的狂欢才能开始。届时,景颇族男女老幼身着民族盛装,男性手持景颇刀,女性持扇子、手绢、竹筒等日常生活中的器物,在领舞———瑙双带领下,沿着“目瑙士栋”上的路线,以腿部自然屈伸带动上身左右摆动,以腰、胯、腿的匀称移动和手势的协调配合为主要动作,向前行进。舞步随鼓点的变化而改变,上万人的队形进退有序、毫不紊乱,直至精力殆尽,人们几乎陷入疯狂状态……在铓锣稳定的节奏中,在景颇族激昂的歌声中,在万人统一的舞步中,景颇族人民完成了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
二、民间乐舞在云南跨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民间乐舞何以具备文化认同之功能呢?笔者认为是与其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显要的教育价值、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自身所具备的审美价值等因素分不开的。
1.民间乐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民间乐舞是由人民大众创造,反映创作主体生活、风俗、信仰等,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是一个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一般来讲,每个民族或某一地区的民间乐舞都具有典型的动律、体态、节奏、仪轨,在服饰、道具和伴奏乐器的选择上也都具有独特性,这一族群正是基于自身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区分“我”(我族)与“他”(异族),并以此来强化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舞蹈是目瑙纵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贯穿始终的舞蹈就是“以腿部自然屈伸带动上身左右摆动,向前行进”这么一个动作体态,并在整个活动中保持着同一个动律,只要所有人始终与自己前面的人保持动作一致,整个活动就能够在领舞者的带领下顺利进行。动作单一,易于掌握,但正因为没有高难度的技术要求,才使得男女老幼都能非常自如地参与到这一仪式活动中来,也因此文化认同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没有花哨的舞蹈技巧和多变的舞蹈动作,却使个体在单一节奏、动作的反复和不断变换的“走线图”所产生的“形式”中,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群体的力量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存在感。正是这种文化符号的独特魅力吸引了海内外景颇族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自己的节日”。可以说,每经历一场目瑙纵歌,景颇族民众的身心就将得到一次彻底洗礼,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就会得到一次强化和再建构。今天国内的目瑙纵歌节已经成为景颇族为主,德昂、傈僳、傣、汉等其他民族参与,面向国内外游客开放的狂欢节日。节日中各族文化在此聚合,各具特色又彼此尊重,争奇斗艳而不失体统,在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既显明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又展现出文化主体宽广博大的胸襟。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举办目瑙纵歌节,缅甸一方的克钦邦也时有代表参加,跨国境线而居的兄弟民族在芒市“中缅友谊馆”前宽阔的目瑙纵歌场上,穿着相同的民族服饰、打扮相似的民族装束、交流共同的民族语言,与广播里轮番播放的景颇族世代传颂的民族乐歌,共同营造出充满景颇族气息的空间氛围,人们在这种“视、听、动觉汇同”的空间中感受到来自共同的民族文化迸发的无形力量,强烈地激发了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
2.民间乐舞以鲜明的教育功能保障民族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所有生产生活经验、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禁忌等都只能依靠“言传身授”的方式进行代代承传,民间乐舞以“具有鲜活生命的人”为载体,成为记载历史、传播知识、教育后代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活的教材”。景颇族是一个迁徙民族,据《目瑙斋瓦》记载,景颇族祖先历经千辛万苦由“木拽省腊崩”⑦迁徙至现在的居住地,目瑙纵歌的“走线图”形象地反映了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它“以一种富有凝聚力的方式,向参与者们不断地陈述着民族自我的历史和轨迹”[5]。作为“教材”的目瑙纵歌,向后代子孙诉说着祖先迁徙的曲折与艰辛,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厚重感和对祖先的敬畏之情。云南是少数民族节日的聚宝盆,丰富的民族节日承载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通过节日既展示了民族风土人情,又以一种自觉的方式传播着民族文化。目瑙纵歌节就作为景颇族文化的集中展演,向参与者展示了各种具有景颇族个性的文化事项,如:族群起源———“走线图”表示民族迁徙的艰辛;宗教信仰———仪式前的祭祀活动表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民族禁忌———景颇族崇尚双数,目瑙纵歌一般跳双倍次数;民族服饰———女子上衣缀饰银泡、下身着红黑色筒裙、腿上带裹腿与男子佩戴景颇族长刀;民族饮食———“鬼鸡”与水酒;民族音乐———激昂、优美、朗朗上口的“喔然然”;民族舞蹈———目瑙纵歌本身;民族礼仪———送礼篮⑧;民族美术———目瑙士栋上的图案、民族服饰上的图案等等。这些文化事项是景颇族进行历史记忆,区分“自我”与“他者”的主要凭借物,构成了“景颇族之所以为景颇族,而不是其他民族”的主要文化判断依据。通过目瑙纵歌,参与者和欣赏者会有不同的心境:作为参与者的景颇族民众,产生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作为本族成员的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再一次得到强化;作为欣赏者的其他民族,则感受到来自“他者”文化强大的震撼力,因此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乐舞这种无需翻译、最不撒谎的“身体文化”,逾越了语言文字的障碍,将不同族属的人们联结到一起,在身体的对话中增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理解、尊重与认知,在同一的步伐中“舞蹈打破一切由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成的各种界限”[7](P1)。跨界少数民族与所在国家主体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平等享受着这种“身体文化”,而使心灵紧紧地绑在一起,民族认同向着更为高级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转变。
3.民间乐舞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参与文化认同
建构丰厚的民族资源、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云南省富饶的民间乐舞宝库。从没有语言文字的原始社会,乐舞就一直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节庆仪式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当人类朦胧地意识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莫不以运动为其主要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时,便衍生出用舞蹈驱邪除役、祈求平安,保证风调雨顺,迎接五谷丰登的观念和仪式。于是,舞蹈成为万能之神……在先民的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8](序言P4)。至今,乐舞仍然渗透到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乐舞之所以能被各类仪式所青睐,是与它的根本属性分不开的:其一,乐舞尤其舞蹈的载体是生命鲜活、富有情感的人体,这种以非语言文字的“肢体语言”为表达方式,以人的身体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凭借自身的节奏感和形式感对灵魂产生震撼的艺术品类,在沟通天地人神、动员族群成员、传播生产知识等各类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张力,这是其他艺术品类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其二,民间乐舞是一种参与性很强的集体活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人们可以在乐舞中感受到自己在群体中的真实存在,并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达到一种心灵的认同;其三,乐舞以身体律动为形式决定了它本身就是审美的艺术,具有自娱和娱人的功能,因此参与者乐于接受。作为舞蹈的“目瑙纵歌”最闪耀的文化魅力,不在于简单的舞蹈动作,而在于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和欣赏者在“视、听、动觉汇同”的空间氛围中感受到一种无形力量对灵魂的震撼。目瑙纵歌场上,由瑙双带领的群众队伍按照“目瑙士栋”上的图案,走出蕨菜纹、云雷纹等舞蹈队形,通过“走”,人们“始终在感受着、体验着、强化着、认同着先民们坚强不屈的意图和意志,从而让这个过程渐渐成为这个民族之本族魂魄的符号象征”[5]。也通过“走”这个单一重复的动态过程,民族神话中表达的民族迁徙史、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变成可以听得到、看得见,而且身体可以直接参与的真实场景———“借助诉诸听觉、视觉、触觉的多维符号活动,参与者们‘身临其境’,在相互之间完成情感的缔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6](P161)这种身体直接参与的动态性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
4.跨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与民间乐舞选择
综上所述,当民族文化成为自己生命的体验和肯定,当文化汇入血液、渗入骨髓,成为自己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舞蹈语言,便成为这个群体认同“自我”、区分“他者”的纽带。跨界民族也常常“基于自身文化的符号和历史记忆,通过‘自我’与‘他者’等区分类社会行为来强化身份认同”[3]。乐舞以一种平和而非对抗的方式,化解了跨界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性,使三者有效地统一到这个主题上来———国家统一与民族的延续。景颇族通过目瑙纵歌这一节日活动,传播发扬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他者”的我们参与这样的活动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相反还被景颇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智慧深深震撼而产生由衷的钦佩;作为“自我”的景颇族因为有“他者”的关注和热情参与而产生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又增强了民族融入世界的自信心。在这种没有语言隔阂的“身体对话”中,跨界民族“因文化认同而凝聚力增强,从而保证了自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环境中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3]。另外,跨界少数民族因为生活在不同国家,其文化艺术必然会受到所在国家主体民族或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产生“异我”成分,这种“异我”成分恰好削弱了境内外跨界民族血缘认同和宗教同宗所带来的“国家离心力”和“民族主义”等不安全因素的威胁。从目瑙纵歌的举办方式看,今天的目瑙纵歌节一般是由当地政府出资,在精心策划下举行的民族歌舞盛会,除了“目瑙纵歌”表演外,其他兄弟民族的音乐、舞蹈也会在节日的其他环节有所展现。俨然,目瑙纵歌节已发展成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地区旅游、增强地区影响力的一张文化名片,这种渴望民族发展、得到“他者”尊重的举措,已初见成效。结语目瑙纵歌是景颇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聚拢族群、传承文化、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能。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变迁的广度、深度和急剧程度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正是由于文化变迁的加剧,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弱势与强势、边缘与中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跨界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这一矛盾中的弱势和边缘。当遭遇来自异文化的强大压力时,“跨界民族中的精英分子会选择文化认同方式,以唤醒本族群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所赋予、联系的身份与权力”[3]。这一过程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其中包含了多重现代性因素,如民族国家施行各族平等的民族政策、着力解决民生重大关切等举措,都会对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民间乐舞的展演与传承来增强文化认同的做法,只能说是跨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现代建构中的一部分,而这种温和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其他手段难以企及的。因为,民间乐舞之于云南少数民族,是无比神圣的。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舞蹈
最新资讯
热门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