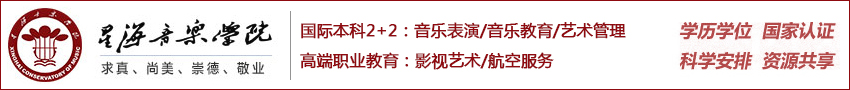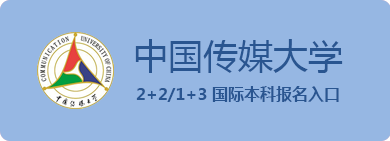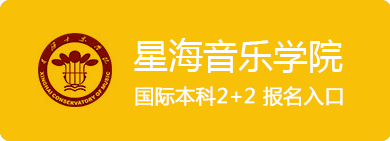谈舞蹈的气质
谈舞蹈的气质
中原汉代舞蹈的艺术特征1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空前统一的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大创造的时期,也是舞蹈艺术重大发展的时期。其时,中国与西方交通道路已开,南亚及中东文化亦渐流入中国。在新的时代精神激荡下,汉代的乐舞冲出了古乐舞的羁绊,民间舞蹈畅通地走进宫廷,百戏技艺空前兴盛,北方乐舞与南方乐舞亲密交融,汉族乐舞与外夷乐舞相互综合,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进入到第一个高峰时期。
在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中,中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始终处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文化积淀丰厚,经济富庶繁华,文人名流荟萃,社会娱乐活动风行,乐舞活动十分兴盛。中原汉代乐舞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原汉代文人张衡、傅毅、卞兰等所着的乐舞大赋,到定格在中原汉画像石砖、壁画中千姿百态的乐舞形象,作为“泱泱汉风”的标志,中原汉代舞蹈的舞容舞韵,不仅生动展现了汉代乐舞文化的灿烂繁盛,更显示出了独具一格、气度非凡的神采与风范。
一、艺、技相融,以舞为重
我国古代的“乐”是由诗、歌、曲、舞组成,那么究竟以何为骨干?古代舞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乐以舞为主”,回答的即是这一问题。魏名臣王朗上奏的表章中说:“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至周《大武》,皆太庙舞。乐,所以乐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表中所说的自《云门》至《大武》,包括了从黄帝中经尧、舜、禹、汤到周武王时的所谓六代乐,除《云门》、《大武》外,还有尧乐《咸池》、舜乐《大韶》、禹乐《大夏》、汤乐《大濩》。这些由于史书记载而传下名字来的最古老的雅乐,都主要是指舞蹈而言,所以王朗以此为论据,说明“凡音乐以舞为主”的观点。我国古代的舞论强调没有舞就没有整个乐,真正的乐是以舞的存在而完成的。“乐以舞为主”的观点,深刻积淀着音乐舞蹈起源发展的古老历史。
正是“乐以舞为主”,中原的舞蹈才由公元前2070年的夏王朝到公元前206年的汉代,以迅猛的速度获得了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与飞跃。尧、舜、禹时的纪功之舞,讲究的是仪式感,动作相对简单,偏重行列造型和场面气势。夏代末年夏桀时,宫廷乐舞讲究“以钜为美,以壮为观”,追求“淑诡殊瑰”、“奇伟猱戏”,以场面的宏大和动作的奇特怪诞满足感官刺激。殷商、西周时代的祭祀性舞蹈,因主要是娱鬼神,舞蹈的表现更侧重的是占卜、祭祀、祈祷的仪式性过程,动作的技艺性相对较弱。周代宫廷的舞以象功的典礼乐舞——“六代大舞”,属正统的雅乐舞,更讲究仪典内涵的丰富、顺序排列的规范、动作的中规中矩和场面的宏伟壮观。春秋战国“桑间濮上”的乐舞,生动、鲜活、情感率真,具有即兴性和群体性。而中原舞蹈真正进入那种在乎肢体的进退曲伸、离合变态,讲究舞姿、舞态、舞容、舞韵的精美精妙,从而由“以舞为主”到“以舞为重”的阶段是汉代。
以舞为重是指“舞艺”的分量之“重”,技巧含量之“重”。汉代的舞蹈将舞蹈的舞艺和杂技的技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舞”更复杂、更惊险、更高难,强化了舞蹈本体的审美特性,这是中国舞蹈的一个“质”的飞跃。
汉代的舞蹈多在音乐、歌舞、杂技、角抵幻术等百戏中演出,艺、技相融,以舞为重的特征也正来源于此。最典型的是《盘鼓舞》。《盘鼓舞》的主要特征是舞蹈与杂技相结合,舞蹈的特征是通过长袖的舞动,舞姿的“进退曲伸”得以体现;杂技的特点是通过在盘和鼓上的踏蹈腾跳得以表现。“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纚”,“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柔和、飘逸、高雅的舞蹈姿态与矫捷、迅猛、惊险的杂技腾跳相结合,舞蹈的柔韧美与杂技的力度感融为一体,技中有艺,艺中有技,刚柔相济,美感丰富,构成了中原汉代舞蹈艺术的一种重要特征。在宋元以后的戏曲舞蹈和民间舞蹈中,杂技和武术中的翻、滚、腾、转等特技和造型的成分广泛增加,亦大大丰富了舞蹈艺术的表现力。
在艺、技交融的基础上,汉代舞蹈“舞”的语汇和动律也得以丰富和强化,突出地表现在“舞袖”、“舞腰”、“舞足”三个方面。
以袖作舞是汉代舞蹈中常见的舞态,以飞扬的长袖作为舞动的主要手段,为汉代舞增添了蓬勃的生命力。长袖是舞者手臂的延长,舞者运用手臂的暗力将长袖横向甩过头部,在头顶划成一道弧形,另一臂反方向将长袖从体前甩过髀间,这两袖形成一个弧度很大的“S”形;身体的曲线随舞袖而动,同时形成一个弧度较小的“S”形;两个“S”型套在一起,形成一幅极其优美的造型,这一造型每每出现在中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中,如郑州新通桥出土的汉画像砖中的长袖舞即典型再现了这一动作造型特征。而《长袖舞》舞态的上扬、下甩、左绕、右缠,一道又一道飞动的弧线鼓荡着的是紧密的律法和热烈的旋动。这些多彩多姿的舞动,为汉代舞蹈纵横交错出一个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图1长袖舞)
“舞腰”在汉代舞蹈中表现的十分突出。腰是身躯的中心枢纽,灵活曲折的转动,既牵动上身,又牵动下肢。中原汉画像中的女乐舞伎均是腰肢纤巧,其舞腰的技巧更是袅娜多姿。有前俯后仰,有左折右倾,有扭腰出胯,有斜冲斜出……丰富多彩的舞腰大大增强了汉代舞蹈的曲线之美。张衡在《舞赋》中写道:“搦纤腰而互折,环倾倚兮低昂。”[注:参见《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里描写的是《盘鼓舞》的舞者纵腾蹈旋中,把那细而柔软的腰肢深深地弯折下去,时而又挺胸昂然卓立的动作姿态,优美而又惊险。傅毅在《舞赋》中对舞腰的描写更为传神:“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纡形赴远,漼似摧折。”[注:参见[汉]傅毅《舞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6页。]这里的舞者是突然腾跃到空中,两只脚一前一后落在两个鼓面上,前腿弓,后腿半跪,“累跪”于两面鼓上,紧接着上身后仰,背部与脚踵相摩,弯曲的腰肢移动般的状态像是遭受摧折,这种高超动作非舞腰纤巧者难于奏效。南阳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舞者那袅袅如束丝的细腰,左折右倾,带动着流畅若水波的长袖,尽展婀娜妩媚。另一幅南阳市西郊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踏拊起舞的舞者,两袖如长策,飘带曳地,大幅度倾驱折腰的舞者,亦展示出那种“纡形赴远,漼似摧折”的独特美韵。
舞足的特点主要显示在汉代《盘鼓舞》的表演中。汉代《盘鼓舞》的主要特点是踏盘踏鼓而舞,所以对于足的舞动特别强调。舞者从此鼓盘向彼鼓盘“浮腾”、“纵蹑”,不能有丝毫误差,蹈鼓时需目光集中,灵活敏锐,足足准确,足足响亮。尚且,不仅足的动作要漂亮,足的装饰也特别讲究,舞者所穿的“屣”(舞鞋),颜色是鲜艳醒目的朱红或彩色修饰。汉代记述舞蹈的文字中,对舞足的描述多能见到。张衡《西京赋》中有“振朱屣于盘樽”[注:参见[汉]张衡《西京赋》,引自《全后汉文》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64页。],卞兰《许昌宫赋》中有“振华足以却蹈”[注:参见[汉]卞兰《许昌宫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王粲《七释》中有“安翘足以徐击”[注:参见[汉]王粲《七释》,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63页。]。特别是卞兰文中讲述的“却蹈”,是个非常高难的动作,舞者需凭着眼睛的余光和内在的“心数”后退蹈鼓,这种如“反弹琵琶”般的非常规动作,溶入了杂技柔术的功夫,极大地调动了观者的审美期待。“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动而不乱,足相续而不并。”[注:参见[汉]卞兰《许昌宫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观众提着心劲看着舞者“却蹈”的动作将止又不止,一只脚相续着上蹈一面鼓,而不将双脚并踩在一个鼓盘,鼓声动而不乱,脚步续而不并。这一高难的舞艺处处显示着舞者技艺的精湛,美中有险,险中见美,带给人极大的审美愉悦。南阳县和南阳许阿瞿墓志画像石中的两幅《盘鼓舞》画像,舞者凝神注目“蹈足”的动态形象,即生动展现了《盘鼓舞》舞者的精彩神韵。
中原汉代舞蹈的艺术特征2
二、美丑相兼,刚柔相济
中原汉代舞蹈深邃的历史渊源和兼收并蓄、广纳博采的开放精神,不仅使得它的舞艺大进,同时舞蹈自身呈现出的美感也是多重的,亦美亦丑,亦刚亦柔,色彩丰富,风格多元,使舞蹈之美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审美层面。
在社会生活中,审美现象是丰富多样的,事物的各种审美特性,如美与丑,喜与悲,崇高与滑稽等,它们之间,互为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特殊条件下,甚至相互转化。所以,艺术创作上有时为了揭示美,为了创造独特的美感,往往要强调对立因素,以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使美表现得更加鲜明,这就是丑中见美的美学原则。在汉代的舞蹈中,人们已经聪明地意识到丑可以转化为美的原理,因而在许多优美的舞蹈画面中,有意地加入了丑的因素,美丑相兼,带给人独特的审美快感。
中原出土的汉画像中,有大量美丑兼溶的舞蹈画面,其表演的内容大都是《盘鼓舞》或《长袖舞》,或杂糅百戏技艺。以女伎为主舞,冠饰华艳,细腰如柳。丑角为伴舞,多袒胸露臂,戴面具。如南阳市七一乡沙岗店出土的画像石,女伎舞双袖踏盘向左作回望状;丑角弓步扬臂,憨态可掬,向右作回应态。南阳县出土的汉画像石,女伎纤腰侧拧,长袖曳地;丑角左手摇鼗鼓,右臂上耍一壶,动作俏皮。郑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画像镜,女伎扬臂双绕袖踏鼓作舞;丑角张臂挺肚,举足踏鼓作舞。荥阳河王村出土的汉乐舞彩绘陶楼壁画中,女伎黑衣、朱唇、细腰、红裳,以纵跳式踏盘,长袖飘扬;丑角赤上身,着红色短裤,在背后正伸出右臂撩逗主舞者。一幅幅美丑相兼的画面,从形象到动作色调,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主舞者美的形象与动作使人感觉优雅、端庄,伴舞者丑的形象与动作使人感觉滑稽、风趣。“美感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表现形式具有个体直觉性”,这种“直觉性是指感受的直接性、直观性或形象性”。[注:参见张涵主编《美学大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我们从一庄一谐的盘鼓舞的画像石上,直接、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了优雅端庄带给人的舒适感,滑稽、风趣带给人的快感,这种由“不协调”到对立的统一而产生的复合型的美感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它折射出汉民族独具一格的审美潜质与审美取向。(图4舞乐百戏)
汉代舞蹈美与丑的二重组合所生发的美感使人欢快欣喜,汉代舞蹈刚与柔的相映相衬所呈现的美感更使人激情愉悦。
从政治组织形式、法律、郡县制等方面来看,史学家认为是“汉承秦制”,而从文化来看,西汉因袭的主要是楚文化,尤其是从乐舞方面,楚声、楚舞统治了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祭祖先的“房中乐”原先本非楚声,这时也改变为楚声,《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注:参见《汉书?礼乐志》第四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3页。]其后,受百戏杂技的影响,舞蹈在一定程度上杂技化,原来楚舞飘逸纤巧的风格中增添了惊险的成分和刚劲的力度。可以说,中原汉代乐舞是黄河流域周文化与江淮流域楚文化的合流,北地风骨与南国姿彩的相交互映,由此,中原汉代乐舞形成了亦刚亦柔、刚柔相济的又一风格。
汉代舞蹈“刚”的风格表现为刚健浑厚、热烈奔放。首先,汉代的袖舞有这种风格。此类袖舞舞衣较短,一般长稍过膝,袖子的尺度也较短,表演时注重身姿的奔放和腰部的跨越腾跳,舞姿矫健而豪爽。另一种是对舞,如现藏于禹州市文化馆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镜上即有一组矫健活泼的男女对舞,男子宽衣大袖,女子紧衣窄袖,一前一后,追逐雀跃,欢快之情,溢于画外。汉代《建鼓舞》是以形体硕大的建鼓作为舞器表演的双人舞蹈,其舞姿“刚”的特点表现得尤为充分。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汉代空心砖《建鼓舞》图,二舞者是大跨步张臂舞袖,举桴击鼓,气势威武;郑州新通桥出土的西汉空心砖《建鼓舞》图,二舞者双飞叉起跳,跃身擂鼓,气氛热烈;南阳新店出土的鼓舞吹箫画像石,二舞者奔跑式飞身腾跃,双手举桴击鼓,舞姿奔放;郑州肥料社出土的西汉《建鼓舞》画像砖,二舞者弓箭步大探身举臂跃足,且鼓且舞,舞态洒脱。一幅幅气势飞动的画面,矫健奋发、气势昂扬,再现了《建鼓舞》雄浑的节奏感和力量的壮美。此外,汉代的《干戚舞》、《剑舞》、《鞞舞》均具有这种豪迈奔放的阳刚之气。
汉代舞蹈“柔”的风格表现为轻柔飘逸,纤巧婀娜。《长袖舞》、《盘鼓舞》、《巾舞》中舞袖、舞巾的飞扬飘洒,细腰、裙裾舞动中的婉转灵动,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在中原汉代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舞者挥动长袖、长巾腾跃翻转的舞态十分丰富,一道道飞动的线条抛向空际,如轻云出岫,如瀑布飞溅,如烟波飘渺,如飞虹悬天,妙不可言。长袖、长巾的扬举,裙裾、裙带的飘曳,配合肢体的折曲,充分体现了“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意境。正如汉代舞论文章所作的精彩描述那般:“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XC;%32%32]合并” [注:参见傅毅《舞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5页。];“体如游龙,袖如素蜺” [注:参见傅毅《舞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6页。];“忽飘飖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 [注:参见边让《章华台赋》,引自《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九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3页。]。这是一种奔逸、飘洒、流转、舒卷的飞动之美。
汉画中的舞女多细腰如蜂,体轻腰弱,这也是造成舞蹈纤巧婀娜之美的重要因素。前文我们谈到“舞腰”时讲到了丰富而高难的舞腰技巧。而正是那些前俯后仰、左折右倾的腰肢技巧,反映了汉代舞蹈娴婉轻盈、柔若杨柳的柔和美。《淮南子?修务训》描写盘鼓舞的“绕身若环”[注:参见《淮南子?修务训》,引自《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页。],其舞姿是向后下腰,手摩于地,其神韵如同仙女纤柔娇娜,如香草偃于秋风,形象地表现了舞腰的高难与腰肢的娟秀。中原出土的许多《盘鼓舞》画像砖石,舞者均是秀颈细腰,宽袖长裾,其腾跃雀跳的舞姿更是轻盈敏捷。如卞兰在《许昌宫赋》所描写:“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翾翾……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凫之迅疾,若祥龙之游天。” [注:参见卞兰《许昌宫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充分表现了汉代舞蹈“身轻若燕”和“体迅轻鸿”的艺术特点。其“拧腰出胯”、“纤腰互折”的舞姿,逶迤袅娜,变化万千,鲜明地表达出追魂摄魄的艺术感染力。济源桃花沟出土的汉代陶塑,舞者单腿独立,扬甩水袖,跨脚翘臀的姿态即灵动地展现了长袖舞的洒脱飘逸这一柔美的神韵(图6长袖舞)。
汉代的《盘鼓舞》虽轻柔飘逸,纤巧婀娜,但也有“刚”的一面,盘鼓之上的顿踏、腾跃,即是异常刚劲的动作。汉代的《建鼓舞》、《鞞舞》虽刚烈奔放,但也有“柔”的一面,当节奏徐缓时,鼓法轻柔,舞姿舒展,亦能呈现出抒情的神韵。
中原汉代舞蹈的艺术特征3
三、神秘奇谲,以悲为美
从中原汉代舞蹈所呈现出的艺术色彩、气度风范来看,还具有神秘奇谲,以悲为美的特点。
观看汉画像石砖中的汉代舞蹈,往往给人一种独特的神秘感。舞台的环境背景,常绘有云气、苍龙、瑞木、怪兽等。《总会仙倡》一类的节目,戏豹舞罴,苍龙白虎奏乐,仙人女娥?洪崖的表演动作,《鱼龙曼延》的神奇变化,《东海黄公》对白虎施行的厌胜术等都带有诡秘之气。从道具、舞器看,盘鼓舞的盘和鼓所象征的日月星辰的太空世界,《建鼓舞》由怪兽座承负,上面所装饰的流苏、羽葆、鹭鸟等,都富有神秘的含义。中原汉代舞蹈这种神秘奇谲的色彩与汉代人带有神秘色彩的意识有关。
这种意识首先是神仙思想。“神仙思想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汉人对宇宙人生的探求”。[注:参见费秉勋《中国舞蹈奇观》,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汉代的一些乐府诗,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对宇宙人生的悲剧性思考。“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 [注:参见《怨诗行》,引自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0页。]人们慨叹,在浩大的宇宙里和无始无终的时间中,人的生命太短暂了,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还是应该及时享受,及时行乐。故而道出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 [注:参见《西门行》,引自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9页。]。但是,这种即时行乐的选择并不能代替他们对死神的恐惧,他们把希望推到死后的享乐,所以,汉代的许多贵族墓葬里,都安排了最奢华的物质条件。洛阳偃师高龙乡辛村出土的汉代新莽墓壁画,生动地再现了这种对享乐生活的奢华追求。其中中室东西壁的四幅壁画最为典型:一幅为《庖厨图》,图上庖丁挽袖操刀切割食品,一旁束发着红色连衣长裙的侍女双膝跪地挽袖向盆里抓食物。两位男侍侧手持托板把食物端向墓主或宾客。二幅图为《六博宴饮图》,图上一老翁因酒量不胜醉态呕吐,并被人服侍,另二位老者正跪坐在席上聚精会神地六博,怀抱乐器的侍者随时准备为他们奏乐。三幅图为《宴饮舞乐图》,图中一男一女欢乐对舞,男者是赤身裸背的丑角舞,女者是典型的“翘袖折腰舞”。六位乐伎席地演奏,墓主和亲朋兴致观赏喝彩,好不乐乎。第四幅图为《宴饮图》,除几组开怀畅饮的对饮者外,被二位侍女搀扶的女墓主人醉态可掬的画面十分醒目。
虽然墓主人升天后的生活如此奢华逍遥,然而,到黄泉之下享乐毕竟是消极之举,于是他们苦思冥想盼长生。神仙思想发源于原始社会灵魂不死观念,由此推想“人是否可以长生”、“生命是否可以复生”等问题,以图寻找长生之术,再造生命长久。仙术在春秋战国时的神仙家手中产生,两汉时期是神仙思想大发展阶段,神仙道教孕育而成,“祭黄老君,求长生福” [注:参见[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69页。]的思想四方盛行。黄老道士、神仙方士和阴阳术日渐合流,“好道之人……故谓人能生毛羽,毛羽备具,能升天也。” [注:参见[汉]王充《论衡?道虚篇》,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汉代上层社会的贵族们时刻都梦想着羽化飞升,所以羽化成仙的观念在汉画像中多有反映。在西汉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中就出现了卜千秋夫妇升仙图等人首鸟身的形象,它象征着死者灵魂的超升,壁画中还出现了飞龙、飞虎等翼兽形象。东汉时羽化图像发展到顶点,许多出土的古墓画像中,身生毛羽,千岁不死,可御风而行的羽人形象比比皆是,大量的西王母仙府天境图、羽化升天图和祥禽瑞兽图反映了人们对羽化升仙崇拜的狂热激情。
汉代人带有神秘色彩的意识还体现在它的阴阳五行思想。汉代百戏“鱼龙曼延”中舍利变为比目鱼,再由比目鱼变成八丈长的黄龙,即《西京赋》里描写的“海鳞变而成龙,壮蜿蜿以蝹蝹” [注:参见[汉]张衡《西京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64页。],所表现的就是汉人的阴阳五行变化思想和祥瑞思想。
在汉代,神秘奇谲、色彩浓郁、极具神仙思想、阴阳五行变化思想的流行舞蹈是《盘鼓舞》。汉代舞蹈中与乐器相结合的舞蹈一般是手持乐器而舞,《盘鼓舞》为什么在盘、鼓上跳舞?盘和鼓各代表什么?费秉勋先生在其所着的《中国舞蹈奇观》中解开了这个谜:
盘鼓舞中积淀着复杂的古代宗教意识。这得首先说到鼓。鼓是雷神的法器,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观念。天上为什么打雷?传说是龙身人头的雷神敲击连鼓发出的声音。《论衡?雷虚篇》记载当时的画工时是这样画雷的:雷公画成力士的形貌,再画一连串的鼓,由雷公左手拉着连鼓,右手擂动鼓棰敲击。意思是天上隆隆的雷声,就是雷神扣击连鼓发出来的声音。……所以,盘鼓舞中的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击乐器,而是潜入着神秘含义的舞器。盘鼓舞中的鼓一般为两座,分别代表日、月。这固然因为太阳和满月都呈圆形,更因为日与月都和雷神有着关系:日神是乘坐雷车而行的;南阳画像石中有一雷神是捧鼓游向月宫的,雷与月也是关系密切的。这样,鼓在盘鼓舞中就取得了代表日月的资格。盘一般为七枚,象征北斗七星,实质上是太空中星座的代表。由鼓和盘作象征,组成了宗教幻想中的天体,舞人穿着罗縠舞衣抗袖舞于盘鼓间和盘鼓上,表示遨游于神仙世界。 [注:参见[汉]费秉勋《中国舞蹈奇观》,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14页。]
这就是《盘鼓舞》在汉代大行其道,大为盛行的原因所在。神秘作为一种美感,可使人产生一种深不可测的悬念和向往的感受,能够在审美中产生一股魔力,引领人们对宇宙、天地、人生进行思考、寻觅与探究。
汉代人的神仙思想,宿命意识不仅形成了汉代舞蹈浓郁的神秘色彩,也形成了汉代舞蹈以悲为美的审美习尚。汉代辞赋中所描写的乐舞,都是以悲为美,推崇的是尚悲的乐舞风,“其歌舞欣赏风尚是以悲怆为高” [注:参见费秉勋《中国舞蹈奇观》,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如枚乘《七发》写音乐,说做琴用的桐木,琴上的零件,都是在悲伤的环境中浸染出来的,依照当时人的唯心看法,这样的琴所奏之乐一定非常的悲怆。张衡在《南都赋》所描写七盘舞及演奏的舞曲,使“寡妇悲吟、鹍鸡哀伤,坐者凄欷,荡魂伤精” [注:参见张衡《南都赋》,引自《全上古两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68页。]。王充在《论衡》中将这种尚悲的审美风尚进行了理性的阐述:“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又说:“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易牙)和膳,肴无澹味。” [注:参见王充《论衡》,卷三十《自纪篇》,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里所讲的“美色”和“悲音”,是人们所共同需求的两个美感层面的极致,这是无可争议的,师旷一演奏乐曲,就是低回、悲哀的调子,使得人们欣赏这位音乐大师的艺术,就如吃易牙烹调出来的食羹一样妙味无比。
尚悲的乐舞风气使得秦汉时代的表现哀伤感情的舞蹈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汉武帝子燕王刘旦,企图夺帝位失败,临难前,在宴会上悲伤歌唱,其妻华容夫人随之扬袂起舞,撕裂人心的歌舞使在座之人无不泪下。汉高祖好楚声,《西京杂记》说:“(高)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 [注:参见《西京杂记》卷一,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高帝想废吕后所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所生的如意为太子,其打算破灭后,二人皆难过,刘邦唱楚歌、戚夫人则嘘唏流涕起楚舞。东汉末年,汉灵帝驾崩,董卓专权乱国,废少帝为弘农王,次年又让郎中令李儒强迫弘农王刘辨饮毒酒,在含辱自尽之时,按照时人的习惯和风气,刘辨与妻唐姬以及宫人一起举行了告别宴会。刘辨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唐姬也扬袖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兮从此乖,我茕独兮心中哀。” [注:参见《后汉书》卷十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450-451页。]两人的歌舞都是“泣下呜咽”,极度悲痛。舞也跳了,歌也唱了,刘辨才端起毒酒来一饮而尽。刘辨死时年仅18岁。由此可见,“绝命舞”是悲情歌舞的最高升华。
愈演愈烈的尚悲之风,至东汉末年有些竟达到病态程度。《续汉书》载,大将军梁商三月上巳日在洛水之滨祓禊,集合了倡优乐工,唱歌跳舞,而最后是以送葬歌《薤露》作结束的。《风俗通义》佚文记载了东汉时的洛阳,有不少嗜悲乐成癖的人连贺寿、娶媳妇之类的喜事也要唱送葬歌,跳丧葬舞,好不奇哉!
中原汉代舞蹈的艺术特征4
四、形神兼备,意境深邃
从中原汉画像石砖上展现出来的舞蹈形态神貌和文人乐舞赋中所阐述的舞蹈审美倾向,明确地显现出中原汉代舞蹈已实现了由强烈的教化品格向鲜明的艺术品格的历史嬗变。其舞蹈的艺术之美较重要的体现在形神兼备、意境深邃的特点之中。
宋代袁文《瓮牖闲评》说:“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 [注:参见袁文《瓮牖闲评》,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艺术创造中,形与神应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形离不开神,神也离不开形。形若离开了神,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神若没有了形象,就失去了物质的依托。所以,“形神兼备”是艺术创造中的高境界。汉代的宫廷女乐舞蹈即达到了这种境界。
1.形与神的和谐展现出了精妙的舞容舞韵。音乐、舞蹈是心灵的律动,抒情是古典舞的主要内容。舞蹈动作在时间过度上的或快或慢,或接或续,或起或落,在空间形象上的或大或小,或曲或伸,或长或短,都应与舞者所表达的情感和谐一致。有了动态性形象与情感表现的和谐一致,就可以舞出饱满的神采,舞出精妙的舞容舞韵。傅毅在《舞赋》中描写《盘鼓舞》有几句传神的句子:“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 [注:参见[汉]傅毅《舞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5页。]其传神的妙笔把舞蹈精妙的动态和神韵勾画出来了。一个舞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雍容富丽、从容不迫的风度,她的技巧那样娴熟,她的舞态那样传神。像是俯身,又像是仰望;像是来,又像是往;像是飞翔,又像步行;像是竦立,又像斜倾。这种若即若离、若动若静的舞容舞韵,不仅带给人“不可为象”的美感,更带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婀娜蹁跹的舞姿时而轻步曼舞像燕子伏巢,时而疾飞高翔像鹄鸟夜惊,时而逶迤似彩云旋转,时而蜿蜒似翔龙游天。丰姿美韵使“舞”的魔力获得了极致的发挥。
2.形与神的和谐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有无相生”、“阴阳调和”的思想。汉代文人的观舞赋给了我们以启示,凡舞蹈必须“千变万化,不可胜知” [注:参见[汉]卞兰《许昌宫赋》,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23页。],而千变万化的舞蹈动作又必须要有一个“宗”,即老子《道德经》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汉代舞蹈的欲进先退、欲伸先屈、或迟或速、乍止乍旋、千变万化、不可胜知的动态特征,即充分挥洒了“万变”与“一宗”;汉代舞蹈的柔中有刚、刚极生柔、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动律规则,即充分发挥了“阴阳调和”。在这一观点的辨析中,舞蹈史论学者彭松先生的阐释颇为精到,他说:“美在于动静之间,即使是在一刹那的静止——‘亮相’中,也要求神采飞动,形停而劲不停;另外,在不断地运动时,又要求如云泛碧空,在舒卷之中形象分明。讲究一中有万,万中有一。‘轶态横出,瑰姿谲起’,就是一中之万;‘摘齐行列,经营切儗’,就是万中之一。它们之中包孕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易,高下相倾’,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规律,贯串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美学法则。” [注:参见彭松《中国舞蹈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3页。]
3.形与神的和谐表现出深邃广阔的意境。意境说在传统美学中具有独特价值。“意境是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象,是意与境的契合。美学上的‘境’,是指突破了有形的象而产生的无限的象,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虚实结合的象。” [注:参见吴毓华《古代戏曲美学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版,第159页。]傅毅在《舞赋》中提出的“与志迁化”、“明诗表指”,是汉代舞蹈的另一美学成就。这里的“诗”和“志”可以归到“精神”的范畴,“舞”和“容”属于“象”的范畴,以有限的舞容表现无限的诗意,从而获得一种“象外之意”、“弦外之音”、“画外之旨”,这是对舞蹈艺术意境美的一个新的拓展。《舞赋》中所描绘的舞蹈,时而挺拔昂扬,有高山巍峨之势;时而婉转流畅,似流水荡荡之形。这里,形与神的和谐相融表现出了诗一般的美丽、深邃广阔的意境。这意境所产生的感染魅力,犹如“烟波渺漫,姿态横逸,揽之不得,挹之不尽” [注:参见王骥德《曲律》卷三,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32页。],令人卷魂动魄,心荡神移。
中原汉代舞蹈所显现出来的情操和艺术品味已达到气若浮云、志若秋霜、令观者叹为观止的境界。其形神兼备、容以表志、舞以明诗的特征,较完美地实现了舞蹈艺术娱乐与教化的双重功能,对中国传统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