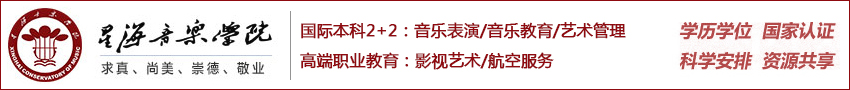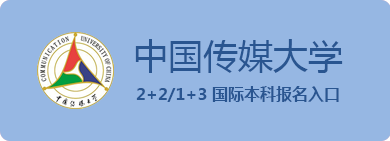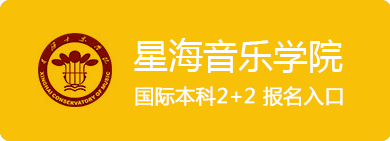民族歌剧表演艺术论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前十七年”间的民族歌剧,大都由民歌唱法或戏曲唱法的演员扮演剧中主人公,其声音清丽甜美、民族风格浓郁,声乐演唱的这种狭义戏剧性,主要体现在用板腔体结构和发展手法写成的大段成套唱腔的演唱中,体现在不同板式变化和速度的对比性处理中,体现在这些速度和板式变化所表现的人物丰富情感和心理层次的生动揭示中,而较少在音高(高低)、音质(厚薄)、音量(强弱)和音色(明暗)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对比。也就是说,民族歌剧声乐演唱中的狭义戏剧性,主要体现为唱段结构和段落间丰富层次的对比,而较为缺乏乐句或段落内部诸多微观表现元素间的对比,或者说这种对比尚未获得强烈的戏剧性张力。诸如此番实例有很多,比如我们完全可以从郭兰英演唱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倚门望》、王玉珍演唱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万馥香演唱的《五洲人民齐欢笑》、方晓天演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大风给我传个讯》、蔡培莹演唱的《凤凰岭上祝红军》以及蒋晓军演唱的《海风阵阵愁煞人》等精彩唱段中发现,这些经典性唱段在各自结构和全剧段落设置上具有较强的层次对比性,这些大段成套唱腔往往在剧中充当戏剧性的“形象代言”。但具体到声区的高低、音质的厚薄、音量的强弱和音色的明暗等,从这些诸多微观表现元素来看,其戏剧性的体现则不是那么强烈。当然,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受限于音乐创作。
作曲家在运用板腔体结构和以发展原则创作这一类大段成套唱腔时,主要着眼于段落之间对比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在乐句或段落内部,旋律线条的展开则相对平稳,情感性质也较为单纯,较少运用诸多微观表现元素间的对比来获得足够的戏剧性张力。其二是受限于演员本身的歌唱能力。由于民族歌剧的主人公多由民歌或戏曲演员扮演,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过美声唱法的训练和影响,但由发声法、共鸣位置等特点所决定,歌唱的声音品质较为单一,音域较窄,导致歌唱缺乏强烈对比。以上两点,都可以在老一辈歌剧表演艺术家早期所演唱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这一唱段中得以印证。从上述谱例不难见出,从乐句的开始,叙唱性的旋律线条、和声、织体的铺展相对平稳,较少采用诸多微观表现元素间的对比来获得足够的戏剧性张力,以突显情感上的单纯性为主。而且从对原始音像材料的视听辨析来说,不论是早期唱山西梆子出身的郭兰英,还是擅长东北民歌的乔佩娟,她们对该唱段的演绎尽管都风味独特、各具特色,但其在歌唱的声音品质和音域范围的戏剧性体现方面仍缺乏强烈的对比性。当然,即便作曲家在唱段的段落或乐句内部为演唱提供了诸多微观表现元素之间的强烈对比,有时也会因演员歌唱能力的局限而未能取得足够的戏剧性张力。这一点在歌剧《红珊瑚》中的经典唱段《海风阵阵愁煞人》的首句中便得以显见。在该唱段中,戏曲音乐中的板腔色彩极为浓郁,比如演员如何对由慢板、中板、快板、散板有机组合而成的叫板“海”字、喷口处理的“风”字、声音迂回处的“阵阵”二字,以及集全段于核心的“愁煞人”三个字的处理上等,均要在咬字、吐字、拖腔运用,及对节奏(如频繁的装饰音处理)、力度、速度、音色、情节起伏变化的处理上做到游刃有余,这种诸多微观表现元素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对歌剧演员歌唱能力和戏剧性表现的有力考验。除上述情况之外,还有一种类型是:不但在段落与段落之间有强烈的戏剧性对比,在段落或乐句内部的诸多微观表现元素之间也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对比。
歌剧《白毛女》中的经典唱段《恨似高山仇似海》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实例。作为该剧中最为出彩的唱段之一,如何通过咬字、吐字、气口、喷口及拖腔等方面的运用,以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情感尤为重要。如在“恨”“山”“海”“撑”“熬”等字,以及“冤魂不散我人不死”等唱词上的重音移位、重复等诸多方面的处理上均要十分考究。试比较20世纪50年代的演唱版本和80年代的演唱版本,虽然演唱的是同一个作品,80年代的新锐歌唱家将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与传统的民族民间唱法有力结合,其“通畅、集中、宽泛、有穿透力、质朴、柔美、亲切、亮神、传神”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便不言而喻。可见两者在声乐演唱的戏剧性表现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从中就可清晰地看出不同时期民族歌剧演员表现作品戏剧性的能力的强弱。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广大歌剧观众对西方歌剧和美声唱法比较陌生,因此在其审美情趣也不易被接受的情况下,对民族歌剧演员在声乐演唱表现力方面的特点非常熟悉且极为喜爱,这也是郭兰英、王玉珍、万馥香等人演唱的经典唱段如此万口传唱、不胫而走的时代原因。然而,随着西方歌剧的日益普及和我国专业美声唱法教学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我国民族歌剧演员在声乐演唱实践中对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程度的加深,我国的歌剧观众对声乐演唱戏剧性的期待值也随之提高。如今再来听《恨似高山仇似海》《海风阵阵愁煞人》当年的演唱版本,就会感到张力不足、戏剧性表现力欠缺。而王祖皆、张卓娅创作的《娘在那片云彩里》一经黄华丽演唱,其强烈的戏剧性便被充分而富有表现力地揭示出来。当然,上述诸多现象均是民族歌剧音乐创作、声乐演唱与观众审美三者在时代演进中互动的必然结果。因此,既不能用今天的戏剧性标准来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歌剧声乐演唱在揭示戏剧性方面的特点和成就,也不能固守在往日的模式里,无视时代、观众审美情趣的发展变化和当今民族歌剧演唱在揭示戏剧性方面的巨大进步。
歌剧作为“用音乐展开的戏剧”,戏剧性品格是其根本。对于歌剧艺术作品的表现是否深刻有力,关键还是要看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内容和形式所结合的完美程度。“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实现了‘歌剧的音乐性’‘音乐的戏剧性’,首先不在于是否一唱到底,是否用音乐铺满全剧或是否用了各种音乐手段和音乐形式,而是看这一切是否有效地为戏剧的展开服务,是否通过音乐手段推进了情节发展、解释了戏剧冲突、抒发了人物情感并在展开戏剧的过程中展示了音乐艺术自身的戏剧性魅力。”②由此可见,歌剧的戏剧性主要通过音乐、演员演唱和角色扮演来体现。而且,演员的演唱尤为重要,因为演员的演唱是对歌剧剧诗(唱词)的演绎,它能够直接实现音乐与语义性载体的结合来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戏剧冲突,进而完成音乐在戏曲中所担负的表现戏剧性的使命。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现“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就是歌剧演员舞台表演过程中声乐演唱的抒情性和戏剧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以为,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中声乐演唱的戏剧性,主要强调歌剧演员在对戏剧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通过舞台演唱来刻画人物形象,揭示其内心世界,表现剧中人物性格的对比与冲突,推动戏剧矛盾、情节的展开与发展,以及在描述戏剧情节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叙述性,在人物抒发情感时所具有的抒情性,在营造戏剧矛盾氛围、展开戏剧冲突时所具有的冲突性等。进言之,它不仅表现在歌剧演员在舞台上所采用的各种艺术手段上,也蕴含在其所要表达的主题和内容当中,还应该是对人物性格、行为及心理活动等二度创作过程的集中体现。因此,这便要求歌剧演员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完善的戏剧化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段的舞台表演体制。
总之,“作为音乐的戏剧”,歌剧舞台表演艺术注重的是戏剧主人公要以歌唱叙事,以自身特有的音乐表演的逻辑性与多重结构的完整性来彼此互补,从而表达出歌剧的戏剧性,并以此来激发受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情感。歌剧是音乐性质的“戏剧思维”,只有“歌唱”才是它最主要的情感表达手段。不论是何种歌剧表演艺术,以“歌”唱“剧”的戏剧性体现,将是其最高的信仰和忠实的灵魂。当然,囿于歌剧艺术家所追求的审美目标不同,其在创演实践方面的审美体现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歌剧演唱中的戏剧性将永远是不同时代、不同歌剧表演艺术家挥之不去的艺术情结,它将是歌剧演员二度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