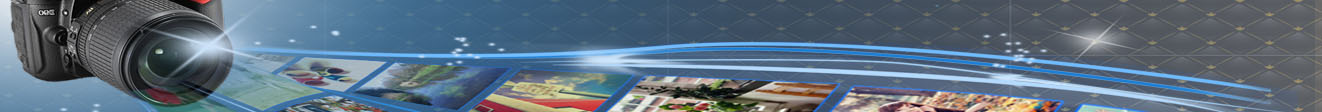徐悲鸿 借美术教育改造国民精神气质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也是伟大的思想者。徐悲鸿始终坚持“五四”启蒙思想,坚持写实主义,纳西而兴中,不只是对艺术技法的革新,更是国民精神气质的革命。徐悲鸿创作了《愚公移山》《徯我后》《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人物画巨章,奔腾不羁的潇潇骏马作品,花鸟走兽和山水画作。徐悲鸿还培养出大批学生,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美术教育是徐悲鸿奋斗一生的事业之一。他认为,一个画家,画得再好,成就再大,不过是自己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把美术教育发展起来,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就是国家的成就。人格品德之教育、广博知识之储备、美术课程体系之改革和学科设置之实践、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等,是笔者总结、理解的徐悲鸿美术教育的几个方面,正好合得上他崇尚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尊德性而道问学
人格品德、胸襟气魄的教育为徐悲鸿首重,这也是他和“五四”一代学者提倡的国民精神改造的首要任务。他一再鼓励学生“研究艺术,务须诚笃”“艺事至不易,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大丈夫立志第一,继往开来,吾辈之责,幸除积习,当仁不让,凡我通道,盍兴乎来”“最大之作家,多愿力最强之人,故能立大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在徐悲鸿看来,只有这样胸襟气魄的人,才有望建设新艺术,才有望实现国家的文艺复兴。在这样的砥砺奋进中,徐悲鸿从江南贫苦少年成长为画坛一代宗师,也激励着学生奋发精进。
除此品德胸襟,徐悲鸿还十分注重广博知识之储备。他博览群书,一生收藏大量中外书籍。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并注重“姊妹艺术”之聚合。姊妹艺术指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书法、园林等众艺术门类。徐悲鸿虽是画家,但强调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营养。这是现代艺术教育思想的体现,而不是单打一的传统作坊式教学理念。
写实主义教育主张
课程体系之改革和学科设置之实践,是徐悲鸿美术教育主张落实的关键。他的美术教育活动,辗转上海、南京、重庆、北京,前后执鞭约30余年。尤以中央大学为其重要阵地,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为其教育改革的重镇。
在中央大学,徐悲鸿开始主管西画组,得以在西画教学中实现自己的教学主张。在国画方面推行徐悲鸿主张,历来不易。徐悲鸿曾在1928年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力主改革,但孤掌难鸣。回到中央大学,他主持西画组成功后,向国画组推进就比在北平时容易多了。上任系主任后,徐悲鸿将西画组和国画组合并为绘画组,仔细安排、调整了课程设置,为推行写实主义教育主张奠定了学科基础平台。
这一教学思路又被1946年北上的徐悲鸿带到了国立北平艺专,他对艺专原有教学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国画学生和其他画科学生一样均先习素描,并把学制定为五年制。“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在第一二年共同修习素描,第三年分班……两年极严格之素描仅能达到观察描写造物之静态,而捕捉其动态,尚须以积久之功力,方克完成。此三年专科中,须学到十种动物,十种翎毛,十种花卉,十种树木以及界画……新中国画至少人物必具神情,山水须辩地域,而宗派门户,则在其次也……尊重先民之精神固善,但不需要乞灵于先民之骸骨也。”这是徐悲鸿1947年《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一文中的话语,是面对“三教授罢课”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后所写的近乎战斗的“迎战檄文”,其中所说的教学思路和课程体系安排,是为达成中国画改良,遵循“素描为一切造型之基础”的写实主义教学理念进行的教学改革。
徐悲鸿推行的写实主义,主张铲除中国画的流弊(哪怕是矫枉过正),提倡师法造化,灌注生气,使得阴柔遁世的古老中国画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也给美术教育带来了强劲春风。这种积极发展,是国民性的重新铸造,遥遥接续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亦是中国现代性启蒙精神的体现。徐悲鸿的亲授弟子艾中信在文章中说:“在20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中,他(徐悲鸿)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于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他们大多数兼教学和创作,推动并发展了中国的美术事业,首先是美术教育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属徐悲鸿教育体系核心命脉的素描却不完全是法国式的,尽管他是在法国最高美术学府学的素描,得安格尔一派的真传;他的素描也当然不是俄罗斯“契斯恰科夫教学法”的素描法,而是综合了中国画意味(融通白描)并融合“姊妹艺术”共同滋养的复合式素描。因此他对没有素描但生机无限的齐白石、张大千,对以线描传神的叶浅予,对并重素描、书法、雕塑的蒋兆和推崇有加,聘请他们加盟教学。这些都说明,徐悲鸿绘画实践和教育理念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对徐悲鸿素描的复合式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徐悲鸿的写实主义。他的写实主义宽约粗放,不固守单一,始终在寻找多方面的养料、“实验”和“突围”,有具象写实的自然主义性质,但对现实不是直接描摹而多间接写之,有古典主义的情怀,有印象主义的色彩,也绝不愿丢掉自己的浪漫天性。虽然有被素描、写实主义捆绑的局限性,并呈现出不小的矛盾性,也不免引发争议,却给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带来了不断拓展的空间。譬如1955年关于中国画教学的论争、1956年素描教学大辩论中,江丰、吴作人、艾中信、宗其香、李斛等坚持“素描为一切现实主义造型艺术的基础”,坚定地支持并继承了徐悲鸿的主张。而叶浅予等坚持“白描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一派,与同是白描派却不主张纯粹白描,而主张辅以西画造型结构的蒋兆和等,也不能说是对徐悲鸿的“背叛”,甚至可以说是对徐悲鸿主张的另一种坚持。
这也正说明,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尚处在探索实验的未完成状态,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其教学体系呈现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但当这一教育体系成为统领全国的主流话语,而被各大美术院校执行遵守的时候,这一体系已不再仅仅是徐悲鸿一家,而是与“延安学派”“苏派”三元交融,共同内化为影响至今的教育整体,成就斐然,不足亦在。这些都是徐悲鸿研究中诸多学者关注并着力探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家们反思往昔时,开始质疑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让徐悲鸿及其学派一肩挑起所有过失,有失偏颇。理性公允的学理态度很重要,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复杂问题进行综合探讨、理性思考,更好地建设推动今天中国美术的发展,促进东西方平等对话,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美术教育的使命。
师者风骨
徐悲鸿是职业画家、美术活动家、策展人和中外美术交流使者,平日里工作繁忙异常。但徐悲鸿只要在岗一天,就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发挥学生特长,开掘学生潜力。
对此,弟子们有许多亲切的回忆。在学生素朴真切的言说中,鲜活而没有“八股气”的,不“温吞水”、不因循守旧的,尊重学生个性、启发心智的,不仅悉心锻造学生扎实基本功而且努力培养他们创造力的美术教师形象,凸显在我们眼前。
徐悲鸿是一位心怀宽广的老师,他不怕学生超过自己,“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必然的。所以,他尽最大可能地找钱、出力、创造机会送学生出国深造。这些青年基本都学成归来,为写实主义、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徐悲鸿不仅悉心培养了大批在校学生,还无私帮助了许多上门求教、求访的画家和美术青年。一位遥远地区的小学生向他写信请教,他也亲笔回信。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长为著名画家的刘勃舒。
“画坛伯乐”、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等词语,不足以说明徐悲鸿助人所蕴含的深刻意义。这种超越公职、看似琐屑却普遍关怀的公共精神意识,当是评判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尺度。
(作者王文娟,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