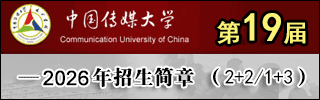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音乐史家持有不同史观,且各有其自己所遵循的研究原则。然而,多元时代不同音乐史观的多元并存,仍有某些普适性研究原则存在,这就是对象第一性原则、史料第一性原则、史实第一性原则、研究第一性原则、秉笔直书原则。所有史家必须共同恪守这些共同原则,本学科研究方有望跨越史观域限,走上科学健康的轨道。
关 键 词: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多元史观/普适性原则
作者简介:居其宏(1943~ ),男,河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13)。
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研究者有不同的音乐史观,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持有不同史观的音乐史家,各有其自己所遵循的研究原则,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们处于当今这个多元化时代,必须真诚承认并尊重不同历史观的多元并存,这是问题的一面;然而,音乐史研究毕竟不同于其他学科,更非街谈巷议、公婆各说各有理,因此必须切实注意问题的另一面,即:史家治史和写作,在处理主体与对象、基础与写作、史料与史实、研究和阐释等相互关系时,是否确实也有某些跨越史观域限并为所有史家必须严格遵循和恪守的、带普适性特点的共同研究原则存在?
对于此问,我的回答是充分肯定的。其理由如次。
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对象第一性原则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历来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说。考其原意,是想指出学科不同性质或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差别。
所谓“我注六经”者,是将六经(即对象)置于首位(即第一性),将主体(即“我”)置于次位(即第二性);其意是说,研究主体的学术使命在于真实揭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和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研究和阐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落中,这类研究路径以史学研究最具代表性。
所谓“六经注我”者则反之,是将主体置于第一性,对象置于第二性;其意是说,研究主体的学术使命在于阐发自身的学术理念和创新见解,而“我”(即研究主体)在分析、论证、阐发这些理念或见解时,“六经”(即对象)便成为“我”佐证和支撑其学理框架的基本材料。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落中,这类研究路径以哲学和美学研究最具代表性。
为史学研究独特性质所决定,史家在处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时,鲜明地强调“对象第一性”原则,将真实揭示历史对象的客观性质和本来面貌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是史学之所以是史学、之所以不同于人文社科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所在。
因此,作为历史学和中国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无论史家的历史观为何,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同样必须牢固确立并严格恪守“对象第一性”这个共同的研究原则,这是确保本学科的研究和写作之符合历史科学本质规定的灵魂所在。
我在《历史本体论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分为“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和“历史的观念性存在”两种,前者正是本文所说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生态;后者正是史家治史的学术成果,是时人和后人对实在性历史存在所做的解读,并在观念中加以重构、在研究和写作中予以再现的“历史”,也即以文字或其他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著述。
因此,史家的治史观念尽可多元,史学视野、史学写作风格亦有诸多不同,但有一条基本原则却是为所有史家理应共同尊奉的,这就是“对象第一性”原则。我们考量一位史家笔下某部历史著述之史学价值如何,最重要的不是评价其历史观以及从历史对象中提升出的结论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音乐艺术规律,而是看他所运用的史料史实、所梳理的历史脉络、所描画的历史图景、所构建的历史意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或者接近了历史的实在性存在,是否较为真切可靠地重现出实在性历史存在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其历史架构在整体上是否可被称之为“信史”等,都在史家对于“对象第一性”原则之是否认真恪守以及恪守程度之是否一以贯之中,必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所谓“音乐史”,通俗说来就是梳理音乐艺术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音乐创作和音乐艺术是史家的研究对象,我们一切形式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种种结论,都是由这个历史对象生发而来,并需回到历史对象中去,接受实在性历史存在的检验。这就要求史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音乐实践、音乐作品等放在第一位,反对任何脱离对象本来面貌去随意剪裁历史、曲解历史的主观主义倾向。
且以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①中关于陈洪《战时音乐》、陆华柏《所谓新音乐》的记写为例。汪著在未作扎实调研、仔细核查原文的情况下,仅凭第二手材料和当事一方之孤证,便对陈、陆二人的文章做了反面性记写和批判。到了新时期音乐界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论辩中,戴鹏海将此种治史作风称为“强史为我”②,也就是强令历史事实为“我”服务而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真相,根本违反了史学研究的“对象第一性”原则。
再以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③为例,它之所以受到国内同行的尖锐批评,从宏观层面看,当然是因为渗透在那个著名“三阶段论”中的历史观;从微观层面看,则在于著者对于历史对象感性体察和理性认知的失真。举一个实例——著者断言: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不是真正的中国音乐”,促成他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的感性依据有两条:其一是将作品的音调素材来源错误地判定为“黄梅戏唱腔”;其二是著者在作品中只听到“以欧洲十八、十九世纪音乐作品的表达能力为蓝本”④的欧洲和声、欧洲对位、欧洲曲式,而对弥漫整个作品的中国旋律、中国节奏、中国音色以及蕴含其中的中国精神、中国风韵、中国气象,则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类似的感性误读还表现在他对钢琴曲《牧童短笛》和《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所做的片面的本体分析中;他之所以由此为据从中得出“不是真正的中国音乐”这个错误判断,进而上升到整体结论层面、推导出所谓“三阶段论”,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这种建立在“只取其一,不取其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治史作风,以及由此派生而来的对于历史真相、音乐作品的严重曲解或误读,再典型不过地违反了“对象第一性”原则,用想当然的主观臆断代替了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科学分析和研究,扭曲了历史对象的真实面貌。我们新一代学人若要想切实避免类似错误,就一定要牢牢树立并以一贯之地实践“对象第一性”原则,不可有丝毫动摇。
基础与研究的关系:史料第一性原则
不论史家持有怎样的历史观,无一不承认:史料是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基础材料。衡量史家治史功夫之深浅,首先看其手中掌握史料的丰歉;衡量历史研究和写作成果大厦之是否坚固牢靠,首先看其史料基础之是否丰厚扎实。
因此,史家在处理基础和研究的相互关系上,必须严格恪守“史料第一性”原则。
确立“史料第一性”原则,从史家和音乐史写作的过程看,其目的是解决历史写作的研究基础问题;从音乐史研究学术继承性的角度看,是处理自身研究与前人相关研究的相互关系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确立“史料第一性”原则,都是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写作必须共同恪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所谓“研究基础”问题,也就是史家的研究是从什么基点上出发的?在历史研究和成果写作过程中,我们选定了一个论题或确定了一个研究对象之后,当务之急是什么?当然是收集史料,把与本课题有关的音响史料、乐谱史料、文物实物史料、文献史料悉数收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做“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史料”,特别是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史料,从而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丰厚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历史研究和史书写作来说,就是充分强调史料收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
所谓“学术继承性”问题,指的是:史家在选定论题、确定对象之后,有一项史料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即在这个选题或对象的范围和相关论域内,前人曾经做过哪些研究?发表过哪些文论和著作?其研究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哪些创造性的建树?要了解、回答这些对于我们的研究和写作极端重要的问题,就必须查阅、收集与此相关的学术文献和史料。只有把我们的选题和研究充分建立在这个学术继承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们的选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科学的定位,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和写作择定自己学术创新的突破口。如果忽视了这个学术继承性,忽视了这方面的史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我们的选题就必然失去方位感,陷入盲目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前人在这个论域内曾经做过什么、写过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取得哪些成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作,很可能变成一场无用功——我们最后拿出的成果、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前人写过的和说过的。
如今在各音乐艺术院校硕士、博士学位教学中,为何要特别重视学位论文“选题论证”和“研究资料综述”这两个环节?它们的真正意义和功能,就是防止学生在学位论文写作的选题阶段处理基础与研究、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时,因史料收集工作不到家、史料分析功夫不到位,导致研究基础羸弱而每每发生对象定位重复陈旧、选题了无新意之类情形。
当然,在研究和写作中实行“史料第一性”原则,是一项笨功夫,更是一项硬功夫,说易而行难。史家唯有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方能真正做到对相关史料的详细占有。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想要偷懒耍滑者,最后受惩罚的必是自己——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选题阶段若未发现上述弊端并及时改弦更张,将它留到中期检查或预答辩阶段才被导师们发现,届时再想亡羊补牢,岂不悔之晚矣!
因此,不光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的硕士、博士学位教学中,即便对于本学科不同史观的成熟史家而言,同样必须牢牢地树立“史料第一性”的原则。非如此,便不能有效防止历史研究和史书写作中急功近利、仓促上马、低水平重复等不良现象;非如此,便不能切实遏制抄袭、剽窃等腐败学风的蔓延。
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实第一性原则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史料和史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所有已被发现或未被发现的史实都是确凿无疑的史料,但并非所有已被掌握或未被掌握的史料都能被证明是铁一般的史实。
音乐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史料中存有大量暧昧难解、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因此,史料的考证和辨伪便成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环节。只有经过严格考证并获得相关材料强力支撑或相互印证的史料才成为史实。
那么,“史料第一性”和“史实第一性”的关系到底如何?
从研究路径上看,“史料第一性”原则是史家进入研究过程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它强调的是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基础材料之是否扎实、是否丰厚问题;而“史实第一性”原则是史家对已有材料进行反复考证和史学分析,它强调的是史料之是否真实、是否可信问题。
因此,“史料第一性”原则是贯彻“史实第一性”原则的材料基础,没有丰厚、扎实的史料基础做支撑,后者的考证和辨伪工作便失去了对象;“史实第一性”原则贯彻是“史料第一性”原则的目的,未经严格考证和辨伪的史料,即便再多再丰厚,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依然是存疑的,也就减弱了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史学价值。
所以说,在音乐史研究和音乐史著述写作中,“史料第一性”和“史实第一性”这两个原则都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
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例如唯物史观、实证主义、考据派、索隐派等等。但无论它们的历史哲学和方法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史实第一性”原则。试问: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学流派,会从根本上撼动、否认乃至反对“史实第一性”原则么?
汉代司马迁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但他在史学巨著《史记》中所倡导、施行并成为中华史学传统伟大精神支柱的“秉笔直书”原则,其核心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史实第一性”原则;在20世纪50~60年代曾被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为“唯心史观”的所谓“考据派”和“索隐派”,它们所坚持和强调的,也正是这个“史实第一性”原则;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实证”,同样强调回到史实本身,同样也坚持“史实第一性”原则。
因此,“史实第一性”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的史学研究和写作,便不成其为严肃的历史科学,因为它的记叙和结论,经不住史实的检验。
特别是从事当代音乐史研究,在接近、认识和把握史实方面较之古代史同行有着更多的便利和更直接的途径,但新音乐史家对史实的认识和掌握依然是永无止境的,依然要把一步步接近史实、力争把握史实的主要脉络和基本面貌放在第一位,将坚持“史实第一性”原则当作一切研究的起点和基本功。只有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接近史实,认真地倾听作品、掌握事实,尽可能地了解和熟悉自己所记叙的人物、事件的真实面貌,以夯实我们的史实基础。
因此,必须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来认识“史实第一性”原则,特别是那些公开声言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历史哲学的学者,更要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贯彻始终。我本人对唯物史观了解不多,从事史学研究的根底也浅,但我服膺这个历史哲学,愿在研究、写作和教学中努力贯彻“史实第一性”原则。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表白,是为了与前辈及同行们共同避免“言不行、行不果”的学风,一起把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境界。
最不该原谅的,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明明对当时所做的那些事、所说的那些话、所开的那些会、所发的那些文件、所写的那些文章,知根知底、一清二楚,到了后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则开始打起了小九九,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不说,还要利用年轻学子的幼稚、浮躁及其他不健康心态,提供伪证,制造假象,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得真假难辨,企图在搅浑水之余,逃脱历史对其灵魂的追问。然而,史实就是史实,史料就是史料,史料可以造假,史实却是铁一般的存在,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何涂抹历史真相的企图和做法,在无情史实面前,迟早要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
从方法论层面看,“史实第一性”原则同时也是音乐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虽然,对于特定的研究者来说,即便终其一生也很难穷尽一个历史时代的全部真相,但必须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专题上占有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和史实,对于同样是“史实”的一系列对象,例如具体的音乐作品研究、音乐家研究、音乐思潮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对乐谱、音响、图片、演出节目单,当时的会议简报、文件、发言记录及理论批评文本等的竭泽而渔,研究者必须直接面对这些史实载体,亲耳聆听它们,仔细研读它们,通过与这些史实的“零距离接触”来亲身感受当年的时代风云及其变幻,由此才能获得对这部分历史史实的真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某一作品、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或某一思潮争鸣的梳理、认识、评价和判断,才是有根有据的和言之成理的,因为我们唯有对与历史对象有关的所有重要史实、史料已经悉数占有并经过一番分析、体验、研究和消化过程,才能在历史写作过程中保持科学冷静的态度,使我们的历史描述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真相,并在扬抑褒贬之际、遣词用语之间,把握分寸感,驾驭张弛度,美其当美,刺其当刺,而不至于发生背离史实、扭曲真相之类根本性错误,也可有效避免较明显的美刺无节、褒贬失度等偏颇。
在史学研究方法论中实行“史实第一性”原则,看起来很费事也很笨拙,但这种方法非常实用也非常有效。可惜,现在有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只看其费事的一面而无视其有效的一面,总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既不费事又很有效的方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是否确有如此神奇的方法存在,倒是因无视“史实第一性”方法而走入歧途的例子见过不少。
例如,一些学者常常分不清史料与史实的联系和区别,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误把史料当史实,以为尽可能地占有史料,我们的研究也就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了。其实不然。你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作品评论,仅仅把当时的批评文本当作论文的主要史料和立论依据来加以引述和评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其实是颠倒了史实和史料的关系。因为,这些当时的批评文本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而且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即便作者对这些文献的搜集已然“竭泽而渔”,也无法改变它们的史料性质。真正的史实是这些被评论的音乐作品本身和隐藏在这些作品及其评论后面的深层文化环境。因此,只有千方百计地将当时的音乐作品的乐谱和音响找来认真听一听、仔细分析一番,联系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对照当时的评论文本来加以综合梳理、研究和评价,才有可能真正接近史实本相。
再如,最近有一篇博士论文,在谈到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音乐界对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时说,吕骥同志没有组织《人民音乐》开展这个讨论,而且批评编辑部将贺绿汀与胡风相联系的做法。作者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对伍雍谊同志的采访笔录。⑤且不说伍雍谊同志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单就作者仅仅根据一个当事人的回忆就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做出这一结论的做法本身而言,显然在处理史实与史料的关系上太轻率了。因为,伍雍谊只是当事人的一方,是否应该听一听当事人另一方提供的说法,以便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再说,当事各方的回忆都是史料而非史实,都要接受史实的严格检验;严肃的治史态度还应该遍寻当时的原始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及简报、内部讲话记录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甄别和辨伪,作者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接近于史实的原貌。这个例子也说明,新一辈史学研究者之缺乏科学史观和方法的训练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史实第一性”原则对他们几乎是全然陌生的。因此,关键是他们的导师首先要牢固树立“史实第一性”观念和方法,乃是当前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当务之急。
因此,当代人写当代史,一定要在史实和史料方面狠下苦功;只有把史实和史料的基础夯实,我们写出的史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史实,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同历史研究及写作一样,历史解读也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实际上,一种历史写作成果的出炉,也就提供了一种历史解读的范式和方法。对于同一段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不仅允许而且极为正常,因为它符合人类对历史现象和历史本质的认识论规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伟大史家敢于说他已经把某一历史时代的所有史实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这样说,并不是在提倡“不可知论”或所谓“历史解读相对论”。历史研究和历史解读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和判断的标准巍然耸立于其间,这就是史实,就是历史真相本身。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其奥秘正在于“史实唯一”的伟力和魅力之中。只要我们在历史解读中坚持“史实第一性”这个标准,把它确立为历史解读的唯一依据,任何视角和方法的历史解读都无法逃脱它的无情检验。某一种解读之是否可信、之能否成立,只要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用相关史实和史料进行综合考察与检验便可真相大白;即便我们这一辈学者都死绝了,即便某一历史谜团直到今天仍是难以拆解的悬案,后世学者或后世的后世学者也一定会借助不断发现的新史实和新史料而给出公正和科学的评判。所以,从事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们切莫忘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句话,我们的成果、我们学生的成果,一旦发表出来,就是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存在,其立论可信度和学术含量如何,都要接受历史和史实的检验,是存不得任何侥幸心理的。
总之,明确史实和史料的联系与区别及史料辨伪的重要性,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牢固确立“史实第一性”原则,响亮地提出“回到史实中去”的口号,使得“史实第一性”原则成为历史哲学的核心、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历史解读的唯一依据。
研究和阐释的关系:研究第一性原则
史家研究历史,其目的当然为了对历史对象做出自己的阐释;为了使这种历史阐释成为可能,并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就必须对历史对象做起码的研究。
因此,在历史研究与历史阐释的关系上,必须坚持“研究第一性”原则。
就一般规律说,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家掌握对象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历史阐释和它的最终成果——音乐史著述是这个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体现。没有对历史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精心研究,就无法进入阐释和写作过程。
同样的,史家对音乐史对象的研究,必然体现为音乐史著述,这就进入了历史阐释学的界域。无研究的历史阐释是“客里空”,无异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米之炊;无阐释形态的历史研究是既不开花也不结果的树,产生不了任何实际价值,因为它没有把研究成果外化为有物质载体的形式,并被学界同行共享,成为公共史学财富的一部分。
史家在处理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阐释的相互关系时,切实恪守“研究第一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围绕历史对象本身所展开的研究。
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实在性历史存在四要素:历史创造的背景——场,即能够影响某一段历史之所以发生、发展直至结束的宏观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和氛围;历史创造的主体——人,即在特定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下活动着的音乐家、听众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创造的过程——事,亦即历史人物历史创造活动的具体事件,及其发端、发展、结局的具体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历史创造的成果——物,亦即历史人物之历史创造活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及其多样化的显现实体。上述之场、人、事、物四要素,便是本文所说的“历史对象本身”。史家只有对这四要素逐一进行全面、深入、立体化的考察分析和综合研究,由此获得丰富的历史质感,才能让历史对象在史家的头脑中鲜活起来,逐渐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建构起一幅整体性的历史长卷。在此前提之下,史家进入阐释和写作过程时,方能做到成竹在胸,下笔得心应手。
其次是围绕与历史对象相关的史料和史实展开研究。
鉴于已经搜集到手的各种史料和史实带有零散性和个别性,并在不同意义上与史家研究的历史对象相关,因此,史家在进入阐释过程之前,必须下苦功夫仔细研读它们,务须切实理解和掌握其中所运载的各种历史信息,更要对大量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严格考证以辨别其真伪,评估这些史料和史实对于论题研究的支撑意义和使用价值,以此为据构建论题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史料史实系统,并分别确定具体史料史实在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使用方式。非如此便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使用史料史实,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非如此便不能切实防止把孤证和伪证当作史实和确证使用之类低级错误。
再次是对论题的展开方式和结构布局进行设计。
史家对历史对象本身的研究一经展开,史料和史实的搜集、分析、考辨基本到位,随之而来的研究便是对论题的展开方式和整体结构进行先期谋划和设计。这是史家进入实际阐释和写作过程之前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本论题将以怎样的逻辑思路和结构形式展开?如何处理论题展开中主与次、详与略、取与舍的关系?如何建构谋篇布局中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微观结构之间的逻辑框架?等等。事实证明,史家若不把上述问题思考清楚、谋划得当,并在反复比较之后逐个提出妥善解决方案,以求做到全局了然于心、各部把控有序,那么,史家进入实际阐释和写作过程之后必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困扰,例如主次脉络处理失当、结构层次不清或逻辑混乱等,严重者甚或不得不推倒重来。
总而言之,本文提出的“对象第一性”“史料第一性”“史实第一性”和“研究第一性”原则,是超越史观域限的共同准则,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阐释实践中,持有不同史观的史家和史书写作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践行之。虽然,这四个共同原则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历史研究和阐释成果一定会达到怎样的高度或深度,但它却可以使得史家遵循科研和思维的客观规律、沿着历史阐释的正确道路探索前行,只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这四个共同研究原则不动摇,我们的历史研究和阐释事业必有所成;何况它也是端正学风、增强学术规范、提高历史研究和阐释的科学性、防止走弯路和无效劳动的重要举措。
史家之大本、治史之灵魂:秉笔直书原则
秉笔直书原则,为我国史学泰斗司马迁及其宏著《史记》所奠定。自此以降,两千余年来一直成为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一根精神支柱。
秉笔直书的基本含义是:秉持史家的道义和学术责任,忠于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排除外界一切干扰,不虚美,不掩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手中的史笔,按照历史的本相来记写历史的来龙去脉,向读者和后人奉献一部真实可信的“信史”。
践行秉笔直书原则,就要求史家采取“历史还原”之法,将历史对象放回到历史对象所处的特定环境之中,看史家及其历史阐释是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所采用的史料在整体上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对历史对象的描述是否符合实在性历史存在及其进程的原貌,是否忠实描绘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发展线索的基本轮廓。只要它在上述问题上都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拷问,那么它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合格的“信史”。
在史学研究中,汉代司马迁所确立的秉笔直书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息息相通。
不仅如此。联系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写作这一领域,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家敢于声称,他的音乐史研究和写作是可以公然不遵循秉笔直书原则的,他笔下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是被他随意涂鸦、篡改过的主观幻象;若真有这样的史家和所谓“音乐史著述”出现,至多也被当作小说或其他无厘头作品来读,绝没有任何一个同行和读者对此会由衷认同,因为它不具备最起码的史学品格。
另外一种情况更加发人深省:某些史家自称是崇尚秉笔直书的中华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然而他们笔下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却是满纸的阶级斗争史;一些重大音乐批判事件和已经得到公认的重大原则性错误,则被隐瞒了,掩盖了,回避了,或者被轻描淡写了,甚至刻意炮制假材料,以蒙骗后世学者,或者倒打一耙,以阻止历史真相的被揭露。这样的“秉笔直书”,这样的“实事求是”,除了让人引为笑柄之外,也为所有史家敲响了警钟,在治史原则上提供了反面教材。
还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情况,对某些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著名音乐家,史家对此所做的人物专题研究,却回避对其若干失误或错误做真实的记写。例如李焕之研究,回避他在李凌批判中对于“资产阶级唯情论”的错误批评;例如在编纂《贺绿汀全集》时,不愿将贺老写的个别文章编进去。这样做的动机和结果,看似十分人性化,但历史研究的秉笔直书和实事求是原则,却被抛在一边。这便是“为尊者讳”思想作祟之故。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就是真相,来不得半点虚假。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光焰无际的太阳尚且有黑子存在,而况贺绿汀和李焕之乎?再说,我们中国古来就有“不以一事之失,否其整体之善”一说,我们忠实记写二老在某些事情上的失误,只要将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客观分析其特定条件,非但不影响他们在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反会因此而凸显人物在历史行为中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令我们的历史书写更显真实、生动和厚重。
因此,贯彻秉笔直书原则,强调的是音乐史研究和写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超越史观域限的,故此也是所有史家必须严格遵守的共同原则。
从另一个高度说,践行秉笔直书原则,还牵涉到史家之史胆和史识诸问题,即敢于直面历史真相,道出历史真谛,将深刻的历史经验揭示给后人,等等;对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这一特殊研究领域及其所承担的史学使命而言,此乃史家之大本、治史之灵魂也,应当成为一切史家的精神脊梁和道义风范。唯其如此,本学科的研究方能更好地承担起自身的史学使命,走上健康、科学、繁荣的轨道。
注释:
①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最初于1959年作为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试用,1964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名义出版、内部发行,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
②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载《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③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台北《音乐时代》杂志出版社,1998。
④刘靖之:《有关中国新音乐的“表达方式、表达能力、美学基础”的几点说明》,载《乐览》,2000年第7期。
⑤魏艳:《音乐活动家吕骥及其历史贡献》(打印稿)第108页。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