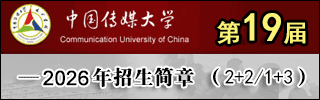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刍议
内容提要:“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是当前音乐学界在解读音乐作品时最常用的两个词汇。现在是到了把“音乐分析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即“一门通过建立系统的音乐分析理论、内容和方法,并在分析实践中把厘清音乐作品的结构脉络、确定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并揭示音乐作品的创造性价值和文化意义作为己任的学科”。
关键词:音乐学/音乐分析/音乐学分析/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学科内涵及学术意义
作者简介:陈鸿铎,音乐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10031)
标题注释:附言:本文获得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T0701。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音乐学与音乐分析
“音乐学”(musicology)可以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一方面可以包罗与音乐有关的所有活动,如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体制中,所有与音乐有关的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和表演活动都被归入一级学科“艺术学”中的“音乐学”这个二级学科名下,这是广义的音乐学概念。另一方面,音乐学也可专指音乐教学与研究中的某些具体活动,特别是具有学术性质的音乐研究活动,如专业音乐院校中音乐学系所开展的各项音乐研究工作,它们包括:传统音乐学中的音乐史学、音乐文献学等;系统音乐学中的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教育学等;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中的音乐民俗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民族志学等,这是狭义的音乐学概念。本文所涉及的即是此狭义的音乐学。
“音乐分析”是对音乐作品进行解读的一种方式,由于它通常会较多涉及音乐创作中的各种技法,因此它通常是不被包含在狭义的音乐学里面的。一直以来,人们习惯地把它当作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即属于作曲这个领域,而作曲与表演都是技术性的,它们是与音乐学相对的另一种行当。
然而,把音乐分析排除在音乐学研究之外的这种看法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学术思考方式,或者说是长期受英美音乐理论体系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思考方式。其实,在整个西方音乐学界,并不是都认为音乐分析不属于音乐学研究的范畴。在传统的英美音乐学理论体系中,有把音乐分析看作是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的倾向,即不把它归属于音乐学研究范畴。然而在德奥的音乐学理论体系中,音乐分析通常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音乐学的研究范畴。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是纯粹的作曲技术分析,也或多或少地会涉及音乐作品的文化意义问题,这两者是很难决然分开的。况且,技法理论研究本身本来也可属于体系音乐学的范畴。我国以往的音乐分析受英美体系的影响较深,大部分的分析类文章从主观意识上把自己的研究当作对作曲经验的总结,和对他人进行创作的指导,较少涉及作品的历史、社会、美学等大文化方面的问题。
但是,自20世纪以来,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的音乐分析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英美的音乐分析观念已产生很大变化,音乐分析中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作品的人文意义,因而实际上已使音乐分析具有了音乐学研究的意义。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中国的音乐学研究中,从而还促发了“音乐学分析”概念的产生。
二、关于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
“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这两个概念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与使用却有很大的区别。10多年前,为了提倡一种与过去不一样的音乐分析模式(即只进行音乐创作技法分析的模式),著名音乐学家于润洋先生就在他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音乐学分析”这个概念,于先生对音乐学分析的内涵进行了这样的概括:“音乐学分析则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于先生以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这部著名乐剧的前奏曲与终曲作为对象,经过从技术语言到人文内涵的全面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既有深入的作曲技术分析,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分析的两者完美结合的范例。从此,在音乐理论界引起了一个关于“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这两种不同概念和分析方法的思考和讨论。自那以后,以“音乐学分析”为目标的音乐作品分析文章开始出现在各种杂志上,并逐渐成为音乐学学者们进行音乐作品分析的一种模式。可以说,于润洋先生所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反映了在中国一般音乐分析在音乐学研究方面存在的缺失,从提升中国音乐学者音乐分析的学术质量来说,无疑是很有必要和非常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词语逻辑上看,“音乐学分析”本来是可以被包含在“音乐分析”之中的。况且在西方音乐理论体系中的名词术语或相关概念的表述中,并不存在“音乐学分析”这个概念。不论是英文权威音乐辞书《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New Grove)还是德文权威音乐辞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MGG)中,都没“音乐学分析”这个专门词条,而都是只有“音乐分析”(Analysis或Analyse)。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西方,所谓的音乐学分析实际上已经被包含在音乐分析之中了。
如果认为西方的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那么,在我们重新审视音乐分析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作为一项音乐研究活动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属性的时候,是否应该对目前这两个概念名称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必要的调整呢?笔者以为,这样的调整或许值得尝试。当然,考虑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调整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近年来由于对音乐学分析产生的一些模糊认识,一些学者在进行音乐学分析时,把只要是不涉及技术分析的文论认为是在做音乐学分析,导致了音乐学分析概念的混乱,有些这样的分析文章其实已经不能再算是分析文章了。为了还分析以本来面目,为了使于润洋先生所做的音乐本体与人文内涵“两手都硬”的分析示范得到人们正确的对待,笔者拟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音乐分析学”的概念,以进一步促进音乐分析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前面提到在西方不存在音乐学分析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在中国也不能提音乐学分析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从词语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会发现,由于“音乐分析”这个概念实际涵盖的外延非常广,所以,“音乐学分析”其实已被包含其中了。这样在词语上,两者实际上是不能并列的。对此,笔者以为是否可以用“作曲技法分析”代替“音乐分析”,它和“音乐学分析”形成并列,而在它们之上则以“音乐分析学”统领之。下图所示即为音乐分析学的基本框架。

三、音乐分析学学科概念的界定、学科内涵及学术意义
自20世纪以来,音乐分析虽已逐步形成一种独立的音乐研究方式,并基本建立起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具备的基础,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音乐分析学”到迄今为止在中外音乐学科的分类中,似乎尚未被明确提出过。尤其在中国,对音乐分析作为学科的认识还未形成。考虑到音乐分析目前所呈现的种种状况和理清其发展脉络的需要,在此,笔者觉得是到了把“音乐分析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提出来的时候。
(一)关于音乐分析的理论现状
在以英、德两种文字为代表的西方音乐文献中,关于音乐分析的专门文献是有的,如英文大型音乐辞典《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analysis”,和德文大型音乐辞典《音乐的历史与现状》中的“Analyse”。②这些条目已相当全面地对音乐分析进行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音乐分析学”的整个学科内容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西方的音乐研究中,“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实际早已存在。
而在中文的文献中,迄今尚没有人全面地阐述关于音乐分析的种种理论问题,“音乐分析学”这个学科概念更未正式地出现过(有些文章或著述中虽出现过这个词,但并未赋予其学科的意义)。我们常见的与此相关的一些概念名称则有“音乐分析”、“作品分析”、“曲式学”、“音乐构造学”、“音乐形态学”等,而这些概念通常是不能被当作“音乐分析学”的学科来看待的。
“音乐分析”与“作品分析”是人们在谈到分析时两个最常用的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人们在运用上常常并没多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别,即把它们都理解为仅指对音乐作品进行本体分析。然而从用词的严格意义上看,“作品分析”似应比“音乐分析”涵盖的面更广些,因为它可以包含对音乐以外因素的分析,尽管许多人在用这个词时并没有意味着要这样去做。
“曲式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音乐作品曲式类型的学问,它的关注点是从众多的音乐作品形式中,找寻共同的组织规律,从中归纳出一些常用的曲式类型,供学习者和作曲家参考。应该说,与音乐分析或作品分析相比,它的研究范围相对狭小,主要是从教授法的角度总结曲式的共同规律。
“音乐构造学”这个概念由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赵晓生提出。③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把音乐作品当作由各种素材组合成的一个“构造物”,通过对其中各种素材特征的分析和综合过程的解释,达到对音乐作品结构组织的深度理解。应该看到,虽然“音乐构造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大量的音乐分析内容,但就其本质来讲,主要是在解释作曲家的创作过程,仍然属于作曲法教学的范畴。
与前面的几个概念有所不同,“音乐形态学”在强调对音乐作品进行本体考证为基础的同时,还主张对综合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史学、美学等,对音乐作品进行更全面的研究,这体现出对音乐作品的音乐学研究指向。根据国内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看,“音乐形态学”最先是由音乐学家叶纯之提出的,他对“音乐形态学”所下的定义是:“根据音乐的形态即具体音乐作品的样式、结构、逻辑等来研究音乐的形式与内容诸关系的学科”。[1]最近出版的由王耀华、乔建中主编的《音乐学概论》一书中也有一章关于“音乐形态学”的论述(由谢嘉幸、李西安撰写),在该章中,作者在先对中外关于“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内容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后,提出了四点重要的学科内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音乐形态学研究应该首先从非欧洲音乐的研究入手,从不同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入手,以弥补以往音乐形态研究(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缺陷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以文化为语境的各民族音乐形态的研究。”[2]
(二)对“音乐分析学”概念及内涵的理论定位
从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概念名称及其内涵所指来看,它们均不能取代“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内容和意义,其理由后面将会述及。现在,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是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分析学”。
首先,音乐分析学是一门从事音乐分析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学科,这个研究可分为3个层面:音乐分析的历史学研究;音乐分析的范畴学研究;音乐分析的方法学(论)研究。3个层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音乐分析学”学科体系。
1、关于第一个层面
追溯音乐分析的历史起源,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外音乐分析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对不同时期音乐发展产生的作用、重要的分析家及其有代表性的成果,为该学科的建设找到历史的支点。具体工作为音乐分析文献的整理、发展线索的勾勒、不同观念的总结、评价观点的提炼等,这一层面的工作是本学科建设的基础。
2、关于第二个层面
阐明音乐分析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确定分析“活动”(activity)为音乐分析学的立足点,首先界定音乐分析的基本工作过程,然后把分析内容再分为两个大的层次,提升音乐分析的成果价值,使音乐分析成为音乐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
分析就其广义的字面意义而言,是指把一个整体分解或化解成若干部分,进行局部的解剖、查找、考证、发现等活动,而音乐分析,则是指针对音乐作品开展这些活动,它所运用的基本工具是各门作曲技术理论,但在预设的分析切入点上得到运用。需要指出的是,分析虽然强调做“各个击破”的工作,但其分析结果却必然是综合各方面的局部分析而得出。因此,分析与综合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在“音乐分析学”中,分析的活动可在两个大的层次展开,即:结构性分析(formal analysis)和风格性分析(stylistic analysis)。正如勋伯格在谈到应如何对音乐作品进行解释的时候所讲的两句话,简单地来说就是两个字,即“how”和“what”,④其所指就是对被分析音乐作品的本体进行完成过程的解释和对其价值意义的定位。这里所提出的两大层次吸收了勋伯格的这一观点。所谓“结构性分析”就是面对音乐作品的实际文本(乐谱、音像或现场表演),通过从较为具体的技术层面上的分析,来解释音乐作品的组织材料和结构原理。这一点与以往一般所理解的音乐分析相同,或者说是继承了传统音乐分析的内容,即所谓“以揭示作品的结构组织关系为目的,不涉及较重大的美学问题,如作品的表现意义或价值问题”的分析模式。⑤所谓“风格性分析”就是把音乐作品放到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民族的大背景中,通过从较为抽象的风格层面上的分析,来解释音乐作品的人文价值和史学意义。这是对传统分析模式的一种拓展,也是音乐分析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如果说结构性分析是“实证性的”,那么风格性分析就是“思辨性的”,或者按照现在人们常用的一种说法,即“音乐学分析”,这种分析已成为现代音乐分析的重要内涵。这两大分析层次可以包含几乎所有的分析内容,它们互为依托,虽可按不同侧重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但思辨性或音乐学分析必须以实证性分析为前提,否则“音乐分析学”的学科性质就会转变而成为“美学”或“史学”了。这一层面的工作是本学科建设的主体。
3、关于第三个层面
对该学科进行分析方法的体系化理论建设,以使音乐分析学的学科体系在理论上更加完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论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它也是构成该学科的“立身之本”。目前,西方的音乐分析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自成一体的分析方法,如基于作曲技术之上的各种结构元素的分析法、勋伯格的主题—动机分析法、雷蒂的主题过程分析法、申克的简化还原分析法、福特的音级集合分析法等。当然,还有许多分析方法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这需要继续进行适当的整理和完善,以适应本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中国的音乐分析,在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基础并以西方音乐作品(或以西方作曲技法为基础创作的中国作品)为分析对象的情况下,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方法,虽在总体思路上未超出西方的范围,但它们对于西方的分析方法是很好的补充,是确立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此外,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分析,虽然也被包含在本学科的“风格性分析”中,但由于这方面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总结一直以来比较薄弱,或主要都是由民族音乐学者和音乐人类学者在进行,因此,其分析方法论的整理对于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建设也显得相当紧迫。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音乐分析学”的分析对象通常主要是针对已经写成的和已被演绎的音乐作品(常常是优秀的、成熟的作品)的结构与风格特征,这是与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主要是经过田野工作再进行整理归纳的研究方式相区别的。
根据以上三个层面的阐述,可以把“音乐分析学”的学科概念简述为:一门通过建立系统的音乐分析理论、内容和方法,并在分析实践中把厘清音乐作品的结构脉络、确定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并揭示音乐作品的创造性价值和文化意义作为己任的学科。从更高的层面来讲,由于音乐分析学研究所跨越的宽广层面,它已不再局限在作曲技术理论的范畴,而跨入了音乐学的领域,属音乐学研究的范畴了。
现在,如果我们把上述对“音乐分析学”的界定与前面提到的几种相关概念名称进行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的。“音乐分析”、“作品分析”、“曲式学”、“音乐构造学”所关注的基本上都是与音乐作品本体相关的技术问题,而叶纯之对“音乐形态学”所作的“音乐形态学是以往的音乐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又为音乐美学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的表述虽与本文所说的“音乐分析学”相类似,但用“形态学”替代“分析学”并认为用“形态学”就可以涵盖更全面的分析内容,笔者认为并不妥当。“音乐形态学”这个名称的问题在于,“形态”本身是一个有着具体含义的词汇,通常指大大小小的各种形态类型,用它来做为一个与分析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名称,反而不如用“音乐分析学”这个名称更为恰当。因为分析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它所涉及的内容,当然也有形态的方面。与“形态学”相比,“分析学”的涵盖面当然更广,而非更窄。至于谢嘉幸、李西安撰写的“音乐形态学”⑥尽管是在叶纯之的“音乐形态学”基础上的发展,但与叶纯之的“音乐形态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叶的“音乐形态学”是对原有音乐分析做了文化方面的扩展但仍没有脱离音乐分析基本任务的话,那么,谢、李的“音乐形态学”则因其对非欧洲音乐研究的强调和对整理采集方法的提倡,表明了他们的“音乐形态学”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倾向,与“音乐分析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已相去甚远。
对音乐作品进行音乐本体的技术分析对于深入的音乐学研究来讲,是一条不能绕开的必经之路,因为它是连通音乐研究中的哲学和写作技术两大领域的重要纽带,而建立一门独立的“音乐分析学”学科必要性在于,它不仅理顺了在分析上各种名词概念的关系,还以更加系统的学科思维展现了分析在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意义。
注释:
①根据这个图式,我们拥有了一个“音乐分析学”专业学科的基本轮廓。当然,如果把“音乐分析学”作为一个学科来看的话,还应包括一块内容,即分析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目前,“音乐分析学”这个学科尚未形成,而与此相近的学科已经有“音乐形态学”,不过它与“音乐分析学”相比又有所不同,因为它更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参见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②请分别参见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和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中的“Analysis”和“Analyse”条目。
③此提法引自赵晓生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音乐构造学”。
④参见Clemens Kǖhn的Analyse lernen第8页,Br enreiter-Verlag,1994。
enreiter-Verlag,1994。
⑤参见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的“Analysis”条目。
⑥参见王耀华、乔建中主编的《音乐学概论》第7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原文参考文献:
[1]叶纯之.音乐形态学[A].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2]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78.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