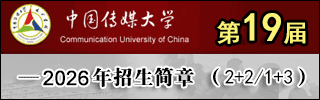内容提要:音乐学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在音乐学领域得到普遍接受,但当学生在进行个案研究时,仍然会出现一筹莫展的情况。面对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作者针对音乐学分析的具体操作、理念提出思考。
关 键 词:音乐学分析/原则/无原则/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法无定法
作者简介:周小静(1953-),女,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天津 300171
“音乐学分析”是于润洋先生提出并建立范式①的一种研究方法。音乐学领域的学者以及音乐学系本科、硕士生、博士生,除田野工作之外,案头工作大部分就是“音乐学分析”。于润洋这篇优秀的论文自问世起就成为学术典范,对学科发展、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必读文献。但当学生们把目光转移到面前的个案时,仍然会发现情况复杂以致一筹莫展,久久难以下笔,可见优秀的范本是不能当作模版套用的,我们应该领会的是于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而不是表面化地模仿其框架。确定使用什么样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基于哪种哲学体系和观念,继而构思、搭建论文框架,最终获得自己独有的体验和思考结果,这是一个庞大繁杂的工程。
本文题目乍看似乎是试图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手段或原则,但笔者的意图并非也不敢如此。文章第一部分“原则”是以一部西方宗教作品为例,提出材料搜集的范畴和选择;第二部分“无原则”是强调拓宽视野,解放思想,特别是强调对某些存在于中国音乐学界的固化思维模式和观念的反思,提倡创造性精神。②
“原则”与“无原则”不是两个毫无干系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阐述方便先简单地将其分开。
对音乐学分析来说,有价值的原则太多了,诸如马克思唯物史观、二元对立、进化论、唯心论、目的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以各种形式体现于西方音乐研究中。这里提出的原则不涉及上述概念,只是强调:在研究中以专业的态度和技能掌握并尽可能穷尽facts即事实。
以一部基督教弥撒为例,它的事实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谱纸上记录的一切:作品采用的调式调性体系;素材来源(是否采用现成的圣咏或他人创作的曲调)及其运用(是否作为持续声部即tenor,该素材是否在乐章中有连续性展开或是否贯穿于各乐章等等);旋律特性(吟诵或歌咏性质);节奏写法(是否采用古老的节奏模式),音乐与歌词关系的处理方式(音乐是否忠实于原文本的句法和韵律,或从音乐意图出发删改、重复歌词,或因特殊表现需求改变词语的重音和节奏特性);声乐与器乐的关系(器乐完全处于伴奏地位还是其本身有特定的甚至独立的象征、表现意味);全曲的情绪布局(对各章歌词内容在情绪上的宏观把握)以及细部处理(个别重要词句在情绪与形象上的音乐表现),整体与细部结构(如各乐章之间的对比、对称、首尾呼应关系以及各乐章内部的曲式结构)。研究者若能获得手稿,还可能获得更多信息,诸如从修改的笔迹看作曲家的创作思路,这些思路与作品最终结果的关系等等。
2.与作品相关的情况:创作年代;创作目的(如为日常仪式或特殊的加冕典礼、特定节日庆典而作);委约人的偏好或规定;演出场所及演出阵容的大小。这些情况对作品本身会有直接的影响。
3.作曲家的情况:他的思想、宗教信仰、个性;供职于何处(如皇家小教堂还是公众大教堂)。创作该作品时作曲家的生活、思想状况;其他作曲家或流派对他的影响。
上述“facts”是与作品和作曲家紧密相关的事实,从乐谱开始,关注点如涟漪一般向外围扩展。很多论文写到这里就止步了,其实这还只是第一步。作品产生的语境是非常需要关注的,否则它的特点不会得到彰显,对其意义和价值也无法作出评价,仿佛盲人摸象,缺少参照。真正有价值的观念(idea或meaning)是在大量相关facts之间的联系、对照之中逐渐生成的。
于是,涟漪继续扩大,以下几个方面也应该纳入视野:
4.该作品与之前、之后弥撒写法的异同(对传统弥撒写法的传承与创新)。
5.该作品与同时期其他音乐体裁的关系(如是否受到歌剧、多乐章套曲结构、协奏性质的声乐体裁、协奏曲、交响曲体裁等风格的影响)。
6.同时期创作观念的总体倾向(如巴洛克时期的激情风格、戏剧性、浪漫主义、世俗化等等)对这部作品的影响。
7.作曲家如何处理宗教仪式与艺术性、宗教信条与人性体验之间的关系。
8.该作品与同时期人文精神、宗教信仰(或基督教神学发展倾向)这个大环境的关系。
9.国家、地域乃至民族精神与民族风格在该作品中的体现。
10.……
与作品或近或远的相关事实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与作品相关的整体语境。
事实(facts)是不是客观、绝对的存在?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有人将事实存在与观念、看法分开,将前者看作是对绝对存在的发掘,就像考古,后者是对存在的看法。实际上没有这种绝对的存在,只要它在人们眼前出现,就必然是通过人的认知的,因此在对一部音乐作品的“事实”进行观察并作出描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附着上观念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研究方法、认知能力、所处时代的文化环境乃至个性都会使他的认知和描述带有个人色彩,这必然会影响到对“事实”的选择、看法,并最终引向他自己的分析结果。这种不确定性有点像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有些令人不安,但实际上并不可怕,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学术才会有不断的发展,对历史的观察和评述才成为有意义的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写作者必须对此现象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尽可能接近事实与大胆作出主观推断这两端之间尽可能理性地保持距离,而且不单要自己清楚,还应在行文中使读者明了。再进一步的要求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用怎样的观念和方法解读作品。
除了“穷尽事实”之外,还有一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要在感性上接受作曲家的“馈赠”。无论一部作品会触及到怎样的文化背景,作曲家在乐谱上留下的任何一个笔迹都是为了“听”,为了将听者裹挟在他的音响洪流中,与他一道体验某种特定的情感和意味,而不是提供一个可供后人分析的纸面材料。笔者看过不少音乐分析文章,结构严密、语言精致,分析和结论头头是道,但从中看不到一丝作为聆赏者的感性体验,显得十分冷酷甚至有“作者缺席”之感。我认为,音乐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音乐接受、感受者,无论是音乐技术的分析还是音乐意味的揭示,都不应缺失声音引发的个体体验,当然,这个感动也不可能是无意识的,而是蕴含着聆听者全部人文修养和音乐素养的。
无原则
前文谈到,对音乐学分析来说有价值的原则很多,诸如马克思唯物史观、唯心论、目的论、中心论、进化论、二元对立、结构主义等等。那么,为何还要提出“无原则”?
事实上“无原则”才是本文写作的首要出发点,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研究以及对国内西方音乐史学界发展倾向的了解中生发的思考。对目前大大小小、各种层次的“成果”我有个总体感觉:有不少只是以详尽的个案分析去证明已经存在的论断。假如这种状态长期保持,我们很难在学术、学科建设上有所发展。
近十几年国内很多资深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西方音乐研究历程进行深刻反思③,使我们认识到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多么荒谬。今人在回顾这些现象时常会摇头连连、哭笑不得,但事实上,那些荒谬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影响深重,也许正以另种形式不知不觉地出现在自己笔端。例如:面对浩瀚的“事实”研究者常常作简单归类,这些类别包括正确—错误、发展—倒退、高级—低级、积极—消极、光明—黑暗、健康向上—低级颓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主流—外围……。与此同时,这样的句式在论文中十分常见:“正如某某(一般为权威)所说……”;“古人云……”;“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句子之后,似乎有众志成城、铜墙铁壁、伟人权威在支持着作者,后面的论述也就毋庸置疑了。再举几个具体例子:“音乐是用来听的,谐和悦耳的声音才能称得上是音乐”;“音乐应该为现实服务”,“为大众理解并喜爱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序列音乐是计算性的,缺少人的情感”,“西方文化完全建立在理性之上”,“西方音乐的科学性思维已至绝境,不得不向东方寻求出路”等等,诸如此类。在引用者看来一切都非常简单,在任何作品面前,只要将这些尺子举起来,做个衡量,归个类,就完事大吉。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一下:这些“尺度”产生于何时?它与怎样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某某权威、古人的观点是否放之四海、四时而皆准?让我们以“为大众理解并喜爱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这个论断为例作一连串追问:谁是大众?由什么成分组成?包括音乐爱好者吗?包括对音乐毫无兴趣的人吗?包括仅热衷于流行音乐或民乐、交响乐、歌剧、原生态民歌、昆曲、古琴的人吗?哪个时代和哪个地域的大众?再问:是不是凭人数多寡就可以确定一部音乐作品的价值?个人的喜好、偏爱,与作品本身的价值有直接关系吗?……可以想象,对中世纪跪在教堂里虔诚吟咏圣咏的大众即基督教徒来说,今天的音乐几乎都是不可忍受甚至有如撒旦的声音;而对喜爱宁静安详音乐的大众来说,大分贝的摇滚乐绝对是对耳朵和心灵的摧残,他们会说“这根本就不是音乐”——正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曾经得到的评价。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巴洛克”一词是怪诞的同义语,莫扎特一部弦乐四重奏绰号“不谐和”,等等。
李应华先生在《西方音乐史学》第一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轨迹”中介绍了苏联历史音乐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40~50年代状况的反思,下面这句话让我深受震动,这是学者们对自身深刻而沉痛的剖析:“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除了外面的压力以外,在深处还稳坐着一个‘内心检察官’”,④直到80年代“如果说我们不再感觉到从上面来的禁令,那么在我们身上死得很慢的‘内心检察官’目前仍是历史意识的最强大的敌人之一”。⑤
若是某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存在于经过荒谬年代的年长者头脑里似乎还有情可原,但若是大量存在于年轻一代的头脑中,就相当可怕并令人焦虑了。
那么,音乐学分析究竟有没有可遵循的原则?当然有,但我认为应该是“法无定法”式的原则。这一思想出自佛教《金刚经》释迦牟尼佛与门徒须菩提的对话,大意是修行求道不要执著于任何理论、学说、方法,任何迷信、教条的态度都是违背佛教基本思想的。佛说“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提倡创造性,突破前人的“定法”,从前人的“无”中发现、发明或创造出新的东西来。佛又说“非法,非非法”,即也不要一概否定前人的“法”,因为这又是一种执著了。⑥
与尊崇“觉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西方人自古以来就有将知识、理论系统化的思维习惯,并一代代传承、发展这些理论体系,更不断大胆反思,从中引发出新的观念。20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的剧烈变革引起世人瞩目,从克尔凯郭尔、尼采哲学精神发展而来的现代存在主义批判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认识论,强调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排斥科学发展对人的异化,支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向往人类终极价值的宏伟远景。显然,存在主义哲学是启蒙思想之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再发展。随后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则是存在主义之“反动”,是对启蒙主义理性精神的全面反思,他们反对将人看作世界的主体,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决定一切的是客观、理想的结构,是包含着无意识活动的普遍规律的模型,它不是个人主动的创造,而是人这个物种的群体心智的自然产物,个人只是这个结构中的组成因子,因而他们忽视个人,强调整体以及“结构”中的关系。结构主义是反历史的,认为人类社会无所谓进化、进步,世界并不存在一个预想的“未来”,一切都只是共时性(或称同时性)的带有差异的模式的重复。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时代迅猛发展的自然科学的产物,也与列维·施特劳斯在人类学、人种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实证主义观念密切相关。随着结构主义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被称作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念,它深受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⑦、混沌理论⑧的影响,一方面承认客观结构的存在,反对线性的、因果的历史观,但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关注这个结构中的差异,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呼吁破除话语权力,反对精神专制和对绝对理性的崇拜。有人批评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始终未提出一整套可循的原则,他的理论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状态,然而这恰恰是解构主义思想的核心,即精神的解放。他们看重的是作为思考的主体——人,强调每个人面对facts时的创造性,强调世界在创造性的人的眼中的多解。在他们看来,启蒙主义对人性的解放是不彻底的,只不过是用新的理性精神取代了过去的神权。尼采说“上帝死了”——是破除神性和形而上学体系的权威,福柯说“人死了”——是破除理性权威和人的中心主义,而德里达说“作者死了”——一切书写文本在完成之时即已脱离作者,更重要的意义和关系发生在文本与读者而不是文本与作者之间,读者的解读成为新的、独立的自在物。⑨
西方近年来的音乐学领域也有引人注目的发展,除了继续深化、拓展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也将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等融合进来,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⑩流派。新颖的视角为音乐研究带来了清新活泼的空气,但也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抵制,认为某些研究成果是无法确认其正确性的,臆测成分太大。这与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遭到的质疑有相似之处:一些人认为“解构主义”是未完成的、不完整的理论,未能为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其破坏的成分远远大于建设。而事实上这正是解构主义的核心精神: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创造的而非重复的,个别的而非集体的,变化的而非规则的。“解构主义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器’,一种操作的原则。”(11)
让我们再次面对前文假设的那部弥撒。穷尽事实,可以使我们避免一叶障目、盲人摸象,但是在开始研究时就必须有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了。现在大量论文采取这样的标题:《××××(作品)的音乐学分析》,显然是效仿于润洋先生的范文。我认为对于一篇学期或学士论文,除非有相当大的容量,否则这样的标题与不长的篇幅之间是不成比例的,只能是泛泛而谈,不如选取一个较小的、新颖的角度进入,尽量做得充分并论点鲜明,如《×××弥撒曲对固定调的使用》,《×××弥撒曲的歌词处理特点》,《×××弥撒曲中管弦乐的表现意义》,《在×××弥撒中体现的套曲思维》,也可聚焦于单个乐章,如《×××弥撒中羔羊经的情感特征》。假如篇幅大一点,可以进入更深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语境,诸如《×××弥撒曲仪式性与艺术性关系的处理》,《×××弥撒曲的〈羔羊经>所体现的基督教救赎思想》,《两部不同时期弥撒中“羔羊经”的对比研究》,等等。当然,这样的题目是不可能凭着灵感或空想预先设定的,否则常常会出现牵强附会或中途做不下去的危险,因此在确定具体视角之前必须对前述所有facts有基本了解,也可以在有了大致范畴、方向之后,一边对facts进行搜集、探究,一边调整切入点。
扩展视角,也是一种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起步于文本即该弥撒,完成于独立的学术研究?笔者有以下粗略的设想:通过这部弥撒,了解弥撒歌词、多乐章曲式的一般规律、宗教仪式的程序与人的精神、情绪发展脉络之间的同构;弥撒歌词结构、情感结构、音响结构之间的关系;作曲家对弥撒固定歌词结构的突破和创新;弥撒仪式及音乐所体现的社会话语权力……。舒伯特对弥撒歌词及仪式的解构与重构;伯恩斯坦对弥撒体裁特定语境的解构与重构;古老文本与现代信仰方式的碰撞;从巴赫的弥撒看其与马丁·路德的血缘关系;基督教弥撒与佛教法会仪式比较……等等。这里列出的种种思路只是一些设想,还需要宽阔的文化视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扎实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开放、解放、创造性。然而这些设想至少探索了延伸的可能性。
德里达认为:“客观地把一个个案纳入到一个特定法律的普遍性中去,从而恰恰导致了不负责任,或者说至少与那个必须要做决定的、总是听说的独特性擦肩而过……既然事件每次都是独特的,那么,人们每次都必须有所创新,这一创新不会得到任何保证或肯定,不是没有概念,而是每次都必须超越概念。”(12)将眼前的个案纳入某个固有的理论框架,是简单而保险的,从个案出发,寻找属于它自身的特殊意义并建立起新的观念,成为通向众多可能性的新的出发点,是艰难并危险的,然而真正的价值只能通过后者实现。不再简单固守一种观念,不再举起武断的尺子,展现在面前将是开阔的、明朗的世界,对勤奋并有勇气的人来说,将是大有可为的。
无原则正如“法无定法”,这个“无”不是虚空,不是无知,而是无比丰富,以及在这无比丰富之上达到的无界无碍的至境。
无原则的原则
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人有自己特殊的视角,有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参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轻率妄言,不可越过facts大讲空话。事实上,扎实的研究和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在我们这里同样匮乏。因此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在专业分析上的扎实再扎实,在独立思考上的创新再创新。
本文最后郑重提出:尊重创作者和他的艺术品,尊重我们自己。上天给我们的是用来思考的大脑,而不是装他人思想的容器,更不是他人观念的复印机。
这两个尊重,就是“无原则的原则”。
注释:
①见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音乐研究》,1993年第1、2期。
②在某种程度上与解构主义的处境有些相似:既然郑重地提出无原则,这已经就是一个原则了!
③参见李应华:《当代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观念变迁》,《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3期;蔡良玉:《我国西方音乐史专著方法回顾》,《人民音乐》,1998年第9期;蔡良玉:《一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西洋音乐简史〉——“文革”时期撰写〈西洋音乐简史>回顾》,《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2期。
④巴尔索娃,张洪模译:《今日音乐史学的主体意识与自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0—11页。转引自周青青、郑祖襄等:《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178页。
⑤同上。
⑥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参见陈一阳著:《东方妙智慧,「金刚经」白话演绎》,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41—42页。
⑦传统哲学是建立在一种“客观观察者”的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也即是假定有一个观察者(人的理性或者神)能够从世界外部“客观”地观察,这种观察活动不会对世界施加任何影响。哲学家们相信存在客观的、超时空的、确定的真理正是由此而来。量子力学的出现粉碎了这种虚拟的客观性。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表明,作为观测者的人或者仪器在观测对象的同时已经干预并改变了对象的存在状态,客观的测量是不存在的,主观和客观其实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概念上的区别。参见杜小真:《德里达学术思想述评》,《学人》第六辑,1994年。
⑧科学家发现许多自然现象即使化为单纯的数学公式,但是其行径仍然无法预测,大量偶然因素或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例如:气象学家Edward Lorenz发现的“蝴蝶效应”。美国数学家Stephen Smale也发现,某些物体的行径经过某种规则性的变化后,随后的发展并无一定的轨迹可寻,呈现出失序的混沌状态。参见吴清山、林天祐:《教育名词》,《教育资料与研究》,1989年第34期。转引自http://sfmoe.org/asp_c/news_Itr/0005.htm。
⑨参见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8—20页。
⑩参见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
(11)参见杜小真:《德里达学术思想述评》,《学人》第六辑,1994年。
(12)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原文参考文献:
[1][英]阿兰·谢里登著,尚志英、许林译:《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2]包亚明主编,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3]杜小真:《德里达学术思想述评》,《学人》,1994年第六辑。
[4]杜小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与文》网站(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http://www.chinese—thought.org。
[5]陈一阳著:《东方妙智慧,「金刚经」白话演绎》,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6]徐崇温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7][英]彼得·沃森著,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20世纪思想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8][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1版。
[9]崔伟奇:《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光明日报》,2007—07—27。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