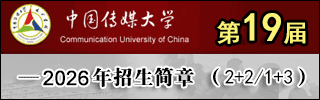作者简介:郑祖襄,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年届八旬的杨荫浏(1899-1984)先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鼓舞下,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讲了题为“我和中国音乐史”的大课,课程一共五次。能够聆听到杨荫浏先生讲课是这批学生的福分,自此以后,杨先生再也没有给学生上过大课。这批学生中日后担任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把这次课比喻为“最后的课”,并把课堂记录整理发表。①杨先生的讲课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基本上是“外来说”,等于说中国没有音乐发展的历史,他的观点有很大的影响。另一位学者林谦三的看法与他不同,他认真钻研,追求事实,态度是严肃的。而田边则是拐弯抹角地贬低中国。他一方面说:全世界以中国音乐最古,唐朝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高峰;但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中国保存得不多,大多数都在日本,欢迎中国人到日本研究中国的古代音乐。这是在将我们的“军”。我承认日本搞了一定的研究,保存了一部分中国古代音乐资料。但也应该指出,假古董不少。我们要严防上当。我在自己的音乐史著述中一般不引用他们的材料,这表示了我的严肃态度,也是我的民族自尊的一种心意,他们应该原谅。
日本的琵琶、笙的演奏水平较低,许多技巧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对此类事情,我们须心里有数,不能盲目。②
对今天来说,这是一段恍若隔世的往事,但它在近代中国音乐史学上牵涉诸多相关问题,却是后学们所不能回避的。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
田边尚雄(1883-1984)是日本近代著名的音乐学家。据当代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系主任植寸幸生(1963-)介绍③,田边尚雄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2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东洋音乐”,1926年出版《日本音乐研究》,1930年完成《东洋音乐史》。1936年东洋音乐学会成立,他担任首任会长。田边尚雄在亚洲各地进行的音乐调查和写下的大量著述,使他成为20世纪以来亚洲民族音乐学的著名学者。其中《东洋音乐史》,除“绪论”之外是五个章节,分别是:“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植寸幸生说:全书的内容大体相当一部《亚洲大陆音乐史》,同时也涵盖了部分日本本土的音乐。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田边尚雄著、陈清泉译的《中国音乐史》,全书除“绪论”(第一章)外是五个章节,五章的标题即是上述《东洋音乐史》的五个章节,只是《东洋音乐史》中的“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这一章的章名,在这里是改成了“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中国音乐的世界化”。除此,在《中国音乐史》章节标题中多处出现“中国”、“中国音乐”或“中国音乐史”名词,这和“东洋音乐史”名称又不太一致。相关具体章节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音乐史研究上之困难
第二节 进化论的看法与中国音乐史存在之意义
第二章 中亚音乐之扩散
第一节 中国音乐之源泉
第二节 印度古代音乐及与中国之关系
第三节 中国古代之音乐
第三章 西亚细亚音乐之东流
第二节 印度佛教艺术之盛时及与中国之关系
第三节 中国中世之音乐
所以据此推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其原本或者母本就是他的《东洋音乐史》。
1941年至1946年,杨荫浏在重庆青木关音乐院任教。其间,杨荫浏在1942-1944年的《乐风》杂志上发表了《国乐前途及其研究》④,文中有一段话,虽不指名道姓,实际说的就是田边尚雄:
在本国有人准备囫囵接受西方整个的音乐文化的时候,不远的邻邦,倒抢先一步地研究我国的国乐,并且略略拗曲了一部分事实,以加强它东亚文化主人的荒谬论点。
这段话,也是现今见到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最早的批评。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外来说”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外来说”,可以说遍布在该书前后的许多地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音乐源于中亚
……中国民族,为太古居中亚细亚东南之黄色人种,东进而移入黄河流域及扬子江流域地方而建国者,与由中亚西亚进之黄色苏美尔人,在太古实有密接关系。因汉民族之思想,与苏美尔人之思想,有共通点,故其音乐之基础,完全一致。(第二章第三节⑤)
中国民族之音阶,采用五声即五段音阶者极古,恐当原始时代,或彼等居原住地时,与苏美尔人共同用之者。此种原始的五声音阶,古代及未开化人屡屡见之。(第二章第三节⑥)
(二)中国乐器多属“外来”
1.琴瑟之外弦乐器均从西方传来
……再就丝属之乐器说明之。即琴与瑟二种,为中国古代国民乐器的代表。其他种类之弦乐器,皆自秦以后,由西方输入。(第二章第三节⑦)
2.笛从西域传来
纵吹之笛名曰管,特用二枚相并者。此与古代埃及等处之复笛相似。……
纵笛之一管者,名篴及籥。篴长,古有指孔四,汉京房加一孔为五孔。籥短而有三孔,皆周时所行者。此种乐器,殆与管系古代由西域入中国者。(第二章第三节⑧)
3.“弦鼗”源自西亚
秦从西域所得之新乐器,尚有与后之琵琶有关系而最有名者,即为弦鼓。杜氏《通典》云:“杜挚曰: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此种乐器,通常称为弦鼓。所谓弦鼓者,即如前述,美索不达米亚之弓形哈铺,张以羊皮于胴,变化而为三弦之形,入于埃及,乃有羊皮胴之那尔夫。此之种类,波斯大流士王以后,盛行于波斯,纪元以前,胴作圆形,张以兽皮,附以细长之柄,张弦数条。(波斯多用三条)当亚历山大帝国时,由波斯传入西域,流行各地。秦之百姓于长城之役,见其简单形状而模仿之;于平面鼓上插以棒,宛如鼗形,张弦用之,依所象形,名为弦鼓。行于秦末汉初,故又称秦汉子。(第三章第三节⑨)
4.弓弦乐器起于印度
用弓所奏之古乐器之一,名拉瓦那斯特隆,相传距今五千年前锡兰岛王拉瓦那所发明。即使不然,谓弓乐器为印度人发明当不为误。……又拉瓦那斯特隆最简单之种类,殆与中国胡琴之称为ur-heen者相一致。此物有二弦,腹部乃木之小片而中空者,张以蛇皮。此非中国古代所有,乃佛教入中国以后,(即自纪元二三世纪后自印度及西藏次第移来者)后遂入于日本。(第二章第二节⑩)
(三)隋唐音乐在中国已佚灭无存
以上系就唐乐传入日本之主要者述之。在中国则隋唐之乐,今皆佚灭无存;而日本今尚传存之。故欲研究隋唐音乐之性质,至日本方面考之殊为便利,兹详记之。(第三章第三节(11))
由于田边尚雄当时在日本、亚洲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他的“中国音乐外来说”不断地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林谦三(1899-1976)和岸边成雄(1912-2005)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关于“弦鼗”的研究,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说:
有人相信古来琵琶(秦汉子)出于弦鼗的传说——魏杜挚说,以为鼗(摇鼓)匡为槽,柄为颈而张弦;琵琶的渊源是这么一个乐器。盲从《乐书》“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之说。可是弦鼗与琵琶,以乐器论,有着根本不同之点。这种传说,乃是见到新乐器的形态远离中国向来的弦乐器,外形象是鼗之张有弦者,而编造出来的俗说。乐器的进化上是不可能有这样演变的。因之,虽说后世所谓弦鼗的乐器在唐代已经实际存在——见《乐府杂录》,终究还是后世的产物。由《乐书》说奚琴与弦鼗之形似来揣测,或者弦鼗倒是奚琴的一种变种也未可知。然而在秦汉之古时,中国已有弦鼗,怎么说也是不能想象的事。(12)
又如关于弓弦乐器的起源,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说:
但是,无论是波斯,或是阿拉伯,再往上溯,就什么都不明白了。因此,求弓擦的起源于印度之说,依然还是不能废弃的。……
如此说来,终于哪里都找不到弓擦法的起源,而只好归于印度吧。(13)
田边尚雄把中国音乐看成是来源于中亚,又把大部分中国乐器看成是外来的,并一直推向中亚或西亚,轻视和否定中国本土的音乐。他们研究中的偏向和错误,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中国的文献史料之外,也和当时运用人类学“传播学派”方法有关。
欧洲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方法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学者格雷布内尔和奥地利学者施米特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是“音乐文化圈论”。俞人豪(1946-)教授在《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一文中介绍“音乐文化圈论”说:
它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没有任何重复性,在不同的地方两次独立创造同样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它把当代各民族多种多样的文化因素在世界各地的空间分布解释为一种或几种文化千百年来不断扩张的结果。其扩张方式为:从一个或几个人类古代文化发祥地出发,向外作同心圆波浪式运动。而这种文化圈最古老的圆心被假设在西亚幼发拉底和第格里斯两河流域,或北非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地带,换言之,即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埃及这些古国的所在地。(14)
田边尚雄在他的《中国音乐史》中也申明他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
地球上人类之发生,在距今数十万年乃至百余万年以前。其发生也,与其谓为各处起于同时,宁谓起于某处者。(15)
并且按田边尚雄的说法,这个“某处”,即是所谓的“印澳大陆”:
(接上文)其发生地为印澳大陆。即太古时代,澳洲与印度及阿非利加之东边,联络成一大陆,人类即发生于此地,在此大陆陷没为印度洋之前,已渐次移动,主要移向西北及北及东北方面。其间分黑人种、黄人种、白人种等。(16)
“传播学派”的这种文化起源“一元论”的弊端,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被人们认识。人类学家海涅·格尔德恩(1885-1963)评价它说:
所谓传播主义并非是必须遵循的教条,而是适合于解释文化的某种现象的一种方法。不应该把所有现象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传播的结果。但在照顾到事实的前提下,用传播说可以说明的地方就应该用此方法加以说明。(17)
从学术方面讲,“中国音乐外来说”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思想方法。(18)在这样的学术方法下,有的史实便受到了“拗曲”。金文达(1919-1999)教授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中史料的偏向性有这样的评述:
……该书的第二个令人遗憾之处,在于有很多结论不是以中国的文献为依据,而是以日本的文献(如《大日本史·礼乐志》、《乐家录》、《教训抄》、《体源抄》等,以及朝鲜、印度等国家的音乐史料)为依据而得出的。因而往往出现并不符合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现象。对隋唐宫廷燕乐曲的考证尤为突出。……(19)
由于“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提出“东亚文化圈”(包括东亚音乐文化圈),这和当时日本政治上推行的“大东亚文化”有某些契合之处。这样的学术研究和这样的政治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社会的背景下,为政治服务和利用。
20世纪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给世界文明起源的认识提供新的证据。亚洲东方的考古成为国际考古学家感兴趣的领域。2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考古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安特生联系中亚的考古提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这个“西来说”被许多中外学者所接受,一时成为显学。(20)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中所用的中亚、西亚的考古材料,也可以看出他的“中国音乐外来说”是和当时这个考古学研究背景相联系的。
1935年,傅斯年(1896-1950)发表了《夷夏东西说》,自此产生了中国文明“东西二元对立说”,打破了一统天下的“西来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又产生了“一元说”,进而又发展到“多元说”。(21)可以说,“中国文明西来说”从20世纪30年代后趋于冷落,50年代后就被淘汰了。对于从属于中国文明的音乐文明来说,需要在中国文明起源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中不断重新思考。
除此,与“中国音乐外来说”的不同观点和学说从20年代起也不断萌生:
——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出版的王光祈(1891-1936)《东方民族之音乐》(22)。王光祈在书中已经提出世界三大乐系: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并指出中国的五声音阶早于西亚,与田边尚雄的观点针锋相对:
诚然,在上古时代,亚西里亚Assyrien(系地中海岸旁亚洲古国)亦系用的“五声调”,但亚西里亚历史上,可考之时代。仅至西历纪元二三○○年之谱,实不如吾国黄帝时代之古。而该国乐制,久已衰灭。因此亦不能作为现代各国“五声调”。……所以本书分类乃把“五声调”的始祖,加在中华民族的头上,称为“中国乐系”。(23)
——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一批古文字学家致力于甲骨文的研究。罗振玉(1866-1940)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1927年)、郭沫若(1892-1978)的《释和言》(1931年)对甲骨文的“乐”字和乐器名称的字(如磬、鼓、籥、稣、言等)作了考证,为商代及更早的音乐文化在本土的发生提供了考古史料。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内出版的几种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中(24),都已经收入了从远古到商代时期的中国本土新出土的各种乐器(陶埙、骨哨、石磬、编铙等),并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实证中国古代音乐的早期历史。
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区系类型理论”,成为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说”的开始。而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史界学者对考古乐器的调查和测音,至90年代《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陆续出版,其丰硕的成果与考古界提出的“多元说”正相默契。尤其是80年代末,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与研究,已经清楚地说明九千年前中国音乐已在本土萌芽。
无论说中国文明外来、还是中国音乐外来,都只是20世纪早期的学术观念。
隋唐音乐在中国已佚灭无存问题
撇开学术之外的用意,就以日本留存的唐代所传乐器和乐谱来说中国本土没有唐乐,于学术道理是讲不通的。唐宋时期留下的历史典籍记录唐代音乐都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宋以后唐乐在不断演变发展。如唐代流行的曲子音乐,在宋代演变为词调,进而变为元曲和明清曲牌。它们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戏曲、曲艺、器乐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的历史源头不仅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隋以前。又如唐代流行的还属于外来的乐器(如梨形音箱琵琶、筚篥、奚琴等)发展到明清,已经完全是中国乐器了。其形制、演奏技法、曲目都有极大的发展和进步,都已经是昔日远不能相比的。这些音乐和乐器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唐代、甚至更早的历史音乐的特点。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的存在本来就是流动的,在流动中也就不可能没有变化。20世纪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兴起,它以研究“非欧洲地区音乐及其历史”为目的,已经意识到“传统”是有其历史的。杨荫浏1944年完成的《中国音乐史纲》,不仅认识到“传统”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更注意到传统音乐中保存着历史音乐:
从民间音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少古代音乐之被保存,也可以看到许多古代音乐之渐失传。生活在延续,也在改变,音乐的形式在递传,也在发展;保存与放弃都是十分自然的事。(25)
……作者于此中稍一著手,便见得材料的丰富,而发觉古代音乐,至今人们共认为失传者,民间却存有不少。真要彻底了解中国音乐史,必须是在民间音乐大量的发掘之后。(26)
……在有些民间曲调中,我们见到古代“解曲”中“解”的部分;在有些曲调中,我们见到古代“下声弄、高声弄、游弄”,所谓“高、下、游弄”的例子;在有些曲调中,我们见到字调得法的处理。在某种合乐曲调中,我们见到唐人大曲排遍、曲破的部分。(27)
很显然,杨先生这一学术思想与田边尚雄所述“到日本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在史料和方法上完全不同。在杨先生之前,姚燮(1805-1864)《今乐考证》、童斐《中乐寻源》(1926)、郑瑾文《中国音乐史》(1929)在这方面都有所涉足,但都没有像杨荫浏思考得那样具体、深入。从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来看,也就是在这本40年代成书的《中国音乐史纲》中提得最多,并且杨荫浏有这样一种愿望:
作者愿于此时诚恳声明:这一部《中国音乐史》,不过就作者此时所知道的,老实的写出来而已,并不算一部完备的书;更完备的书,还得待后来得有更好的收集民间音乐的机会的人们,从更多的材料中获得了总结,然后能写成。(28)
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上说,这是一种思路、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它在杨先生学术思想中发展、成熟,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杨先生有深厚的中国传统音乐功底,也有来自外部的田边尚雄在学术上“‘将’我们的‘军’”的原因。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刘廷芳博士等邀请他去美国研究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学,杨先生拒绝了。他的回答是:中国音乐根植于民间,研究中国音乐,应在中国土壤上去研究古代遗留下了的活的音乐。(29)杨先生对这一学术思想方法的坚定信念,一直贯彻到他生命的最后。1980年,在由杨荫浏口述、李丹娜笔录的《音乐史问题漫谈》中,杨先生反复地讲这个问题:
……要是后来的人,踏踏实实地钻到民间音乐里面去,一个个把它的规律找出来,后来的每一部音乐史如果都能拿出一些这样的东西,就可以使这门科学提高一步。
……作为一个音乐史家,不要老去写音乐史,最好多去调查,收集各种曲牌,写出一本本曲谱来,用实践来充实音乐史,向深、广两个方面去搞。(30)
这期间,有一个代表性的民间音乐调查例子,实证了这一学术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1953年,杨荫浏亲自采访调查了北京城内的智化寺京音乐。在采访报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采访记录第一号)中论及乐器“十七簧笙”时,杨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笙——这种十七簧笙,还是北宋大乐所用的笙的旧制。陈旸《乐书》(1099)卷一百五十“义管笙”条说:“圣朝大乐所传之笙,并十七簧。旧外设二管,不定置,谓之‘义管’,每变均易调,则更用之。”用十七簧而不用“义管”,现在智化寺的笙,就是如此。
日本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在讲到笙的时候,曾说:“此十七管昔皆备簧。但日本只备十五簧,二管不用簧。今日中国所行者备十三簧,四管不用簧。”自河南方笙及保定吹歌会的“全字笙”出现以后,此说已见为不确。现在智化寺的十七簧笙一出现,则这一说法的错误,更是显然了。(31)
比杨先生略早一些接触到智化寺京音乐的古琴家、音乐理论家查阜西(1898-1976),在《写给智化寺僧人的信》中也说道:
看到了你们的乐器和乐谱,听到了你们的乐调和乐音,我才十分惭愧地感到:反而是你们这些过去被人视为“下贱僧徒”的苦人们才能拿出证据,去驳倒所谓日本的“中国音乐史世界权威”的鬼话!才能否定他所肯定的“中国音乐史家”所供给他的材料;才能替祖国的这种光荣传统理直……(32)
杨先生之后,黄翔鹏先生(1927-1997)秉承这一学术理念进而提出“曲调考证”。黄先生说:
把中国古代音乐史从文字的历史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富有实践意义的谱例宏富的历史,这也是杨先生在世时念兹在兹的事情。反正先生做不完的事情,学生接着做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33)
经过艰难而苦心的研究,黄先生已从传统音乐中考证出《望江南》、《万年花》、《念奴娇》、《菩萨蛮》等十余首唐宋曲调。(34)
80年代中期,冯文慈(1926-)教授沿用历史学界“逆向考察”的概念,把这种的研究方法称之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并通过许多研究实例(包括对杨荫浏的研究),指出它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35)今天,这种研究方法已成为这门学科中的基本方法之一。
而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所列举的日本保留的、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唐代流传过去的音乐,在日本长达一千多年时间的保存中,即使在有意识的传承当中,音乐也必定发生演变。前引金文达教授文章又认为:
……日本派人赴唐学习音乐的目的,主要是借鉴唐乐,走自己的路,使之日本化,从而创造自己的宫廷音乐,即日本的雅乐。……由此可见,田边尚雄的中国唐乐即寓于日本雅乐之中,并在两者之间画个等号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实事求是地承认日本雅乐是在借鉴唐乐后,日本自己创造的一种宫廷音乐,既符合事实,又不抹杀自己民族的创造性。这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事情。(36)
此后,金文达教授承担了国家教委课题“日本雅乐的实质”,进而对日本雅乐进行剖析。先后发表了题为《日本雅乐的实质》三篇论文,其副题分别为:借唐乐之名,取印度及其他多种音乐之实的一种混合物(37);为其中的中国古代已失传的乐曲而正名(38);使外来音乐日本化的几个步骤(39)。首篇论文一开始就申明:
研究的目的是弄清中国是否真如日本所说那样“在中国,则隋唐之乐,今皆佚灭无存,而日本今尚保存之。故欲研究隋、唐音乐之性质,至日本方面考之殊为便利”。这个问题也曾是前辈们的一个苦恼。……笔者愿意继承他们的遗志,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承担起来。(40)
金文达教授说的“前辈”,应该就有杨荫浏。
199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冯文慈教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作者在书中对唐乐传入日本等相关问题做了详细的描述:
日本“雅乐”吸取唐朝的宫廷音乐,除了宴飨所用的燕乐外,还有散乐,而不是祭祀等等场合所用的雅乐。日本“雅乐”的概念和中国传统雅乐的概念已经迥然不同。……(41)
唐乐被日本“雅乐”吸取以后,在奈良时代(710-794)还保持着它本身的风格。但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以后,内容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经历了日本对它的研究、消化,使之适合日本自己的口味,即产生了日本化的改造。(42)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于隋唐音乐的研究,硕果累累。唐代音乐在民间通过千丝万缕的渠道延续、留存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内容之丰富,已经举不胜举。但田边尚雄所说的“隋唐之乐在中国皆佚灭无存”等语,在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影响仍然不小。1983年秋天岸边成雄来华讲学,在中央音乐学院(地点小礼堂)讲学时,演讲中仍然说出了类似的话,笔者在场聆听,这些话犹觉在耳。2009年11月,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中日韩雅乐舞国际研讨会”,音乐厅演出之前日本学者的发言也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当时笔者也在场。一个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在今天的学术研究面前已经是完全被淘汰的中国音乐史学旧观点,还能出自今人之口,在令人诧异的同时,就不得不去做历史反思了。
是非得失,唯后人思之
田边尚雄作为20世纪初研究亚洲音乐的早期音乐学家,他的亚洲音乐、中国音乐的研究影响是相当大的。1923年他曾应邀在北京大学讲学,题为“中国古乐之价值”,由周作人(1885-1967)担任翻译。(43)同年,田边尚雄在上海聆听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演出后,称这个乐队是“亚洲第一交响乐队”(44)。他撰写的《孩子们的音乐》、《生活与音乐》(45),20年代曾由丰子恺(1898-1975)翻译介绍到中国等等。但是,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大东亚音乐”政治倾向是存在的;他的“中国音乐外来说”,以及它在林谦三、岸边成雄研究中的影响,也都是存在的。前引日本学者植寸幸生文章又叙述道:
1941年,日本《东亚的音乐》唱片选集发行,其解说的文字由田边尚雄执笔。1943年,田边尚雄在该解说文字的基础上出版了《大东亚音乐》小册子,内容包含满洲、中国、蒙古、爪哇、巴厘、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46)
……时逢“大东亚共荣圈”的提倡逐渐正当化,田边尚雄积极应和这一提倡,在其1940年的著述中开始出现“大东亚音乐”的用语。(47)
然而,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对中国古代音乐日本音乐、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音乐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述,在中国、亚洲甚至是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中国学界相当高的学术评价。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了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1998年商务印书馆又重版。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钱稻孙翻译的中文版196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96年再版。岸边成雄的著述(论文和论著)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上世纪90年代,黄翔鹏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高兴,他的硕士论文题即为《简论岸边成雄先生的唐代音乐史研究》,文章开头即说明:
……学术界自本世纪以来随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如岸边成雄、林谦三、劳伦斯·毕铿等,克服了语言、民族心理等方面的障碍,在唐代音乐研究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惜由于较少地得到翻译介绍,我们国内音乐学界知之甚少。为了吸收他们的有益经验,克服我们在学术信息方面长期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弱点,改进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故对日本著名学者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研究试作探讨。(48)
2005年岸边成雄逝世,国内著名音乐学学者王耀华(1942-)教授撰写了《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文章全面、高度评价了岸边成雄的研究成果,称他是“东方音乐学界的先驱和泰斗”(49)。
回到1944年杨荫浏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对田边尚雄的批评,其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杨先生的话既指出了他的《中国音乐史》中“拗曲了部分事实”,也道明了该书的“大东亚文化”的政治倾向。义正词严,无可非议。
再回到文章开头杨荫浏所说的“我在自己的音乐史著述中一般不引用他们的材料,这表示了我的严肃态度,也是我的民族自尊的一种心意,他们应该原谅”。这段话可以说是国内五六十年代社会背景下的学术思想。其时,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激烈,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文化正在不断高扬;日本侵华的历史阴影还远远不能在中国人心灵上散去。杨荫浏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表达出一种政治的和民族的态度,也不为过。而且杨荫浏又说:“(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音乐资料,假古董不少,我们要严防上当”;“日本的琵琶、笙的演奏水平较低,我们须心里有数,不能盲目。”这是在告诫后学:在对待日本的中国古代音乐资料、日本的琵琶和笙,要保持一种冷静和清醒的态度。杨先生或许不知道他的这次讲课会是“最后的课”,但至少,在杨先生的学术思想中,这是一件不能忘却的事情。
杨先生去世后的第三年(1987),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郑珉中(1923-)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了《论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一文(50)。文章对日本正仓院的国宝“金银平文琴”——这张历来被日本学者视为从中国唐代流传过去的“舶载品”(岸边成雄1983年来华讲学时称之为“真正的唐琴”(51))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
……在形制方面、在髹漆工艺方面、在铭文腹款方面、在装饰风格方面,皆于我国的制作不甚相合。它应该是日本人依据我国“宝琴”的特点所制造的,而不是中国人的制作,所以才发生了日本有相似之作,而为中国所无的现象。
也是在这一年,金文达教授开始针对日本雅乐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52)
一点余绪
新中国建立以后,田边尚雄曾几次来华访问:
——1951年,田边尚雄率日本音乐家代表团访华。(53)
——1956年,以田边尚雄为团长的日本文化人士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国内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招待。(54)
——1982年,田边尚雄之子田边秀雄(1913-)来北京登门拜访杨荫浏。(55)
——2003年,田边秀雄向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捐赠一批音乐图书和唱片。据有关媒体报道,这批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图书中还有不少是明清时期的珍贵版本。(56)
联系前述史实不难看出:新中国建立后,田边尚雄在访华的同时,并没有改变他“隋唐音乐在中国已佚灭无存”的观点;杨荫浏在接待日本音乐界人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
20世纪过去了,老一辈的音乐史家都已作古了。当年的热情洋溢、当年的慷慨激昂,都已经付诸东流。留下的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证据,它静静地告诉了后人这一段不平凡的音乐史学史。音乐史学的发展自有它的客观条件,音乐史家难以摆脱复杂的政治社会和人文时代的种种影响,学术研究往往和社会政治倾向交织在一起,甚至难以扯开、分离。但史料的偏向和不实、研究方法的偏差,是导致学术本身偏离科学性的根本原因。
两千年前,“不虚美,不隐恶”的古代史家司马迁的史学风范,早已为学界树立起楷模。如何书写历史,曾是前贤们深思的问题,今天,它仍然是后学们不断思考、进取的问题。
音乐史学史留给后人的既是经验,又是教训。
注释:
①乔建中《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5—14页。
②同注①。
③[日]植村幸生撰、周耘译《田边尚雄与东洋音乐的概念》,《黄钟》2010年第2期,第81—87页。在这篇文章之前,赵维平《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载《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中对此已有介绍。
④魏廷格《反思中国现代音乐文化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16—23页。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15页。
⑤田边尚雄著、陈清泉译《中国音乐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页。
⑥同注⑤,第118页。
⑦同注⑤,第99页。
⑧同注⑤,第105页。
⑨同注⑤,第181页。
⑩同注⑤,第49页。
(11)同注⑤,第325页。
(12)[日]林谦三著、钱稻孙译《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5页。
(13)同注(12),第296页。
(14)俞人豪《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音乐探索》1986年第3期,第46页。
(15)同注⑤,第35页。
(16)同注⑤,第36页。
(17)庄锡昌、孙志民《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18)郑祖襄《“弦鼗”研究的争议和讨论》,《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1期,第58—66页。
(19)金文达《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某些误解》,《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第60—67页。
(20)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第6—9页。
(21)同注(20)。
(22)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
(23)同注(22),第3页。
(24)李纯一《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中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
(25)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上海万叶书店1952年版,第336页。
(26)同注(25)。
(27)同注(25),第337页。
(28)同注(25),第336—337页。
(29)曹安和《杨荫浏和音乐史》,《人民音乐》1985年第4期,第26—27页。
(30)杨荫浏《音乐史问题漫谈》,《音乐艺术》1980年第2期,第12—18页。
(31)杨荫浏《智化寺京音乐》,收录《杨荫浏全集》第6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2)转引自田青《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第62—76页。
(33)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谈黄翔鹏的“曲调考证”及其学术价值》,《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第5—9页。
(34)同注(33)。
(35)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5页。
(36)金文达《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某些误解》,《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第60—67页。
(37)金文达《日本雅乐的实质——借唐乐之名,取印度及其他多种音乐之实的混合物》,《音乐研究》1993年第3期,第47—57页。
(38)金文达《日本雅乐的实质——为其中的中国古代已失传的乐曲而正名》,《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第81—93页。
(39)金文达《日本雅乐的实质——使外来音乐日本化的几个步骤(续篇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53—60页;《日本雅乐的实质——使外来音乐日本化的几个步骤(续篇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64—72页。
(40)同注(37)。
(41)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42)同注(41),第113页。
(43)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44)田边尚雄《中国、朝鲜音乐调查纪行》,转引自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音乐研究》2010年第5期,第86—97页。
(45)见《丰子恺年谱》,收入殷琦、丰华瞻《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6)同注③。
(47)同注③。
(48)高兴《岸边成雄先生的唐代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1期,第109—125页。
(49)王耀华《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音乐研究》2005年第2期,第64—74页。
(50)郑珉中《论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4期,第25—36页。
(51)岸边成雄《日本正仓院乐器的起源(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49—54页。
(52)金文达这方面发表的研究论文第一篇是《传奇式的人藤原贞敏——其人、其事及其乐器》,《交响》1987年第3期,第40—42页。
(53)解嵋、武陵《古谱名曲赠知音》,《中国艺术报》2003年6月24日。
(54)新华社报道《对外文协欢宴日本文化人士访华团》,《人民日报》1956年9月29日。
(55)翟风俭《杨荫浏:中国宗教音乐的拓荒者》,《中国宗教》2009年第2期,第22—25页。
(56)同注(53)。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