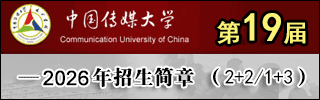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戏曲音乐的历史范型及其创造性转换
作为文章标题的句式,是从众所周知的“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点化而来的。从戏曲表演“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要求来看,音乐(歌)和舞蹈(舞)倒是具有同一性的。它们共同标示出戏曲表演的审美取向,也共同彰显出戏曲艺术的灵魂居所。
一、戏曲艺术是有别于歌剧艺术的音乐戏剧
在戏剧艺术中,音乐戏剧是相对于非音乐戏剧而言的。实际上,除了话剧之外,举凡歌剧、舞剧和蔚为大观的戏曲都属于音乐戏剧。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音乐戏剧是戏剧艺术的主导方面,是舞台演艺的主要构成。强调音乐戏剧在戏剧艺术中的地位,是为了说明戏剧艺术的艺术语言主要是在对日常生活形态的偏离中建构起自己的美学原则的。因为所有音乐戏剧的演剧样式,其艺术语言都是高度偏离日常生活形态的。
以日常生活形态的语言交流为参照,舞剧的偏离远甚于歌剧;而“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我以为介于两者之间。同是音乐戏剧,戏曲之有别于歌剧,不仅在于戏曲是唱、念、做、打“四功”的综合运用,而且在于二者音乐形态构成方法和音乐手段实施理念的差异。与歌剧音乐的作曲理念相比,人们都注意到注重“程式化”表现的戏曲音乐是“传统曲调的重复运用”(何为先生语);在我看来,称戏曲音乐为“历史范型的适时活用”可能更为恰切。因为较之“传统曲调”而言,“历史范型”本身包含着一个建构过程;而“适时活用”比“重复运用”更能道出戏曲音乐创作的本质。
除“创作”的音乐和“活用”的音乐外,戏曲与歌剧在音乐方面的差异还有许多,其中比较重要的认识是:歌剧主要是和声艺术,而戏曲主要是旋律,特别是节奏强化的旋律艺术。在这一基础上,作为演奏形态的戏曲音乐,其功用主要在于为演唱“托腔保调”。因此,不同地方戏曲的音乐演奏,都运用能强化演唱风格的主奏乐器(如昆腔用曲笛、皮黄腔用京胡、梆子腔用板胡等),而伴随演唱的演奏以“点板清唱”、“紧拉慢唱”等多种方式,形成与演唱异曲和鸣、殊途同行的效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戏曲音乐为适应场景“戏剧性”和人物“性格化”的需要,使“传统曲调”的“历史范型”有了“行当唱法”的多种变异。这在戏曲人物的性格塑造和戏曲观众的审美接受间找到了最具实效的纽结方式。
二、戏曲音乐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声腔体系
戏曲音乐与方言关系的密切性是不言而喻的。纵观戏曲音乐的历史流变,其实又可视为其地域播布的交互飚扬——元代是南北曲的交汇时期,明代是昆山腔、弋阳腔等南曲的主导时期,清代则是梆子腔、皮黄腔等北曲的坐庄时期。这种“交互飚扬”(其中当然也不能避免“交互融通”)其实是中央政权“民族变更”在戏曲审美中的投影。这使我们从根源上认识到,以戏曲音乐基本的声腔体系,是建立在瓯、越方言基础上的南曲和建立在晋、陕方言基础上的北曲。任半塘先生著《唐戏弄》,认为在闽南和晋南保留着古戏的遗韵,或许正是南曲源泉和北曲根本之存留。
南、北曲之基本体系随着方言的种属分布而不断分化,使戏曲艺术的“地方分化”成为这门艺术因繁衍而繁荣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今日谈及戏曲艺术,不仅会想到它是中国所特有,而且会想到它有地方之分野,以至于“地方戏”成为除京、昆之外的戏曲艺术的统称。从音乐的角度来看戏曲的“地方分化”,可以看到众多的戏曲基本上都归属在昆腔、京腔、梆子腔和皮黄腔四大声腔系统中。而从方言的角度来看戏曲的“地方分化”,我们则注意到,北曲播布的地区皆为北方方言区,南曲播布则有吴方言、赣方言、鄂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之多。也就是说,南方方言区比北方方言区有更大的差异性,而这也就意味着其声腔系统可能有更大的丰富性。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北曲的“地方分化”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文化整合,这使得梆子腔、皮黄腔腔系的各剧种形成了一种“板式变化”的“作曲”机制。而南曲的“地方分化”,一方面是昆山腔以高蹈为地标的,试图“以雅化俗”;另一方面则是弋阳腔以广布为取向,用史家们的话来说,是“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是“乡语错用,改调歌之”。南曲在向差异性较大的南方各方言区的播布中,其声腔系统得到极大的丰富,因而形成了与“板式变化”迥然有别的“曲牌联套”的“作曲”方法。曲牌丰富,才有“联套”的可能;“曲牌”有限,就要从有限的曲牌中去开掘“板式变化”的可能性。南曲的“曲牌”较北曲更为丰富,从根源上来说是基于方言差异的幅度较大,而这又是由北方“一马平川”和南方“万壑争流”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三、曲牌联套和板式变化构成戏曲音乐的基础形态
戏曲音乐的研究家都注意到其“程式化”表现的特征。何为先生认为,戏曲音乐的程式表现就其基本形态而言,无非是“曲牌联套”和“程式变化”。而已经成型的四大声腔系统中,昆腔腔系和高腔腔系的表现程式是“曲牌联套”,梆子腔系和皮黄腔系则以“板式变化”为其表现程式。按专家们的阐述,所谓“曲牌联套”,是把许多不同曲牌的曲调联成套曲来讲述戏剧故事或抒发人物情感。不同“曲牌”,有与之对应的不同长短句体来吟唱,“联套”的方式虽变化多端,但一是强调用宫调来组织,二是强调以节奏缓急定顺序。所谓“板式变化”,是在区别于长短句的“上下句”基础上形成的曲式结构。这种对偶体的曲式结构,主要通过变奏来发展,在某些基本板式上形成了慢板、原板、二六、流水、快板、摇板、散板等丰富的变化,“板式变化”的程式表现,一要择调,二要定板,三要安腔。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板式变化”作为曲调发展的一种方式,似乎与古典歌剧主题变奏的作曲方式较为相似;而“时尚”音乐剧的创作,曲调的组织亦有些“曲牌联套”的意味(当然二者既非“板式”亦非“曲牌”)。其实,无论是歌剧还是戏曲,其音乐创作都讲究“有耳音”,也即尊重观众的“接受机制”和“期待视野”。研究者们认为,作为戏曲音乐程式表现的两种基本曲体,“曲牌联套”的前提是对曲调广为罗致,而“板式变化”的前提是对曲调深度开掘。事实上,这种差异在先秦的周之《大武》和楚之《九歌》等古歌舞剧艺术表现中就已然现出端倪——《大武》六出,从《诗·颂》的有关篇章来看,其戏剧情节的展开就颇类“板式变化”的展开;而《九歌》的章阙,其对诸多戏剧性格的刻画就呈现为“曲牌联套”的形态。
指出这一点,就说明戏曲音乐的程式表现沉淀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心理。戏曲音乐界认为戏曲音乐的“程式化”表现与其“民间性”传承分不开,而这种“民间性”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有“礼失求诸野”的因素。特别就北曲诸声腔而言是如此。论及戏曲音乐程式化与民间性的关系,我们都会注意到民间歌舞、说唱给戏曲音乐以滋养。我们也注意到,近代以来地方戏曲新剧种的出现,似乎由民间说唱孕育而来的发展得更迅速更完备。不仅北方的评剧是如此,南方的越剧也是如此。但事实上,我们不可忽略由民间歌舞而衍生的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等所蕴藏的潜质。当民间说唱由“坐唱”经分角色“彩唱”而演进为昆剧、京剧奠定其范型的“戏曲”之时,民间歌舞也正由歌舞小戏向“中国特色的音乐剧”走去。不少关心中国戏曲前途的有识之士认为,南方近代以来兴盛的歌舞小戏,与其亦步亦趋地走向范型化的“戏曲”,莫如以当今国际舞台上走红的“音乐剧”为参照,实现戏曲艺术的跨越式发展。而歌舞小戏“曲牌联套”的音乐创作方式正提供了这种可能。
四、戏曲音乐要实现历史范型的创造性转换
如前所述,戏曲音乐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声腔体系,戏曲音乐的程式化表现基于其民间性传承;这后一点确切来说,又是基于其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民间性”。艺术的功能,无论怎样去阐说,诸如认知、教化、娱兴、审美……其基本的前提是“交流”。事实上,在一定方言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声腔体系,其出发点也是为了“交流”,为了便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交流”;而声腔体系特色的形成是这种“交流”不断反馈、不断调适、不断建构的结果。从“交流”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我们发现戏曲艺术在当前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其音乐表现“程式化”的困境。这一方面是在特定地域、特定人群中“有效”的表现手段,在跨地域、跨人群的交流中变得“有限”了;另一方面,当“程式化”驻足的“民间性”成为历史,在一定历史时期曾经“有效”的“程式化”手段在时尚的“民间性”面前变得“有限”了。在我看来,要使戏曲音乐超越“有限”而重建“有效”,就必须实现其历史范型的创造性转换。
我认为,戏曲音乐“历史范型”的创造性转换,最重要的便是应当正视我们从乡村文明走向都市文明的时代场景变化。京剧艺术在上一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以为就是初步建立了这门艺术的都市品格。诚如京剧研究家徐城北先生所言,自谭鑫培以降,梅兰芳和周信芳分别在适应并征服北京、上海观众的过程中,培育了京剧艺术的都市品格。只是在当时,上海的“洋场”较之北京的“皇城”更具现代都市品格的意味。因此,就京剧艺术的都市品格而言,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发育得更为充分。事实上,从乡村文明走向都市文明,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地域”的迁徙,更在于一种“品格”的提升。不仅京剧艺术是如此,近代以来许多地方戏的跨越式建构,也都与其进入都市发展有关——比如从嵊州进入上海的越剧、从唐山进入天津的评剧以及从黄梅进入安庆的黄梅戏等。
对于乡村文明而言,都市文明不仅是一种生活节奏的变更和一种生活趣味的改造,它还孕育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民主气氛和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我国都市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京剧艺术得以迅速地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多声腔剧种”所具有的极强的兼收并蓄的能力。我以为,“多声腔”本身就隐含着“跨地域”的意味,这与都市文明在一定“地域性”标志下所拥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一致的。无论有怎样的地域局限,开放性和包容性都是都市文明所拥有的品格,它可以包容建立在某一方言基础上的声腔体系,却拒绝认同那一声腔体系的自足和自闭。事实上,即便是地域性特征格外明显的都市,“方言”由于人群的混杂和交流的便易也在逐渐淡化;并且,都市文明所培养的“民间性”也早已不是乡村文明所陶冶的民间歌舞和说唱。也就是说,都市文明无论从“开放性”还是从“民间性”的视角来看,都在瓦解“方言”并进而挑战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声腔体系。在固守“体系”和扩大“交流”之间,我们更应当重视后者。实际上,京剧艺术对诸多地方剧种优秀剧目的移植,就是在扩大“交流”理念指导下的举措。这成为其音乐的历史范型实现创造性转换的一条重要路径。
与“方言”瓦解接踵而至的,是都市文明对戏曲声腔“本嗓”的疑虑。顾名思义,“本嗓”是基于“方言”言说的“原生态”噪音,为便于“方言”的言说和演唱,戏曲艺术还形成了以特色乐器为主奏的音乐伴奏。如何调节“本嗓”演唱和科学发声之间的音色关系,如何调节特色乐器和伴奏乐队的配器关系,其实也是戏曲音乐实现创造性转换中不得不正视的课题。在这里,简单地认为在美声唱法指导下的发声、在管弦乐队编配下的演奏“更科学”,可能会使戏曲音乐在创造性转换中步入迷津。在我看来,通过正确处理上述关系而实现创造性转换,一是仍要从更深层上理解戏曲音乐的“民间性”原则。正如表现彝族生活题材的京剧《凤氏彝兰》吸收彝族民歌而成功实现转换、塑造广西人物形象的桂剧《大儒还乡》吸收广西民歌而丰富声腔体系一样,表现都市题材或服务都市大众的戏曲艺术,也不能不从都市生活的“民间性”中汲取养料,这当然包括都市生活“民间性”中的青春意气和时尚风情。其二,应当更加重视戏曲音乐的“戏剧性”原则。既往,我们是在戏曲艺术的“程式化”表现中来营造“戏剧性”,不仅有音乐的曲牌来对应而且有角色的行当来定位。戏曲音乐的“戏剧性”,固然要重视抒情唱段和叙事唱段的合理布局,但更要审度戏剧性格的底蕴和戏剧冲突的走向。越剧艺术历史进程中几次大的音乐创新,比如“四工调”及“尺腔调”的先后出现,就是刻画戏剧性格、揭示戏剧冲突而产生的效应。其三,对戏曲音乐的“时尚性”原则也需加以正视。中国戏曲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有如此深厚的根基和如此繁茂的枝叶,本身就有着“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的传统。今日许多看来“老态”的剧种,当年其实也都“时尚”过。昆曲的“水磨调”在当年是时尚,京剧用胡琴取代笛子来托腔在当年也是时尚,越剧直言以话剧作为自己的“奶妈”之一更是时尚得了不得……实际上,今日许多戏曲剧种往往是“心态”比“状态”显得更“老态”——争相将自己定位于“遗产”就是心态未老先衰的一种表现。无疑,对于中国戏曲需要保护和扶持,但更需要创新和发展;对于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演艺的“活态文化”,说是“遗产”其实对那些仍在生长、仍然青春的演艺品种并不确切,而视其为“遗产”并强调对其“原汁原味”的保护,则更是遏止了其“与时俱进”、“老树新花”的可能。就以当下的戏曲音乐创作而言,京剧《梅兰芳》以交响化的音乐体现时尚,京剧《文成公主》以京剧、藏戏强反差的结合体现时尚;更有许多地方戏曲,通过现代题材、青春歌舞的表现追求时尚……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传统戏曲的扶持重点在扶持“创新”,而传统戏曲的发展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实现戏曲音乐历史范型的创造性转换,根本在于“民间性”的坚守、“戏剧性”的维护和“时尚性”的求索。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