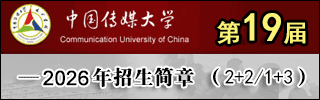来源:国内高校 浏览: 次 作者:中国艺考网
在我还年轻时 — 也就是写下《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那时 — 曾问过自己这么个问题:“计算机程序会有写出优美音乐的那一天吗?”然后做出了如下推断:“计算机作曲程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产生什么有新意的成果……‘我们就快能用一台批量生产的二十块钱邮购获得的预置程序桌上型音乐盒子中那贫乏的电路写出肖邦或巴赫假如活到今日将写出的曲子’ — 这种念头,哪怕只是想一想 (事实上我的确听人如此提过),也已是对人类心智深度的一种荒诞可耻的误估。”那时我的调子就是如此这般。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是如何看待这种推断的呢?说不准。这些问题已困扰我多年,直到现在还是没找到一个确定的解答。 1995 年春,我偶然发现了 David Cope 的《计算机与音乐风格 (Computers and Musical Style)》一书,他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一位教授。在书中我注意到了一首模仿肖邦风格的马祖卡舞曲,它是由 Cope 的 EMI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 (音乐智能实验)”一词的缩写) 程序所谱的。之所以能引起注意,是因为作为毕生的肖邦爱好者,我觉得没什么伪托肖邦的曲子能骗过我的眼睛。所以我直接在钢琴上即兴把这首 EMI 马祖卡反复弹了好些次,每弹一次,我的困惑与惊讶便增加一层。
尽管能间或能听出些小瑕疵,这首曲子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似乎在“倾诉”着什么。如果谁告诉我它是出自人手,我绝不会怀疑它的表现力。这首曲子听来有些怀旧,带点波兰味道,而全无抄袭嫌疑。它是崭新的,而又毫无疑问地刻上了“肖邦风格”的烙印,却不令人觉得情感空乏。我的的确确受到了震撼:抒情的乐曲怎么能从一个从未听过一个音、从未活过一秒钟、从无一丝一毫情感的程序中写出来?
越是纠缠于此,我就越是困扰 — 但也越是为之着迷。这里确实有个不符情理的矛盾,狠狠将了我一军。但我不会就此拒绝承认,认为 EMI 无关紧要或缺乏乐感,不然这只能说明我的怯懦心虚而已。我要直面矛盾,与这个怪异的程序奋战到底,因为它动摇了早在我内心深处的信念:关于音乐的神圣地位的信念、关于音乐是人类灵魂的终极圣地的信念。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奔向思维力、洞察力与创造力之前的最后障碍。
如果我只是看过 EMI 的架构而未听过任何它的产出,我肯定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尽管 Cope 在 EMI 上花的功夫比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者在任何项目上花的功夫都要多得多,EMI 的基本原理在我看来并不新鲜,甚至显得没什么前途。颠覆我看法的是 EMI 所谱的曲子。
后续的几个月里,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地方做了关于 EMI 的讲座,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几个听众对 Cope 模拟艺术创造力上的这一妙着感到沮丧,几乎没有谁感到威胁或担忧。反之,我却觉得某种能显示人类深邃思维的崇高性不复存在了。对我来说,不仅丢脸,还很可怕。
EMI 中最深层次的原理是被 Cope 称作“重组音乐 (recombinant music)”的原理 — 从一名作曲家的作品中识别出不同类型的重现结构,然后以新的排列来复用这些结构,依此产生一份“同样风格下的”新作品。你可以想象 EMI 在学习了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后,自行谱出《贝多芬第十交响曲》的情景。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是如何看待这种推断的呢?说不准。这些问题已困扰我多年,直到现在还是没找到一个确定的解答。 1995 年春,我偶然发现了 David Cope 的《计算机与音乐风格 (Computers and Musical Style)》一书,他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一位教授。在书中我注意到了一首模仿肖邦风格的马祖卡舞曲,它是由 Cope 的 EMI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 (音乐智能实验)”一词的缩写) 程序所谱的。之所以能引起注意,是因为作为毕生的肖邦爱好者,我觉得没什么伪托肖邦的曲子能骗过我的眼睛。所以我直接在钢琴上即兴把这首 EMI 马祖卡反复弹了好些次,每弹一次,我的困惑与惊讶便增加一层。
尽管能间或能听出些小瑕疵,这首曲子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似乎在“倾诉”着什么。如果谁告诉我它是出自人手,我绝不会怀疑它的表现力。这首曲子听来有些怀旧,带点波兰味道,而全无抄袭嫌疑。它是崭新的,而又毫无疑问地刻上了“肖邦风格”的烙印,却不令人觉得情感空乏。我的的确确受到了震撼:抒情的乐曲怎么能从一个从未听过一个音、从未活过一秒钟、从无一丝一毫情感的程序中写出来?
越是纠缠于此,我就越是困扰 — 但也越是为之着迷。这里确实有个不符情理的矛盾,狠狠将了我一军。但我不会就此拒绝承认,认为 EMI 无关紧要或缺乏乐感,不然这只能说明我的怯懦心虚而已。我要直面矛盾,与这个怪异的程序奋战到底,因为它动摇了早在我内心深处的信念:关于音乐的神圣地位的信念、关于音乐是人类灵魂的终极圣地的信念。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奔向思维力、洞察力与创造力之前的最后障碍。
如果我只是看过 EMI 的架构而未听过任何它的产出,我肯定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尽管 Cope 在 EMI 上花的功夫比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者在任何项目上花的功夫都要多得多,EMI 的基本原理在我看来并不新鲜,甚至显得没什么前途。颠覆我看法的是 EMI 所谱的曲子。
后续的几个月里,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地方做了关于 EMI 的讲座,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几个听众对 Cope 模拟艺术创造力上的这一妙着感到沮丧,几乎没有谁感到威胁或担忧。反之,我却觉得某种能显示人类深邃思维的崇高性不复存在了。对我来说,不仅丢脸,还很可怕。
EMI 中最深层次的原理是被 Cope 称作“重组音乐 (recombinant music)”的原理 — 从一名作曲家的作品中识别出不同类型的重现结构,然后以新的排列来复用这些结构,依此产生一份“同样风格下的”新作品。你可以想象 EMI 在学习了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后,自行谱出《贝多芬第十交响曲》的情景。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