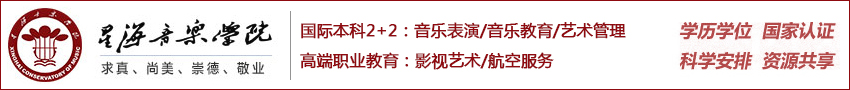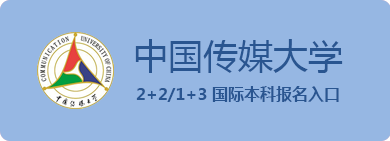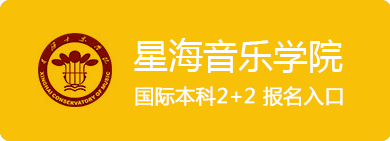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向度
内容提要: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也同时表明了一种研究趋向和维度:“系统论”说明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始终以“整体”观照“中国音乐”,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微观研究,都注意从“整体”出发并最终回到“整体”;“发生论”说明把握一种事物的当下存在,首先应溯其本源以及生成的相关社会环境,然后探究其演化脉络;“正统论”提醒音乐史、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应当充分关注“少数民族政权”如何对“礼乐”进行继承与扩充。文章指出:研究音乐本体,是音乐学的基本任务和首要任务。以“音乐文化”之名进行研究,绝不是要“去‘音乐本体’化”,而是在完成这个“基本”“首要”任务的同时充分注意到:音乐是人的创造、承载、传播,而不只是音响、器物、数字;“音乐文化”是一个整体,研究不应只做“分割”与“抽取”,还应回到整体;音乐本体分析要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相结合。
关 键 词: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向度/思维基础
作者简介:郭威,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0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下传统音声形态中的‘曲子’积淀研究”(编号14CD11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京畿汉族民间宗教宣卷音乐文化的考察与研究”(编号16JDYTA012)阶段成果。
201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国音乐学》杂志社共同举办了“理念·视角·方法: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汇集了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各领域的数十位学者,围绕“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定位与方法论”展开探讨,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于“如何认知中国音乐史”的广泛讨论,争论焦点即是“中国音乐文化史”。①
有关“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或者说有意识强化这个概念,并在这个概念下展开研究和探讨的,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为代表,近年有两个学术事件值得关注:其一(整体)即是上述会议的召开以及《中国音乐学》同名专栏讨论、会议文集出版(2016);其二(个体)是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于2014年出版,该著集合了项阳近年在“历史”“田野”两方面的诸多成果,并明确以“中国音乐文化史”为题予以强调。
若将回溯的时间稍作延伸,则可知“音研所”以与“中国音乐文化史”概念相关的“音乐文化”之名开展的学术工作还有:①自2000年始,由音研所乔建中、张振涛两任所长主导,陆续出版具有“丛刊”性质的“音研所”文集《音乐文化》(见表1)

②200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博士招生方向设“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研究”,该专业方向的介绍是:“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研究,就是要在文化的整体理念下接通音乐史和传统音乐两个既有学科,加强与大学术界的联系,借助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而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具体事象产生新的认知,将我们的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
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对“音研所”往年组织的活动及其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所做的粗略统计来看,这种对“音乐文化”的注重,乃是一种“传统”(见表2、3)。

以上所列皆是严谨的学术工作,当事人在使用“音乐文化”时自然有着与使用“音乐”一词不同的认识与考虑。尽管学者们对“音乐文化”一词理解各有不同,但这本身就表明其处于一种无法用“音乐(本体)”表达“音乐文化”的语境之中。②足见“音乐文化”作为学术用语的必要性与不可替代。
回到“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上,从当下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也同时表明一种研究趋向和维度。
一、“系统”论:接通的意义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按照一定的结构所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1]P61“整体”“要素”“结构”“功能”乃其基本要点。“整体”则是其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始终以“整体”观照“中国音乐”,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微观研究,都注意从“整体”出发并最终回到“整体”。
以“音研所”近年的学术工作为例,如:秦序研究员的“秦礼研究”“魏晋六朝音乐文化研究”接续了李纯一先生《先秦音乐史》(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时名为“中国音乐史第一分册”)的研究路径,以“心有全豹”之视野而逐一进行断代研究。此外,李岩研究员对于近现代中国音乐史料的挖掘与史实的梳理;李玫研究员对于乐律学文献的爬梳与研究;林晨以“琴”为轴,从“书、谱、器、人、演”全方位通研古今琴“事”;王清雷承继前辈师长之路,对全国音乐文物持续搜集、整理、研究;冯卓慧从乐种的视野、用实证的方法进行音乐科技的研究;李宏锋“宫调理论与实践历史”的研究;陈瑜对于道教音乐全面的挖掘与整理;孙晨荟对于中国基督教音乐的研究等等。乃至于《中国音乐年鉴》的编撰、《中国音乐学》的编辑,都体现出学者们对于“中国音乐”研究的“整体”,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国音乐学”的“系统”。项阳研究员是这一研究理念的极力倡导者,其明确以“接通”“史论结合”进行“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并且在身体力行研究之外,还指导了一批专题研究,围绕“制度·礼俗·音乐”成系列地铺陈开来。(见表4)

上述研究共同的特征即是基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理念。各专题从“中国音乐发展脉络”的“整体”出发,细致分析对象但不囿于对象本身,始终注重“国家制度”“礼俗用乐”之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深刻影响,尽可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局限。这恰符合系统论所指出的:“要素是系统的基础,没有要素,就不可能形成系统这样一个整体。但要素只是形成系统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这些要素不以一定的结构方式组合起来,那么这些要素就不能形成一个具有系统性质的有机整体,而只能构成一个‘堆’。”[1]系统论有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P51其意即在于:“系统的整体具有系统中部分所不具有的性质,系统整体不同于系统的部分的简单加和即机械和,系统整体的性质不可能完全归结为系统要素的性质来解释。”[3]P205当下一些个案研究无法更进一步“知其所以然”,原因即在于缺乏这种理念上的整体认知。
笔者曾以项阳的研究为例,阐述了“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模式:[4]
原则:接通
视域:宏观—微观;历史—田野—传统
制度:礼节—乐藉—民间礼俗
空间:整体—区域;中央(宫廷)—地方(官府、王府、镇戍)—民间
时间:历时的传承与变化
材料:文物、文献、活态遗存
图1 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模式
上述研究模式不同于“管窥式”的专题音乐史研究,其首先在研究理念上充分考虑到“中国音乐”之于中国社会制度与观念的历史语境,进而开展个案研究并最终回到“整体”上对个案进行分析与阐释。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反映出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一个研究向度,即系统论。
二、“发生”论:“音乐本体·承载主体·国家制度”的研究视角
郭乃安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学术理念“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文化史即是对于这个理念的接受并作为研究的基础。从这个理念出发,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关注到“承载群体”与“国家制度”,这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特征,其本质就是“发生学”,或可称“发生”论。项阳先生指出:“关于发生学,学界是将自然科学的理念借鉴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把握一种事物的当下存在,溯其本源以及生成的相关社会环境,然后探究演化脉络。任何成为传统者,肯定有着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若只以当下样态而忽略复杂的演化过程,难以厘清,故从‘逻辑起点’上梳理尤为重要。”[5]P1-2笔者的博士论题《曲子的发生学意义》即是在这种认识下提出的。
中国音乐数千年中有很多如今人所谓的“专业创作”的音乐,兴于隋唐的曲子即是其一,杨荫浏先生称其为“艺术歌曲”。笔者据为数不少的传世文献(官书正史、笔记小说、诗词歌赋、地方志书均有)指出:曲子是专业创作,乐人是其承载主体;乐人这个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群体背后则是一个具有高度管理水准的国家机制——乐籍制度;基于这种国家制度,构建起一个音乐的创承与传播体系——乐籍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形成一个“音声技艺的国家体系”(见图2)。这个体系形成了当时的所谓音声技艺的“主流”与“风尚”,曲子就是其中最为重要者之一:其一,它是乐人习乐的基础;其二,它是作乐制曲的基础;其三,它是当时及后世众多音声技艺的“母体”。

图2 国家制度下的音乐传播
学界的研究不论是音乐史学,还是传统音乐,对于现象和个体事件的关注,远多于对音乐现象生成机制的关注。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音乐在历史上依托什么发生、发展,传承、传播?何以形成所谓的“高文化”现象?何以形成当下全国各地的丰富的一致性存在?……这些以现代传播学的理论是无法完全解答的,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深入探究当时的“发生”机制。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应当注意到一个被制度学界,尤其是研究古代法制的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有着数千历史的古代中国,其制度化的程度并不低于现代。而通过研究同样可以发现:古代中国,音乐的创承和发展绝不是缺乏管理的无序自由状态——这即是对事物发生学的一种关注。发生学与传统起源学的区别就在于不止于材料呈现与现象描述,而是从生成机制、功能、承载主体的角度,注重从事物的发展逻辑去关注事物怎样由“此”发展为“彼”的中间过程。
由此,笔者将这种对“发生学”层面的关注,总结为“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第二个研究向度。
三、“正统”论:关注“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音乐史”
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部分。杜亚雄教授曾在“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中国音乐文化史≠汉族音乐文化史”。③的确如此,而且汉族音乐文化史不仅不能代表“中国音乐文化史”,就算在“帝王史”这种有明显局限、早已为学界摒弃的史观下来看,我们对于所谓“少数民族政权下的音乐”关注也是不够的——秦以后的有北朝、辽、元、金、清,都是“非汉族政权”,而在这些朝代里,发生了诸多足以影响中国文化的关键事件。就音乐史来看,不谈“非汉”民族自己的音乐发展,仅仅说其对传统主流音乐的影响也有很多重要的事件,如:北周时“灭佛”对于佛教音声的影响;北朝“胡腾(旋)”舞的传入直至唐代“人人学圜转”;辽人对于唐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保留;金、元、清三朝,曲艺、戏曲的发展等等。
笔者对少数民族音乐没有研究,不敢妄议。但是,结合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来看,如果说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仅就“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音乐”来看,“中国音乐文化史”应当注意关于“少数民族政权正统化”建设的问题。④
“正统”是历代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其实质在于“如何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中国历代任何族群在夺得大统之际,首要考虑的都是如何确立自身的‘正统性’。‘正统性’包罗三个核心涵义:一是‘大一统’,即王朝需要占据足够广阔的边境,同时具备上天赐予的德行。二是需要制礼作乐,董仲舒就说过:‘王者必纠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三是以中国之地为本位,‘内诸夏而外夷狄’,处理惩罚好族群之间离合聚散的干系。”[6]从秦后历代政治理想看,“大一统”是其核心。这里不存在“汉族”“外族”的区别,无论是谁入主中原,都一定会遵从这个思路。若不如此,则统治难以长久,此即“族群—国家—正统”之必然逻辑。这种情形下,在既有的政体中融进自身民族的文化,是最经济、最可取的办法。其中,礼乐制度建设的问题,就是首要与关键,此即《礼记·乐记》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礼乐治国是中华之传统,在礼乐之下融入自己的民族文化(如音乐),既符合国家根本,又不失民族自身,此即所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国家与民族之间寻得的最佳路径(相关朝代的官书正史即可为证)。
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与统治,实是一个“正统化”建设的过程。这其中,如何对“礼乐”进行继承与扩充,是“中国音乐文化史”,同时也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方面。
四、“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意义
笔者曾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术传统提出一些认识,指出其包含三个基本理念(或称“学术观”),即全局观、本体观、整体观。⑤笔者认为“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思维基础就源于此。
杨荫浏先生指出:
“若我们孤立研究民歌,就看不到它的去路,若我们孤立研究戏曲,就看不到它的来路。若我们光研究民歌和戏曲的关系,就又会觉得戏曲来得太突然,而缺少了它准备阶段中的各个步骤。总之,在注意到联系与发展规律之时,我们就会觉得,抛弃了风俗、宗教等音乐,会使我们在从古代到现代,在从民歌、山歌等初级形式到戏曲器乐等高度发展形式,需求共同的发展规律之时,很有可能,会使我们有了头、有了尾,而缺少了中段的腰部。整个发展规程,截去了腰部,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料,来帮助我们完整地说明发展的规律。”[7]P247
如果比较杨先生及其之后的音乐学研究成果来看,这种认识是中国音乐学界研究的一种具共识性的基本学术态度。如:作为“音研所”研究生教育(也是新中国音乐学界研究生教育)首届毕业生的何昌林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学——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念与方法论,简称“九点两结合”:九点,是考察中国传统音乐时所取的九个审视点:宫、官、营、家、儒、道、僧、俗、巫—宫伎、官伎、营伎、家伎、儒乐、道乐、僧乐、俗乐、巫乐。有了这“九点”,……才能兼顾历时与共时;“两结合,是指文献学与田野工作相结合。……文献学与田野工作相结合,从发生学考察到技术操作,皆不失为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抓纲布网络,是指历史音乐学研究必须要有一根历史纲绳维系着一张历史网络,呈纲举目张之势。”[8]
这些关于中国音乐研究的基本理念,可以看作是当下“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向度的先声,是对以杨荫浏为代表的“音研所”,乃至新中国音乐学界当时的学术研究的一种总结与期冀。而“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提出与探索(如三个研究向度),则是对“音研所”优秀传统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中国音乐文化史”这个概念并不难理解,核心在于“音乐文化”。对于“音乐文化”,很多学者都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此不赘述。正如项阳研究员所言的“文化不是贴在音乐上的膏药”。笔者认为: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看,“音乐与文化”不是“音乐(本体)+文化”,“音乐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学界研究的多数也是“音乐(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谈“音乐”而不谈“音乐文化”完全可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基于“音乐工作者”的身份,这种“音乐(文化)”讲的多了,往往变成了“音乐(本体)+文化”或“音乐(本体)”。
研究音乐本体,是音乐学最为基本和首要的任务,这一点毋庸置疑。以“音乐文化”之名进行研究,绝不是要“去‘音乐本体’化”,而是在进行这个“基本”“首要”任务的时候,需要一种“提醒”:①一种伦理学上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音乐是人的创造、承载、传播”,而不只是音响、器物、数字;②一种视野上的提醒,提醒我们,“音乐文化”是一个整体,研究不应只做“分割”与“抽取”,还应回到整体,“音乐(本体)”之外的社会、历史,有些是与音乐史相互缠绕甚或本为一体,绝非仅是“故事的背景”;③一种方法论上的提醒,提醒我们,音乐本体分析要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地进行,充分考虑对象的复杂性。
笔者上述分析“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特征,用了三个理论,看似“拉大旗”。而实际上,系统论、发生学、正统论,并不是什么新兴理论,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科、社会学科普遍采用的方法论。它们也不是纯粹舶来品,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照样有相类的探索,只不过所谓的“工业化”“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建立也就看起来很“西方”。但这些最终都成为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理念、方法、路径。理论无所谓“中西”“新旧”——立足实践,解决问题,继承前学,向未来推进,才是重点!
中国音乐学的学术史近百年,每代学人都做了很多事情,总体看其实也就是一件事,即建立“中国音乐的话语体系”。如果将这个“体系”比作一座城,以杨荫浏、李元庆、李纯一、郭乃安、黄翔鹏等音乐研究所学术群体并推及至20世纪以来的数代音乐学学术群体,已经为此筹划蓝图、夯土备料、择址定位,做了不计其数的工作,打下宽阔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今天我们提出“中国音乐文化史”之理念,学界同人予以“接通”“集体协作”“共同研究”,皆是极其必要的事情。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任务,在学习继承前辈的基础上,若再往前走,就应当遵循前辈指引,拓展开来、延展下去——逐步建立我们的话语体系。
注释:
①详见《中国音乐学》同名专栏(2015年第4期、2016年第1期)。
②在音乐学界经典著述中,“音乐文化”也是高频率使用词汇。如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书名虽未提“文化”,但在第一章中即“开宗明义”地讲道:“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根源深远”。可见冯先生同样认可并重视“音乐文化”的使用。
③同名文章载于《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1期。
④此方面已有学者予以关注,如刘晓伟博士关于北朝墓葬出土音乐文物及其政权正统化问题的研究。
⑤详见拙文《“音研所”的学术传统刍论》(待刊),本文曾于2016年1月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年会“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专题研讨中宣读。
原文参考文献:
[1]魏宏森,等.开创复杂性研究的新学科——系统科学纵览[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Wei Hongsen,et al.,A New Discipline That Initiates Complexity Research:An Overview of Systems Science,Chengdu:Sichuan Education Press,1991.
[2][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US]Bertalanffy,General Systems Theory,trans.by Lin Kangyi,Wei Hongsen,et al.,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1987.
[3]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Wei Hongsen,Zeng Guoping,Systems Theory:Philosophy of Systems Science,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1995.
[4]郭威.在学术自觉中不断前行——项阳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评介[J].民族艺术,2015,(1).
Guo Wei,March on with Academic Consciousness:A Review of Xiang Yang'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Culture,Ethnic Arts Quarterly,2015.
[5]项阳.《曲子的发生学意义》序[M].台湾:学生书局,2013.
Xiang Yang,Preface to The Phylogenetic Meaning Of Music,Taiwan:Student Bookstore,2013.
[6]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J].读书,2015,(12).
Yang Nianqun,Interpretation of orthodoxy: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Reading,No.12(2015).
[7]杨荫浏.怎样研究戏曲音乐规律——在戏曲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A].“在湖南音乐的采访工作中所得到的有关以后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启示”[C].杨荫浏全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Yang Yinliu,How to Study the Law of Opera Music:A Report at the Symposium of Opera Music,Some Inspiration from Interviews on Hunan Music for Future Research Methods,Yang Yinliu's Complete Works(Volume IV),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11.
[8]何昌林.中国音乐学——音乐学在中国[J]中国音乐,1994,(2).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