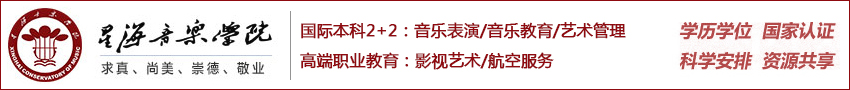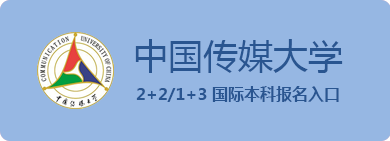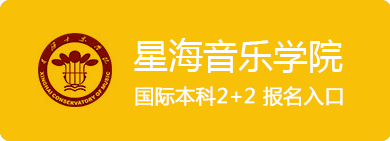作为观念的表演与作为仪式的戏剧
仪式之所以被当成戏剧,与作为观念的扮演或者说表演具有密切的关系,当仪式参与者产生了扮演或表演的观念时,仪式就已经具有了戏剧的特征,这就是作为仪式的戏剧。在仪式发展的晚期阶段,仪式中神的人格化蕴涵了戏剧形象的扮演性因素。表演实际上是一个极具统括性的概念。如果把戏剧等同于表演,我们就会发现,戏剧几乎从人类社会产生伊始就已经出现,并且是随时随地都广泛存在——戏剧就会和表演一样,成为泛人类学的概念,如此,便不再存在古希腊戏剧与印度梵剧、中国戏剧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的狭义戏剧概念。因此,要确定戏剧的概念与范畴,首先需要明确表演的概念与范畴。
广义的表演不仅包括仪式表演与戏剧表演,还包括歌舞表演、游戏表演、体育表演、政治表演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演。如果建立在这种广义意义上的表演认识基础上,中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的历史都将上溯到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前历史阶段,而其范畴也将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正如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说唐戏“横面发展之极,人人能作戏,随时随地能作戏,事事可以戏剧化……”;“唐戏在社会上被运用之广,几乎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以有赖于戏剧。” [⑦]然而,诚如任先生自己所说,“虽戏弄其实,而文人笔下,每每仍命之曰‘乐’,曰‘歌’,曰‘舞’,仅得‘戏弄’之意而已。后世人但从其所写之正面,逐意以求,而不从背面、旁面,以窥其实,当然失之,——原有者失之为无,原是者失之为非。” [⑧]这实际上涉及到表演的范畴与功能,也就是表演的观念与认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戏剧的界定之所以困难重重、障碍重重,是因为对戏剧或者说表演的观念与认识存在着种种分歧。
著名人类学家格雷姆斯指出,当仪式不再是一种直接的体验,而是变成了模仿、虚构和扮演,或当仪式仅仅成为一种传统惯习时,戏剧便历史地出现。 [⑨]因此,区分仪式与戏剧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上的表演性,而在于观念上的表演性。仪式、戏剧乃至表演都是一种观念与认识,把握仪式与戏剧的关系,区分仪式表演与戏剧表演的不同在于区分人的观念与认识。就仪式表演观念与认识而言,它涉及到仪式“表演者”与“参与者”的关系,二者表现为神与人的关系;而就戏剧表演观念与认识而言,它涉及到“演员”与“观众”关系,二者表现为表演者与被表演者的同一,以及观看者与表演者和被表演者的观演关系。实际上,表演者与参与者以及演员与观众的不同表达已经暗示了两者的根本不同,也就是仪式观念与戏剧观念的不同。关于此,谢克纳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仪式表演与戏剧表演的不同在于前者为有效、为求结果、与不在场的人有关、时间为象征性的、表演者为“附体”式、观众参与、观众相信、不鼓励批评、群体性完成品,后者为娱乐、为嬉戏、只与在场的人有关、强调当下、演出者投入但清醒、观众观看与欣赏、存在批评、个人性创作。 [⑩]
扮演因素的出现意味着仪式参与者在观念上的改变,这就是从参与到模仿,也就是表演观念的产生。哈里森指出,图腾崇拜仪式的思维方式基础是集体情感,是基于人与图腾休戚相关的、合而为一的感觉,这些仪式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是参与,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参与本性,而不是对其他特性的模仿;随着人的智力的进步,个人的观察逐渐取代集体暗示,人们心中的统一感慢慢模糊,渐渐地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事物的区分上,于是,参与让位于模仿。 [11]
正是由于观念上的参与转变为模仿,仪式参与者与仪式表演者的参与关系开始向戏剧观众与表演者的观演关系转变。观演关系的形成涉及到演员与观众,那么,仪式参与者是怎样分化出观众与演员的呢?关于此,哈里森对古希腊酒神祭祀仪式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哈里森指出,酒神祭祀仪式中的酒神颂本来是伴有合唱的集体歌舞,舞蹈者抑制自己的个性,在情感上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体,而不是许多个体的相加,但是,由于出于实际的需要,舞蹈队需要一个现实的领舞者:
当舞蹈队把领舞者当作他们的发言人、领袖和代表后,慢慢地他的地位被推到极至,他成了他们的‘牧师’,他们对他的态度逐渐演变成一种宗教性的冥想和尊敬;集体性的共同情感不复存在。歌队渐渐成为兴致勃勃的旁观者,开始时他们对所看到的情景充满了同情,后来变得挑剔起来。从戏剧的角度而言,他们变成了观众;从宗教的角度而言,他们成了神的崇拜者。神与崇拜者、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分离的演变过程是很慢的。伴随有祈祷、赞美、献祭的实际意义上的崇拜表明这种分离已经完成。 [12]
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仪式中神的人格化过程,同时也是作为仪式的戏剧形成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戏剧几乎所有的外在形式要素:演员——从领舞者演变而成的神;观众——从舞蹈者演变而成的崇拜者;戏剧情节——神的生平经历。就此看来,作为仪式的戏剧的形成与神的人格化同步,或者说,神的人格化是作为仪式的戏剧出现的标志。
由于人与神的差别出现,参与让位于模仿,同一感让位于替代感,全民性、集体性性参与仪式因此而成为有了神与人、观众与演员之分的戏剧,酒神颂就是仪式之神与人、观众与演员出现明显分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由于仪式中的神具有分裂的两种类型,仪式因此而具有了戏剧的角色体制,有了建立在性别差异、官方与民间差异、个体与群体差异等现实社会关系结构基础上的主角与配角之角色差异的角色雏形;最后,祭祀仪式中的主体神死而复生的神话具有了一定故事情节性,从而为戏剧提供了情节的雏形。
高度人格化、个性化的神,源自高度个性化的自我;而自我意识产生的实质是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分离。语言学研究表明,原始人并没有把作为主体的自我从他所应对的客体中区分出来,人类最初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具有与他人分离的人格,而认为自己是群体活动的中心。 [13]因此,仪式中的神最初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合一,神的形象显示为自然的动物或植物图腾形象,随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为自然的主宰,神才显示为人格化形象。人格化神出现意味着形体具有特殊的形象性意义:作为神的形象标记,神与人显示出力量与地位的差异,神与人之间的差异通过形象得以体现。当神由现实中的人扮演,仪式实际上就不仅仅是戏剧,而且已经是作为艺术的戏剧了。 [14]
总之,从作为仪式的戏剧看,就表演而言,仪式与戏剧存在着相似或相通,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与戏剧之间至少存在着五个共同点,一是角色表演,二是修辞风格语言的运用,三是有观众,四是知识和对一组单项规则的接受,五是高潮。 [15]因此,戏剧与仪式这两个概念只能更多说明二者之间的相通,不能说明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其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其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体现为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按照发生认识论原理,知识是继续不断构造的结果,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在过渡中,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为标志,这些新的结构在以前既不存在于外在世界,也不存在于主体的心灵之中。 [16]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实际上正是这样的认识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对戏剧的理解实际上是观念与认识问题,在表演形式上,仪式与戏剧不存在阶段性的呈递性,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与递进联系,只有在表演形式所反映的内容及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功能上,仪式与戏剧才具有承递性,仪式的主导情感是集体性情感,戏剧的主导情感是个体性情感,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因此,能够有效解释仪式与戏剧之间本质差异的是仪式与艺术的承递性与差异性概念,戏剧的发生是作为仪式的戏剧转变为作为艺术的戏剧。仅仅从美学角度无法把握仪式与戏剧的内在本质联系,必须从历史发生的社会人类学视角,从仪式与戏剧外在形态与内在功能的统一,才能洞察仪式与戏剧的本质差异,这就是作为仪式的戏剧反映的集体性情感与作为艺术的戏剧反映的个体性情感的差异。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