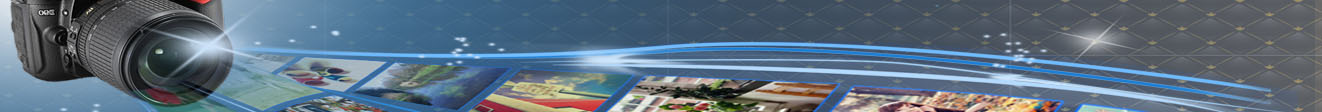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梁祝》音乐诞生的启示
之所以想起写有关《梁祝》音乐的文章,是缘于近日孟波仙逝。孟波何人?乃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三点”功臣——“三点”者,点题、点将和点睛也。
先说“点题”。当年孟波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1958年初秋,当“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成员们为选什么题材向国庆10周年献礼而争论不休时,孟波面对最后集中的三个题材做抉择:1.大炼钢铁;2.女民兵;3.《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选择“主旋律”差不多是不二选择,可孟波却毫不犹豫地在“3”字上打了一个“√”。这个“3”在孟波的一笔勾动下,横过来就好似一个“蝴蝶”,从此这只神奇的蝴蝶进入胚胎发育期,然后渐渐成形,最后展开美丽翅膀飞向世界。《梁祝》作曲之一何占豪说,他们实验小组成员原来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大炼钢铁或女民兵的题材,第三个只是凑凑数,“陪太子读书”而已。可孟波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梁祝》呢?由是说到了“内行”和“担当”的关系。在孟波这个内行的“党的领导”看来,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和柔软,难以表现大炼钢铁、女民兵这样一类生活所需要的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而越剧《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孟波的这个内行选择绝非出于偶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晚上常到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住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又致力于传播优秀革命歌曲。他本来就是个音乐事业组织家,以后几十年,他都在文艺单位当领导,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有了这些前提,才有他“毫不犹豫打钩”的决断。当然决断后并非一帆风顺,有人就以“宣扬爱情至上和封建迷信”提出异议。但孟波自有一套说辞:“《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孟波这种政治和艺术上的双重自信,得益于他文艺工作领导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这是说的“点题”。
再说“点将”。陈钢和何占豪的合作,就是孟波“点将”的结果。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任二胡演奏员。他虽然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但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未学过作曲。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于是孟波对副院长、著名作曲教授丁善德建议,希望作曲系找个优秀学生支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推荐过来。但这个陈钢,是“有历史问题”的旧社会作曲家陈歌辛的儿子,于是免不了又有人质问,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孟波斩钉截铁地回应:“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之所以敢于斩钉截铁,也是缘于他的政治水平,他懂得掌握“不唯成分论”的政策,且勇于担当。因此,两位青年才俊得以心无旁骛地沉醉于创作,终成正果。
最后说“点睛”。《梁祝》初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问作曲者“为什么省去了化蝶”?他们回答说,写“化蝶”这段怕人说是宣传封建迷信。孟波为他们打消顾虑说“化蝶”并非迷信,而是反映封建社会人们美好理想的追求,活着不能成双对,死后化成蝶双飞,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而且从音乐本身来讲,第一主题的再现,会给听众美好的想象。作品实现ABA的曲式结构,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更显完整。于是,我们今天听到了凄美之下饱含浪漫的“化蝶”旋律……
无论是“点题”、“点将”还是“点睛”,这些故事里孟波所呈现的,是一个政治上和艺术上都非常成熟的艺术界领导的正面形象。这样的形象,容易让我们想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想到夏衍、茅盾……假如我们的文艺界领导都是政治和艺术的“双重内行”,同时又“敢于担当”,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是否就能找到答案?最近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大胆明确提出了“择将”问题——虽然缺“高峰”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化单位常常被作为安置干部的地方。由这样的干部管理文艺单位,莫说“高峰”,只怕日后“高原”都会变为“盆地”。话说得有点重,但重锤响鼓,事出有因,值得深思和反思。我想,孟波的例子,或许会给出启迪。
关于“《梁祝》音乐诞生故事”以及启示,到这里还没有讲完。在此再披露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那是以演奏《梁祝》而成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的“独家披露”:当年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听完《梁祝》,嫌26分钟太长,就让俞丽拿跟作曲家说改短点。可俞丽拿想,单乐章的《梁祝》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改短就残缺了,为此她狠狠心没“颁旨”。后来,又有演出了,周总理再听,发觉并没改。这时怎么样呢?没怎么样,周总理尊重艺术家,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改就不改吧。请看,这个故事里,一个艺术家敢“瞒旨”,一个领导人竟“不责备”,更遑论“雷霆震怒”。于是,才有了响彻环宇的完整版《梁祝》。陈钢对此特别敬佩俞丽拿:“她当时如果如实传达了指示,我们能不改吗?”是的,《梁祝》得以“完整成活”,其间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值得玩味:在对待文艺创作问题上,领导和艺术家如何既高度沟通又各守职责,既尊重领导又尊重艺术家,既可以“听话”又可以“商榷”,这才是“和谐共舞”的良性局面。我们“此时”比“彼时”做得更好么?值得追问和扪心自问。
此外,还有一个有关艺术的“《梁祝》音乐诞生故事”值得分享。陈钢在写作《梁祝》的乐队部分时,为了充分“民族化”,曾想在描写“同窗共读”时加入“月琴、琵琶、三弦”三件弹拨乐器,以增强民族色彩。但是第一次合排时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乐器,因为庞大的管弦乐队将它们全给淹没了。第二次合排时陈钢要求他们尽量放声演奏,可听到的则全是噪音。再合乐时,这些民乐未参加,听起来乐队反而干净了,而所需要的弹拨效果就改用弦乐拨奏代替了。这件事情令陈钢感悟到,不是用了民族乐器就是“民族化”,“民族”当作为一种融入世界的音乐元素时,其主要是取民族之魂与民族之精粹,乐器与演奏法则是次要的。不过,《梁祝》中还留存了一只非留不可、不可替代的民族乐器,就是“板鼓”。因为,此时只有板鼓才能打到人的心扉,才能打出中国戏曲中特有的戏剧性手法——紧打慢唱。所以陈钢认为,交响乐的着眼点首先应该是它的国际化特点,同时要将我们特有的民族元素有机地融入其中,建构成一个既是世界、又是民族和个人的艺术精品。有位学者曾作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比喻:越剧原是绍兴的地方小戏,好比“乡镇企业”;进上海经袁雪芬的改革,算是入了上海户口,流传到全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从此就领取了一张“国际护照”,走向世界!
以上讲述的《梁祝》音乐诞生故事,通过孟波、俞丽拿、陈钢的遭遇、表现和感悟,也许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些丰富的联想和启示。我从中领略到“三点启示”——“政治和艺术的双重内行和担当”、“领导者和艺术家的互相尊重与和谐”、“民族化与国家化的辩证关系”……假如读者诸君能够在解读这些故事时得到更多的启示,也是我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