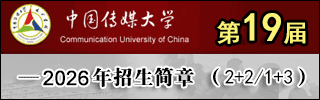显然,“民族音乐学”是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已经逐渐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将“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观念、视角、态度去理解,并运用于音乐文化研究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同样倾向于共时研究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在国内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衔接上已经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工作和贡献……
中国“民族音乐学”:危机与未来趋势
显然,“民族音乐学”是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已经逐渐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将“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观念、视角、态度去理解,并运用于音乐文化研究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同样倾向于共时研究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在国内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衔接上已经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工作和贡献,相当一部分该领域的学者以其自身丰富的传统音乐阅历作为研究基础,在吸取了西方民族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及强调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内以“局内、局外”视角进行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经验之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可观的学术成果,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纵观西方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音乐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是在1980年南京第一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之后,国内学者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性、民族性,尤其是对建立“中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讨论,至今,在中国如何发展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音乐学这一问题,仍然是学界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出于对民族音乐学的极大兴趣,笔者也就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希望在尽量摆脱国内现代学科划分体系影响的基础上,以一个中国的视角,尤其是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对西方民族音乐学自身建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尝试性的判断与归纳,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曾经对“民族化”、“中国化”问题较为关注,并成为处理外来文化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西方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后,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于在共时研究方法上的相似性以及对民族音乐学名称的某些误解,一度出现主张以中国传统音乐的相关研究来替代西方民族音乐学,使之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流派”的观点。到了近几年,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民族音乐学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普世的学术观念,无需在国籍及研究对象上加以限定,因此,对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化”问题逐渐淡出视野,支持,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了看似理论观念与西方向平等的对话状态。
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的提法,高厚永在1980年前后曾谈到“要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系统而完整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其实,世界上的民族音乐学流派亦多,他们的观念也不尽相同,中国民族音乐学也应是世界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并希望通过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引进,“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从而把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摧残、当时尚处在极度萧条之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1];魏廷格则建议用“中国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从而明确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研究的本土性[2];沈洽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从王光祈至今)的梳理,在一定的历史意义上构建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脉络结构,并以此作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中国化”过程的解读视角[3];…… 显然,面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进入,首先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相关领域积极参与了互动与讨论,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担负起了绝大多数的民族音乐学部分相关研究与工作,不少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者通过学术转型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这种贡献一直延续至今。
在大量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讨论之后,学者们的关注点逐渐从之前的研究对象转移到了研究方法及观念的层面。诸如管建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讨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性质问题[4];罗艺峰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到文化全元论的方法论视角探讨了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及未来展望[5];杨民康对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位—客位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讨论[6]等等,除此之外,大量田野个案的研究成果模式化地出现,移民音乐、仪式音乐、流行音乐等等新的论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要补充;并且,诸多相关学术会议频频举行,如专门从学术方法角度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单独成会,并引起来众多学者的呼应[7];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文章不断出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逐渐发展升温,并已进入国际对话行列,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界的焦点。
但是,看似平稳发展的民族音乐学是否已经步入成熟了呢?在笔者看来,其中仍然隐藏危机,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反思。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危机——原动力的缺失
认为西方文化体系是优于其他落后国家文化体系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在中国音乐界曾经有所盛行,主要表现在创作技法等音乐本体相关领域。客观地说,这种以“先进的”西方音乐体系为标准来评价或解释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形式及价值的做法,在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国内各音乐院校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要教学对象,并严重忽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现象即是“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当代具体表现,并且,随着这种思想与现象在国内社会文化意识的普遍传播,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价值判断等仍然倾向于西化,甚至直接影响到考学就业、学校教学体系改革的困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当这些现实问题被认同为“正常、自然”状态时,对“欧洲中心论” 原本应该突显的批判性被弱化了,对其反对之声越发无力。
反思是西方人的文化“惯性”,这与西方人的宗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也正是由于其类似做了错事,只要到教堂忏悔、反省,便可释下包袱,继续下一次的错误和反省一样,这种“惯性”的反思并不深刻。西方人善于反思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构建了“民族音乐学”。经过对殖民地文化的搜集考察、文化比较,到后来的文化多元、文化相对,西方人成功的从一个全球殖民者转变为全球文化的积极阐释者,并且以其自己曾经犯下“欧洲中心论”的错误来警示那些曾经沦为被殖民的世人,将“文化中心”转型为“观念中心”。仍然没有从过去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摆脱出来的中国人是否会“顺理成章”的再次接受?
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思。这里提出的不彻底,不是指文化相对的不彻底,而是指西方世界在提出“文化相对”的反思时,是建立在自身曾经错误的基础上,其背景是一个殖民者自我反省的过程,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应该是“他管住他自己就好”,而不是如同一个地主打了长工后,反省了自己不该打人,于是理直气壮的告诉长工“你以后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是否滑稽?就怕这个长工还是改不了奴性,一如既往的接受佛光普照,莫名其妙的恪守这般真理。这在现实中并非没有对应:不少外国学者来国内讲学,他们带来了很多“知识资源”,这是我们欠缺和需要的,但是也不乏“传经布道者”,刻意表现出“我带来了你们尚未察觉到的问题”,所以“你们必须同我们一起反思”的姿态,而我们的学生却如获至宝。
但是,令人感到尴尬的是,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确仍然盛行“欧洲中心论”,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错误在先,这导致西方再次成功引领我们来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文化相对世界,原本的受害者再次成为了受害者。音乐就是文化、世界文化多元平等、整体视角下的人文观察等等等等,成为今天中国音乐学界恪守的至理名言。
当然,也许这是一种抱怨,但是这样的抱怨并不是否定这些学术观念,这些学术观念都是在正常不过的,正常到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人早就以其作为为人处世的执行准则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将音乐作为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成为承担“君子”名号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魏晋的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疏方异俗,歌哭不同”已经是音乐视角下的文化多元思想的直接表达;佛家禅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不但将整体联系的视角表达的淋漓尽致,更加体现出了超出学理层面的精神内涵……(更不用说“一粒沙可见三千大世界”这种宇宙全息论了)
这便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前危机——遗忘了自己曾经有的,直到别人反省至此才如获至宝。进一步说,我们的危机不是停留在学术理论方法上,而是出现在自我发展的“原动力”的缺失上。如果摆脱不了这种“西方带领”的状态,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甚至是中国的音乐学,将一直跟随别人的脚步去走自己走过的路。
三、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未来趋势——中国音乐史及文化史学界的必要补充
提到中国文化史,并不是认为中国音乐史无法承担相应的工作,而是希望尽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全貌作为今天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历史文化祭奠。
前面已经提及,西方民族音乐学传入至今,学科划分体制下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承担起了主要的呼应及研究工作,这一点有目共睹,这是由其共时性研究的相似性造成的。自从瑞斯在梅里亚姆三分模式基础上加入了历史概念,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中国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论述:洛秦以其博士论文为例,论述了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8];项阳指出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在论域、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交叉现象[9];赵志安则通过对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兴起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了剖析。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