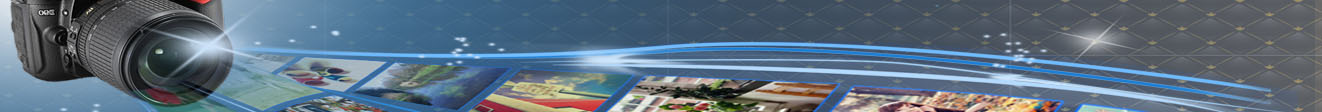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来源:未知 编辑:中国艺考网
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地缘环境中历经漫长岁月的时光雕琢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精神浓缩,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种内在灵魂,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推动力、向心力、凝聚力。它渗透在其风俗习惯、艺术活动之中,内化于民族成员个人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民族成员个人的情感、道德和意志,使本民族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指导民族实践行为。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精神的真谛。汉族的大型舞龙活动,含有民族意识的认同,含有一种潜在的凝聚力。通过舞龙,强化了巍巍中华自强不息、奋起腾飞的民族精神,刚健有力、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
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会表现出民族成员性格的共同性,它影响人的形体动作特征与形体表达。维族性格开朗活泼、幽默风趣,他们高兴时会摇头摆颈,这些动作被吸收到了“赛乃姆”里,形成了移颈、摇头动作。羌族的民族性格勇武不屈、豪放豁达,“跳盔甲”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威武雄壮,尽显粗犷性格。朝鲜族性格既沉着坚韧又内敛含蓄,故其舞蹈风貌是潇洒柔婉与刚劲跌宕兼而有之。因此,民族舞蹈也是“性格舞”,其动作性格正来源于民族性格。
作为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民俗,如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是民间的、群众性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的传承性文化,由民众和群体传习而得以嬗变和发展。它既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又是群体所享受的文化。独特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加强同样起着积极地整合与促进作用。许多民族岁时节令几乎都是载歌载舞,如红河哈尼族人“苦扎扎”节跳扇子舞、竹棍舞、乐作舞,拉祜族“库扎节”跳芦笙舞。一个民族的民俗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劳动是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与之有关的习俗不外乎是希望生产顺利、硕果累累。在白族“田家乐”里,霸王鞭、白鹤舞、蚌舞等穿插其间,整个活动囊括了水稻栽插劳动的全过程,表现出白族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充分反映了白族人民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希冀。民俗舞蹈和民俗的传承载体均为特定的民族群体,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寨、乡、县,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在民俗活动的特定时空中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强化、凝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婚丧习俗是民族舞蹈的重要内容,婚嫁舞蹈主要功能是祝福、庆贺。从“龙纵舞”、“洒米舞”的哈尼族婚礼舞蹈,到“奎翮嘎”和“腊叉嘎”的怒族婚礼舞蹈,都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气氛。与送鬼祭魂仪式相配合的丧葬舞蹈主要是安抚死者的亡灵,如景颇族丧葬舞蹈“格本歌”欢乐豪放,“思港斋”稳健低沉,“金寨寨”粗犷而充满原始气息。就民俗与舞蹈的关系而言,“民俗为舞蹈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也为它增添了民族文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民间风俗为舞蹈艺术提供了内容、气氛和表现环境,而舞蹈又是民俗文化整体中有形传承的重要表现”(14)。
由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宗教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志愿顺从,宗教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的支柱,有净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的意义。它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所谓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作为一种精神风俗, 宗教信仰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孕育与发生于原始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民俗文化,对大自然的依赖性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多神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活动主要是一种被明确表达的、参与者可以理解相关行动的显性仪式活动。比如跳“雨舞”的显性仪式是求雨,参加者对仪式的目的、结果有明确的意图和决心,这可以理解为结构功能性认知模式。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1.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2.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的结构框架。3.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4.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5.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的表述。(15)“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16)。而舞蹈就含有配合信仰观念而进行的具体的、感性的、实践的仪式活动的功能意义。如哈尼族在二月祭寨神、三月祭山、六月祭水、七月祭天地,每一次仪式活动又都是盛大的歌舞庆典。这些“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17)。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炼和浓缩着民族成员炽烈的情感、信仰和愿望,抒发出民族成员膜拜神鬼、祷求安泰、期待美好婚姻的感情,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在景颇族的“目脑纵歌”中,就有上千名舞蹈者围绕着汇集了多种崇拜偶像祭坛“目脑示标”起舞。他们通过舞蹈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对象的崇敬和希望神灵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反过来,宗教信仰与崇拜也对舞蹈动作、运动路线、舞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制的礼仪,使得藏民形成躬腰敬礼、低手前伸,表示“敬意”的习惯动作,因此在藏族舞蹈的舞姿、体态上,就刻有宗教心理的痕迹。“锅庄舞”等一些舞蹈运动路线具有按顺时针方向(由左向右)行进的特点,反映出对吉祥追求的宗教心理。壮族舞蹈中“凤凰手”、“蛙形”动作,由蛙状动作演变而来,是壮族人以蛙为图腾的原始宗教风俗的体现和衍化。羌族的“羊皮鼓舞”则在舞具上留有“羊人合一”的羊崇拜古代遗风。一些民族文化风俗活动,为舞蹈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表演环境,在内容上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内涵;同时,舞蹈以规律性的人体动态为媒介,表现、传达并保存了宗教主旨和文化底蕴。
这些社会生态因素(民族心理、意识、精神、性格、习俗等)虽然对舞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影响了舞蹈的不同层面,或内容、或形式、或风格、或动律。

舞蹈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