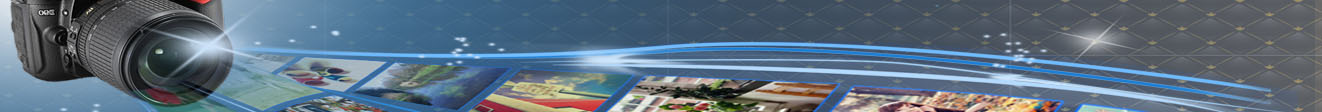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解读:方法论范式再议
【内容提要】如何观察和解读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音乐学术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运用语言分析的角度,进而通过具体研究例证思考和论述了“音乐在文化中”、“音乐作为文化”和“音乐即是文化”这三种不同表述方式所蕴含的深层差别。作者认为,上述三种表述方式实际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方法论范式,在观察和解读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论策略有明显不同,但均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应该在研究实践中形成相互平行、彼此支撑的局面。
【关 键 词】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梅里亚姆/内特尔/海顿/韦伯/李皖
【作者简介】杨燕迪(1963~),男,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副院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 200031)。
中图分类号:J1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1)01-0062-07
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历来是音乐学术思考中的重要问题,其中不仅引发诸多争辩和议论,而且一直受到众多音乐学者的持续关注。由此可见这方面的探讨确乎触及到某些音乐核心问题的关键部位,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学科和知识的演进,该课题始终保持着历久弥新的吸引力。笔者的思考试图通过对前人相关学说的批评性考察,对这一似已成“老生常谈”的问题提出试探性的个人己见,是为本文标题中的所谓“再议”。其中的立场和观点或许与当前通行的某些论说并不相同,如有不当和不妥,敬请各位同仁提出批评指正。
一、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分析与反思
关于音乐与文化的论题,众所周知,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从一开始就将其作为学科发展的宗旨性纲领。该学科在方法论上有别于其他音乐学子学科的关键要义,正在于它不仅关注音乐的产品和过程本身,而且更为关心音乐在具体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中所承担的功能与作用。美国著名学者布鲁诺·内特尔对该学科的著名定义——“对音乐进行‘在文化中’(in culture)或‘作为文化’(as culture)的研究,或者说研究文化语境中的音乐”① ——申明了这一音乐学子学科集中关注音乐与文化关系的本质要求。为此,在音乐人类学的学理建构中,关于音乐与文化关系的阐述层出不穷,相关的学术“范式”也根据看待音乐与文化角度的不同而形成某种“有据可查”的演化轨迹。依照洛秦教授的理解,近几十年来国内外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中,逐渐浮现出关于音乐与文化的三种彼此相连但又相互有别的理论“范式”:1)music in culture(音乐在文化中);2)music as culture(音乐作为文化);3)music is culture(音乐即是文化)。②
在上面的表述中,英文的三个表达式就体现意义的区别而论,比中文翻译显然更直观、清晰。我想就此进一步进行推理和反思,这三种不同的表述究竟反映了怎样的音乐文化意识和观念。在英文表述中,music(音乐)与culture(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同,是通过简单的介词或系词转变(in, as, is)体现出来,其间的语词转变貌似简单,但却显露了值得深思的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学理思路和解读策略。
所谓music in culture(音乐在文化中)这一表述,关键在于“in”一词,其意为“在……之中”。因此该表述就意味着“音乐在文化的范围之中”,其逻辑内涵是,音乐小于文化,文化大于音乐;或者说,文化包围着音乐并对音乐起支配作用。依此推演,这一表述进一步的内涵可能是,音乐是文化的一份子,音乐是文化的家族成员,但音乐并不能等同于文化。正如杨某人是杨氏家族的一个成员,如果要界定这位杨某人的身份,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他置于杨氏家族的大范围中予以考察,但不能就此将杨某人和杨氏家族等同,因为毕竟杨某人和杨氏家族是两个层级的范畴,不能混淆。所以,“音乐在文化中”的观念内核就在于,音乐是文化的下属和亚种,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两者从根本上说是不能等同的。
再看music as culture(音乐作为文化)这一表述。从前一表述中的in转换为这里的as,观察音乐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角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里的as是“作为……”的意思,因而,音乐就被“作为”文化、被“当作”文化来看待。不妨进一步深究这里的含义。既然是把音乐作为文化,那就意味着音乐与文化仍不是一个东西,但音乐已经有充分资格被当作是文化的代表和体现。显然,在这个定义中,音乐不再是文化的下属和亚种,也不是被包含在文化中,而是被当作文化的一个大约的对等物。音乐于是大约等同于文化。
最后我们来考察music is culture这一表述中的视角改变。通过is(是)的对等连接,音乐与文化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体。音乐即是文化,这就是说,音乐等同于文化,而不是外在于文化的“他者”。与前面两种表述相比,在这一表述的视角中的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当然是最为紧密的。音乐既不是文化的下属和亚种,也不是文化的大约对等物,而就是文化本身,音乐等于文化。
通过如此这般的语言分析和反思,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某种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表述中逐渐从分离走向合一的过程。有意思的是,这也恰是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在音乐与文化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学理思想发展轨迹。以我个人的理解,梅里亚姆(Alan Merriam)这位较早的学科领袖在其理论架构中,所强调的往往是“音乐在文化中”(music in culture)的研究思路③;而布鲁诺·内特尔这位后来的领军人物在1970至1980年代所提倡的方法论可能更多就带有“音乐作为文化”(music as culture)的思想;而近来在学科理论前沿中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蒂莫西·赖斯所倡导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的新模式④ 中,“音乐即是文化”(music is culture)的观念可以说是某种暗含于其中的前提。必须提请注意,我并不认为这三种表述的演进是一种学理上的“进步”,它们之间也并不存在后者替代前者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论述中仍会提及。
二、方法论范式之一:音乐在文化中
基于上一节中的语言分析和反思,我想对上述三种针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不同视角从“写文化”的实践层面再予以具体考察。关于音乐与文化,或许还可以从理论上提出更多的思考和论辩,但我个人更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是,如何在实践层面来对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分析和写作?也即,如何针对音乐与文化这一所有关心音乐的人都感到非常重要的关联进行富有成效的解读和诠释?显然,这个关切已经不再局限于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范畴,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学科方法论意义。无论是面对艺术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无论是针对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如何揭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这永远是音乐学的根本任务和重大命题。
笔者以为,“音乐在文化中”、“音乐作为文化”和“音乐即是文化”不仅是针对音乐与文化观察视角的三种简单有效的语言表述,而且在更深的意义上恰恰可以作为解读和诠释音乐与文化关系的三种不同的方法论范式,其效用已经被前人的解读实践和研究成果所证实。下面,我将以具体的研究实践为例证,具体展示和分析三种不同视角的方法论启发。
首先,我们来观察“音乐在文化中”视角中的方法论策略。正如上一节的语言分析所示,“音乐在文化中”既然将音乐置于文化的包围之中,这种视角主要的解读重心便是音乐置身其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对音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中,研究者所关注和处理的往往不是音乐的实体和文本(无论是音响文本还是乐谱文本),而是音乐的外围,也即“关于音乐”(about music)的境况和情形。这一思路的总体方向是,围绕有关音乐的社会与文化境况进行勘察,但最终并不一定进入和触及音乐本身——特别是音乐的音响构造和技术语言。应该说,如果没有对这些外围文化境况进行了解和考察,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将是极不完整和全面的。诸多音乐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以及音乐人类学中田野考察的很多内容便是这一视角下的产物。
我所列举的具体例证来自我个人的研究体验。2009年正值“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约瑟夫·海顿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我应邀举办专题讲座并撰写文论。⑤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海顿的音乐创作态度,我对海顿的社会身份进行了一番考察。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留存至今的一份于1761年签署的海顿受雇协议具有突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⑥ 话说这一年5月1日,海顿正式受雇于奥地利的匈牙利贵族埃斯特哈齐家族,担任宫廷副乐长。当时签署的共14款雇佣协议详尽和明确地规定了他的音乐使命、业务能力、日常职责、作品归属和使用范围、薪俸标准、起居准则、穿戴要求、谈吐规范及其他相关细节事务。作为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这份协议生动地反映出当时音乐家的社会地位、身份角色以及职业生态。我仔细阅读了这份档案文献,并从当代人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了社会学角度的文化解读:
今天的人读到这份协议,不免产生一丝好玩的感觉,特别会对其中居高临下的口吻多少有些敏感——因为我们都经过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精神的教育和平等意识的熏陶。显然,与其说这是一份协议,还不如说这是一份规定,具有“霸王条款”的味道。雇佣方埃斯特哈齐亲王与被雇方“工匠艺人”海顿之间,在社会地位上不在一个“档次”,上下距离相当明显。海顿的前途和发展全仗亲王殿下的“恩宠”和“信任”。他的艺术创作也完全受制于亲王的个人指令,对于现代艺术家而言至关紧要的“著作权”概念在这份协议中尚无丝毫表露。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份协议中也清晰透露出对海顿的礼貌性尊重。特别有一个细节,海顿被认为是“家族的成员之一”,而不是一个“奴仆”或“下人”,因而有权“在职员专用席位上进餐”。这说明,在欧洲启蒙运动到来之际,音乐家尽管仍然属于“工匠艺人”,但在一些开明和有文化的贵族宫廷中,其地位身份已经在提升当中,而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家”出现的前奏性准备。⑦
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反思,我在此所进行的解读和分析应该属于“音乐在文化中”的观察视角。因为我在这里并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海顿音乐,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音乐在其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常态。音乐在此是被置于文化“之中”,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必须通过这个大的背景,我们才能知晓和了解音乐的取向以及音乐家的方位,具体到海顿的社会身份,他正是一个位于“前现代工匠艺人”和“现代自由艺术家”之间的典型代表。反之,没有这种“音乐之外”的文化和社会的背景知识,我们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无疑会陷入贫困、狭隘和肤浅。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从“音乐在文化中”这种视角来观察音乐与文化,两者之间就不是对等与同构的关系,而是音乐由文化决定,并隶属于文化。
三、方法论范式之二:音乐作为文化
在“音乐作为文化”的视角中,音乐被当作是文化的大约等同物,而不仅仅是文化的隶属现象;音乐能够体现和代表文化,而不仅仅是受到文化支配和决定。这显然是一种比“音乐在文化中”更为复杂的观察视角,解读者所关心的不再仅是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境况,不再仅是音乐如何被外在于自身的某种社会力量和文化惯例所影响或制约,而是要进一步观察,音乐是否以及如何映照、象征、影射,乃至型塑了文化的某个方面或甚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看出,这种视角和思路总的路线是朝向音乐之外,以音乐为媒介和通道来理解文化和社会。从音乐开始,出发点是音乐的过程和产品,但最终的指向和落脚点是在音乐之外的文化。当然,这种指向并不绝对,正如“音乐在文化中”的解读视角在很多时候也帮助我们理解音乐自身(如我后来发现,海顿那种介于“工匠艺人”和“自由艺术家”的独特社会身份极大地影响了他谦逊和质朴的创作态度,并由此促成了他在音乐幽默与喜剧上的伟大创意),“音乐作为文化”的方法论视角除了增进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之外,也会深刻地改变我们对某种音乐的感知和认识。但是,在这种视角中,即便是通过文化回过头来了解音乐,这种了解仍更多是指向音乐所发挥的文化功用和蕴藏的社会意义,而不是音乐自身的价值和意蕴。
具体而言,如在音乐人类学中,诸多研究的要旨是希望揭示音乐的行为、观念和形态中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和暗示。而这方面最常见的研究路线是解读音乐所具备和履行的社会文化功能。梅利亚姆曾列出音乐可能具有的十大总体功能。⑧ 这其中除了我们通常较为熟悉的“情感表达功能”、“审美愉悦功能”、“娱乐的功能”之外,他还通过大量丰富的世界各地民族音乐的例证,总结了音乐发挥的其他或许更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有时甚至是通过集体无意识或个人潜意识而发挥作用),如“沟通的功能”、“象征再现的功能”、“身体反应的功能”、“强化服从社会规范的功能”、“确认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的功能”、“促进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功能”、“促进社会融合的功能”。⑨ 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在具体文化语境中了解和研究具体音乐的用途和功能,才能切实揭示音乐作为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内在机理。
然而,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论,这种“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视角除了在音乐人类学中已经成为研究惯例的文化功能解释之外,还存在一些更加大胆和具有想象力的路径,这尤其体现在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音乐的声音结构和组织形式来探查社会信息和文化内涵的努力中。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重要论著《音乐的社会和理性基础》。⑩ 韦伯终生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如何通过“理性化”进程而生成“现代性”的典型社会建构,近年来被国际学界公认是社会思想界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他在这部其仅有的音乐论著中,着力探讨了西方艺术音乐的相关元素的发展如何体现和映照了西方整体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这些元素包括音阶、和声、调性等“音体系”材料,西方的乐队和相关乐器的发展,以及西方记谱法的演进。韦伯认为:
朝向理性化的驱动——即,以可计算的规则来支配经验的某一领域在西方文化中出现。这种将艺术的创造减缩为一种基于可计算的、可理解的程序形式的驱动尤其体现在音乐中。西方的乐音音程在其他地方也被人所知,被人计算。然而,理性化的和声音乐,不论是对位还是和声,以及基于和声泛音的三和弦的乐音材料组织,却是西方独有的。同样如此的还有以和声角度来解释的半音与等音现象。西方独有的还有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对与管乐器合奏的组织化。在西方,也出现了一种记谱体系,这使得近代的音乐作品的创作成为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存在的现象。(11)
或许可以作出批判,认为韦伯的音乐认识中存在某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子,这是处于20世纪初的西方学者所难于避免的。然而,换个角度看,韦伯的学说恰恰说明了西方音乐的艺术特性和文化特质是西方社会典型的“理性化”建构所带来的产物。尤其发人深思的是,韦伯并没有简单地对音乐表层的文化用途与社会功能进行描述和说明,而是深入到音乐的内部结构和组织机理中来考察音乐中所蕴藏的文化意识内核,这当然与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观驱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思路如出一辙。(12) 这种独特的“音乐作为文化”的解读视角,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包括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等在内的诸多学人的音乐文化观念。阿多诺在自己的论著中始终坚持,具有“本真性”的音乐并不是简单直接反映社会文化的现实,而是以“否定的辩证法”映射出社会文化的内在本质。例如无调性音乐正是以自己的不妥协、不协和、不协调来映照出社会现实的异化与非理性本质(13)。近来在英美“新音乐学”中独树一帜的女性学者萝丝·苏波特尼克则公开继承阿多诺的衣钵,对西方音乐中的隐蔽意识形态和前人少有关注的深层文化建构进行了深入开掘和批判(14);另一位女权主义音乐学代表人物苏姗·麦克拉瑞(Susan McClary)在其已经成为经典的《阴性终止》一书中,用文化批判的立场研究音乐中的性(sex)、社会性别(gender)与性征特质(sexuality),揭露西方调性音乐中“男权中心”的映射,并抨击音乐中的这种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歪曲和贬低。(15) 可以看出,所有上述的研究和解读均是着力于挖掘音乐中的意识形态内核或文化价值隐喻,与上一节中“音乐在文化中”的方法论范式不同,这类“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不是着眼于音乐的外围和周边,而是力图深入音乐的结构内层。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在这里我们的兴趣似乎不是导向音乐自身,而是导向音乐所指涉或隐喻的文化。
四、方法论范式之三:音乐即是文化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将音乐与文化的解读导向音乐自身的方法论范式呢?也即通过这种文化性的解读,是否有可能让我们更深入和更有兴致地聆听、鉴赏和理解音乐本身,而不是将我们的兴趣导向音乐的文化背景(音乐在文化中)或音乐的文化隐喻(音乐作为文化)?我的个人观点是,“音乐即是文化”的解读思路也许可能提供这样一种方法和途径。在“音乐即是文化”的视角中,总的行走路线是,从音乐自身开始,有时会游弋到音乐之外,但最终停留在音乐之中,因为音乐就是文化。在这种解读中,并不排斥文化外围的知识和文化隐喻的暗示,甚至这种解读本身就建筑在“音乐在文化中”和“音乐作为文化”的前提之上,但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音乐即是文化”的视角最为珍视的始终是音乐——音乐的声音、声响、节奏、韵律、色彩、旋律、和声、织体、结构以及所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声音组织和形态。而且,持这一视角的解读者会充分意识到这些声音元素就是为聆听而存在的本体价值。当然,这里的声音和聆听绝不是孤立的,与文化和社会隔绝,恰恰相反,这里的声音和聆听是将文化的意涵、社会的讯息与生命的体验统统卷入进去,从而形成某种在聆听中产生的丰满、生动而多彩的文化与生命互动。进一步,解读者应该通过富有感召力的文字表述将这种聆听体验表达出来。(16)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例证来说明这种可能性。我这里想到了国内著名的流行音乐批评家李皖的音乐文字解读。虽然李皖并不是“学院派”的音乐研究者或音乐批评家,但长期以来,这位作者通过《读书》、《文汇报》等重要的文化思想报刊媒体,不断通过自己优美而鲜活的中文写作,深刻地触及并揭示了音乐(特别是流行音乐以及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中的文化意蕴和生命内涵。我们不妨以他在《读书》2009年第10期的一篇“浪漫漫流大地——新疆音乐如是我闻”作为例证,来观察和品评他的解读是否具备我们理想中“音乐即是文化”的观察视角的品格。在介绍了新疆音乐的多民族构成之后,李皖直接开始触及新疆音乐的特殊品质:
真实的新疆音乐,是一种旋律并不太明显的音乐……熟悉的旋律完全被热腾腾的节奏给淹没了,听到耳朵里就是旋转。等新疆人拿出了新疆歌曲原味,它们全变了味,就是一股子节奏,一股子节奏的圈圈,一股子节奏的旋舞,旋转旋转旋转……新疆音乐的性格绝非优美,而是火烫,是激情炙烤着饥渴。新疆人的趣味不在旋律方面,表达的重点也不是抒情,而是激情的发散。它是歌舞一体的艺术,是一种狂态。(17)
这是一个具有丰富聆听经验和深厚文化趣味的聆听者对音乐心理性格的用心把握。其用意在于迅速揭示和刻画这种音乐的内在特质。我个人并不具备资格来判定这段音乐描述的专业准确性,但这段音乐文字令我好似真切听到了新疆音乐的声音,并鲜活地将这种音乐的动态展现在我的耳旁。随后,李皖又以具有充沛感性的语言文字从技术元素的角度对新疆音乐予以界定:
新疆音乐的最主要特征,在于一组热情、激烈、循环往复、不断回旋、不断加强的节奏套子。往往是四四拍,但二、四尤其是四拍的重音被格外地加重,还要加上一堆手鼓、一排拔弦以更碎、更狂的八拍、十六拍甚至奇数拍子予以叠加、炒动、掺和。奇数不要紧,点子乱也不要紧,关键要在紧要处重合,在一句末尾达到循环……在复节奏的弹拨与打击中,新疆歌曲线条优美的旋律,配合着脖子的错动、腰肢的扭动、身体的旋转,添出许多波折出来。歌曲的拖音很少平直,而是拐着弯着扭着花浪着点儿顿着音儿……(18)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的修辞,那是利用文字的最大可能对音乐效果的模拟式传达——但毕竟在生动的音乐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词不达意”的。或许我们可以指责这段文字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错漏,如作者根本没有说明这里指的是什么音乐体裁和品种,因而此处的节拍描述恐怕很难与真正的音乐对上号,此外对于节拍节奏的描述可能也存在一些误导(什么是“八拍、十六拍甚至奇数拍子”?)。但是作者显然希望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音响本身的技术特征,并力图希望说明我们所感到的音乐情感效果背后的技术原因,无论作者是否成功,但他的努力方向却值得认可。
在规定了新疆音乐的性格特征和技术特点之后,作者笔锋一转,深入到了形成这种音乐性格和形式建构背后的文化社会原因,并将新疆音乐的内涵与该地区人民的生存状态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将他对音乐的感受与解读推进到了文化诠释的高度:
那种饥渴往往跟痛苦有关,在爱情里是情欲,在生活里是困苦,在人生里是难舍难破的终局。但新疆人面临着困苦时,从不见低吟苦闷消沉,而是用迷狂的旋舞将之转成狂喜,用火一般的烈焰烧灼人生的苦痛……新疆音乐火烫、激情炙烤的性格,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性格。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种群和人生处境,孕育出游牧民族以欢乐面对苦痛的哲学。由于人生中特别的不安定,前路的不可知,安稳生活的不可求,世代历史的动荡不居,游牧民族培养出笑对无常的豁达。(19)
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被作者热情而锐利的笔锋所感染,我们首先希望听到这样的音乐,同时也希望通过聆听这种音乐而体察其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音乐的声音中直接承载着这样的人生体验和价值尺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此热烈的精神追求和如此豁达的文化生活信念只能通过这样的声音(以及舞姿)才能表达和存在。毋庸置疑,在这里,音乐确乎就是文化,因为音乐与文化从根本上是不能分离的。音乐不仅是文化的下属和亚种,不仅履行和完成具体的社会功用与文化功能,也不仅仅是文化的价值隐喻符号,它有可能凭借自己的魅力和感召直接成为文化的精神化身。
上述三种音乐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解读思路和策略,实际上是某种为了理论阐述方便而人为划定的“范式”,在研究实际中很有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态势。我想再次强调,这三种方法论范式并无好坏高低和落后先进之分,必须根据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和实际情况来作出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法和策略。而且,这三种方法论范式应该形成相互平行与彼此支持,而不是相互替代和彼此对立的局面。最后需要提醒的是,解读音乐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尽管方法论意识极为重要,但决定这种解读的有效性和质量的最终准绳,是解读者自身的音乐功力、文化素养、学术视野,以及放在最后,但绝非次要的文字语言的表述能力。
2011年1月31日初稿
2011年2月14日二稿
2011年2月15日三稿
于沪上“书乐斋”
(注:本文同为上海音乐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注释:
① Bruno Nettl,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 2[n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p. 5.
② 参见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反思与发展构想”(上、下),《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第2期。
③ 参见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陈铭道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
④ Timothy Rice,“Toward the Remodelling of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31) 1986, pp. 469~88.
⑤ 笔者分别于上海音乐学院第六届钢琴大师班和深圳音乐厅作了专题演讲。该讲演稿约7千字后来全文发表于《文汇报》2009年10月24日第6版,题为“海顿二百年祭”。该文也转载于《音乐爱好者》2009年第12期。
⑥ 该协议的全文(Karl Geiringer英译)参见Philip G. Downs, Classical Music: the Era of Haydn, Mozart and Beethoven, W. W. Norton Company, 1992, pp. 212~214.
⑦ 见杨燕迪,“海顿二百年祭”。文中所涉及的“工匠艺人”和“自由艺术家”概念,笔者参考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在其精彩的音乐社会学论著《莫扎特——探求天才的奥秘》(吕爱华中译本,台北连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中的相关阐述。
⑧ 《音乐人类学》(中译本),特别是第十一章,“用途与功能”,第217~236页。
⑨ 我个人认为,梅里亚姆对音乐功能的总结并不见得具有充足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至少,“情感表达的功能”和“沟通的功能”之间就很难清晰划分,而“强化服从社会规范的功能”、“确认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的功能”、“促进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功能”和“促进社会融合的功能”这几个范畴之间更是存在交叉重叠。
⑩ Max Weber, The Ration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Music, Eng. translated by D. Martindale, J. Riedel, G. Neuwirth,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8.
(11) 同上注,Introduction, p. xxii.
(12) 参见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中译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 参见Thoedor W. Adorno, The Philosophy of New Music, Eng. translated. by Robert Hullot-Kentor,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6.中文文献请参见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4) 参见Rose Rosengard Subotnik: Developing Variations: Style and Ideology in Western Music, Uni.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Deconstructive Variations: Music and Reason in Western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5) 参见苏姗·麦克拉瑞,《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张馨涛译,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3年。
(16) 这里显然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其他学理问题,如音乐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音乐研究和文化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又如,音乐分析和批评如何同时公正而完备地处理音乐结构分析和音乐意义诠释的问题(这一问题近来在国内集中体现为有关“音乐学分析”概念和实践的讨论);再如,最近以来有不少学者(包括我自己)开始关心如何运用文字语言来描述和表达音乐体验的问题。我们欢迎相关同道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但为了本文的集中论述起见,在此笔者对上述问题不做进一步展开。
(17) 《读书》2009年第10期,第155~156页。
(18) 同上,第156页。
(19) 同上,第157~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