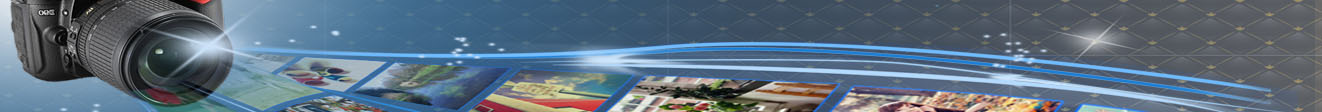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
【作者简介】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历史上曾经作为主流的音乐传统,在当下以非主流的方式得以生存与繁衍。一个时期以来,对于传统音乐究竟能否传承下去的讨论不绝于耳,相当多的学者忧心忡忡。的确,中国的音乐传统能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保存与传承,真是不容乐观。
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和传承条件是两个问题。在当下,特别是在城市文化中,传统受到的冲击更大、更多。相比较而言,在广袤的乡村,传统音乐文化保存依然较好,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城市是文化的交汇点,其中生活的民众来自五湖四海,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因此最容易形成新的艺术形式,也更容易吸收外来文化并引领潮流。当外来的强势文化“入侵”的时候,也几乎无一例外是从城市开始。
可以看到,多种音乐新形式的产生,多是在城市中完成的,特别是在中心城市。正是由于外来强势音乐文化的进入,导致西方专业音乐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以及两者混合而产生的所谓“新音乐文化”三分的状况,并进而影响全国的城市。所以说,西方音乐文化进入中国一个世纪之后的实际状况就是在城市音乐文化中引领潮流,并导致了城市音乐文化格局的变化。
乡村文化能够相对稳定而变化较慢,而且是基本以传统音乐文化占据主导的格局。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有相对稳定的居住人群,族群与血缘关系导致了人文生态环境的超稳定结构。一个村子有一个或几个大的家族所构成的现象绝不少见,许多人家均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的亲戚也都相距不是太远,大多数人的婚姻状况也都是本村、邻村、邻乡,交织成一个网状体系。因此,形成传统后较为容易积淀下来,也具有相当的认同性,除非有巨大的外力或不可抗力,否则很难导致突变。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的力量甚至形成相当程度的排异性。此外,传统一旦以民俗的形式得以固定,这种隐性的制度其力量更是不能低估。也不必有人将这些写在纸上,但就是这些东西却代代相承,想改变也难。
笔者属于经历了中国“文革”的一代,而且曾经有相当长时间的乡村生活经历,那些伴随新娘花轿以及哀声街衢的唢呐声,还保存在儿时的记忆中。“文革”期间在乡间葬礼仪式上唢呐声似乎绝响了。然而,当我以一个音乐文化学者的身份在近十几年间不断深入民间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儿时的记忆在许多民俗仪式中又不断被复制、重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仅仅是红白喜事还就罢了,什么祭祀药王、关帝等各种神庙,“过周年”、“过三年”的礼俗也有恢复。近期我的研究生在山东菏泽采录了一个完整的“过三年”仪式,我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家乡河南焦作,有的家庭在做“过十年”的仪式①。
乡村中与乐相关的礼俗甚多,民间礼俗有着相当程度的丰富性,诸如葬礼、婚礼、祭祖、祈雨、迎神赛社、驱傩、多种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上梁、开光、上元节、放焰口、斋醮科仪等等,但最为重要的是一些与祭祀相关者。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与“礼”相辅相成者,当然是“祀”,自周朝延续下来的传统即是凡大礼必用乐,乐为礼生,礼乐相辅相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世代浸染的乡民们来说,“孝”的观念是至为重要的。当葬礼仪式成为检验某个家庭是“孝”与否的时候,当丧葬礼俗成为乡间各种礼俗中至为重要的时候,当葬礼用乐被乡民们作为礼俗必须遵守的时候,在葬礼中所用的乐曲依附于各个程序诸如吊孝、行奠、烧轿、送路、上林等等被乡民们规定为程式化的时候,传统音乐与这些礼俗一起得以传承。
有意思的是,就葬礼中是否应该用乐的问题,即便是作为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似乎也一直是文人雅士们争论的重要问题,所谓“居丧不言乐”者。
《读礼通考》云:“丧葬所以哀死也。乃江南则惟列酒食为吊慰,厚奠赙以烊观主,殡者鼓吹优人之杂陈,顿忘哭踊之节,执绋者歌童乐妓之具在,毫无共戚之心,彼此同流,甚而浮荡之子弃亲不葬十有余年为弊极矣。”
明律十恶不孝条:“居父母丧作乐,不义条居夫丧作乐,丧制未终释服从吉、忘哀作乐及参预筵宴者、杖八十。”
大清律文与明律同。如果单从以上的言语看,都是讲在居丧期间作乐,未说明在葬礼时是否可以作乐者,而下面的言语则明显是说不能在出殡时作乐的:
黄佐乡礼,凡丧事不得用乐及送殡用鼓吹、杂剧、纸幡、纸鬼等物,违者罪之。
《元史》:诸职官父母亡,匿丧纵宴乐,遇国哀私家设音乐,并罢不叙。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循习元人旧俗,凡有丧葬设燕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筵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取,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弊可胜言,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厚风俗。上乃诏礼官定民丧服之制。②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似乎统治者都不赞成民间的葬礼仪式用乐。诸如居丧用乐不合于礼,村民们在举行丧礼之时过分铺张等等,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文献以及现实社会生活中,葬礼用乐又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究竟哪一种是不“合礼”的呢?所谓“礼不下庶民”,难道丧礼仪式用乐仅仅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吗?是否作者在其心目中有对庶民轻贱的含义呢?如果“礼”仅限于王公贵族,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的成分是要失传了。我们看到,“礼”的观念在历史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诸如隋唐以前的驱傩仪礼是为国家大礼,而宋代以后则成为市井吉礼,可见“礼”也在“文化下移”。民众举行葬礼过于奢华、铺张,的确应该被劝戒,但某些文人雅士的说法实际上显现出对平民百姓的一种轻蔑。虽然统治者不断发布禁止乡民葬礼用乐的政令,但葬礼用乐的情况却从来没有被真正禁绝。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各个省市卷本以及我们实地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葬礼用乐的乐曲占了相当的比重。
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可说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百宝箱”。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来文化的涌入,城市文化的快速变异,当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中的某种“一致性”和“均衡性”被打破,乡村之中传统文化积淀的厚重性得以凸显。并非一说传统文化就是指乡村,而是中国社会形态历史演化的一种当下存在形式。要想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真是要对乡村社会进行认真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传统音乐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脉在当下主要存在于与民间礼俗的相辅相成之中。
中国乡村礼俗能够承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原因,就是历史上在乐籍制度下生存的乐人们,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其用乐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和主导脉络的体系化,他们本身承载着礼乐和俗乐的所有程序和与此相关的乐曲,并引领着各个时期用乐的潮流。在乐籍制度解体后(雍正元年,1723年),他们转向为一般平民百姓服务的时候,会将礼俗和与其相辅相成的乐曲传承下去,并成为各地的约定俗成者。脱籍之初的乐人们,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他们的领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之后,他们中在城市里生活的一群,有些进入了各级艺术团体,有些进入了专业院校,逐渐被另一种文化所影响和规范。而在乡村者,其技艺则在外来文化冲击不甚大以及在乡民文化认同的情况下得到有效传承,虽然其中也会有许多的新变化,但基本上属于体系内传承和发展。我们在对山西、山东等省市的乐户后人们进行调查时这种印象尤为彰显。乐籍制度解体之后,这个乐人群体并非都集中在城市,在制度一致性的定规下,在乡村礼俗生活中他们将音乐本体与其相辅相成,在服务于乡民的时候,把这种上下一致的音乐文化传统沉淀在乡村,在各种礼俗的应用中使传统音乐也得以世代延续。
城市中的音乐文化,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呈现出三分的局面。在乡间,由于宗族血缘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礼俗传承的延续性使得与此相关的音乐文化显现出传统占据主导的局面。乡村社会中的乐人们大多没有受到过现代音乐教育,他们受业多由“行内人”所传,或是集中办学习班,或是班社内以师带徒,律、调、谱、器甚至乐曲都是“体系内传承”,在传统礼俗的作用下、在体系内传承的形式中,传统音乐与传统礼俗共生共存实属必然。
我们一些音乐文化学者,既没有看到礼俗与传统音乐文化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没有到乡间实地考察,只将目光着眼于城市,坐在书斋里去臆断传统音乐文化的消亡,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的城市文化中,音乐似乎成为仅仅供人欣赏和审美的艺术品类,而乡村社会中音乐文化的功能性比城市里要宽泛得多,内涵要深厚得多。多种民间礼俗中的用乐并非仅仅是供欣赏和审美,而是强调与礼相辅相成之存在,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的音乐文化的多功能作用。一位乐户后人对我讲,在葬礼仪式中乡民们并不在意乐队奏了什么曲子,也很少有乡民能够知道乐队奏的是什么曲子,而是在于乐队所奏与葬礼程序的相辅相成。在仪式中所奏曲目只有司仪(俗称茶房、礼相)和音乐班社之间最为默契,这恰恰说明乡村葬礼奏乐更注重其在礼俗中的功能意义。至于款待乡民的奏乐(俗称“玩一玩”),是在葬礼正式仪式之外的事情。当学者们将目光仅仅聚焦于城市,或称以当下城市文化的观念来审视乡村文化、对乡村音乐文化所具有的多功能性“集体无意识”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仅仅盯住“民间乐曲”本身,却看不到这些乐曲和音乐形式所负载的内涵,看不到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音乐一直是作为沟通人与鬼神间的桥梁和纽带功能的存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先民,常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这恰恰说明鬼神观念的存在,否则先民们一直存有并延续在当下民间信仰中的“万物有灵”,以及现在经过浩劫之后依然保存下来的如此众多的佛、道和神庙以及禳灾祈福的迎神赛社又说明了什么呢?“唯物主义”不相信世间有什么鬼神的存在,但作为千百年来人们固有观念下所形成的、已然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当下的取舍是一回事,对于文化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又是一回事,如若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片面而有局限的,换言之,对历史上存在的文化事象视而不见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历史上的人们对于鬼神虔诚地敬奉,在天、地、人之间,在人、鬼、神之间,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先民们在社会底层一直存有的观念,被思想家们进行了升华,并由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种种祭祀活动中,这种观念得以充分地显现。仪式其实是承载这些观念的外化,虽然乡民们说不清多种民俗仪式的初始内涵,却依然不断地重复着,毕竟这是祖先代代相承传下来的。既然能够千百年不变地延续,必然有其存在的道理。
那么,我们的教科书中为什么对这些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呢?我们音乐文化学者就要将历史上所实际存在的、与传统音乐文化息息相关的事象统统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范畴之中,既对音乐本体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又要将与音乐本体相关的文化事象——民俗、仪式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将音乐文化史上“有什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这是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现象重新认知。正如此,方能看到我们这些年来的学术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前提下所存在的局限性。作为研究传统音乐文化的学者,我们的确应该对当下传统音乐文化最为深厚的乡村社会投入更多的关注,将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关系、与传统音乐相关的民间礼俗、当下存活的民间礼俗其历史的脉络及演化关系、礼俗与音乐所具有的种种功能意义、传统音乐文化自身的体系等等,做较为系统的梳理。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从民间礼俗仪式以及音乐在礼俗仪式中的功能作用来考察传统音乐。在考察中间,注重对礼俗仪式的整体进行共时层面的描述,但这种做法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形成这些礼俗仪式的历时层面,因而看不清它们的背后意义。我们强调的是既要对共时层面亦要对历时层面进行考察,对礼俗仪式及其用乐有全面的把握。当然,在考察中间有所侧重是必须的,但这种侧重是要建立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之上的。
民间礼俗是千百年文化积淀所形成,反映出人们的文化观念,其外在的形式变化相对较小,但其内容有相当变异,这是时代的发展使然。但也有一些礼俗,特别是与祭祀相关的礼俗,变异的成分相对较小,这可以从其仪式程序中得到反映。仪式的内容是否有变化是要加以分析的。就我们在鲁西南调查的情况来看,一些仪式中使用的乐曲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诸如《开门》、《小二番》、《哭皇天》、《朝天子》、《将军令》、《水龙吟》、《十样锦》等等,然而也的确有一些乐曲是不一致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单就乐曲依然是传统这一点来说,不排除乐人们在传承过程中的主动选择,即为了适应当地人的需求将传统音乐中的某些乐曲传承,而忽略了或称淡忘了另外一些乐曲的存在,久而久之形成了各地在用乐过程中既有一致性又有相异性的局面。但如果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却发现各地使用传统乐曲的总和依然可以构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导脉络相对完整的体系。这可以从目前已经出版和正在编辑出版的各个省市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得以显现。
乡村音乐班社在葬礼中常常演奏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戏曲唱段,因而有人觉得乡村礼俗也不“传统”了,笔者近年来就这个问题有相对深入地考察,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从一个音乐班社受雇于丧家奏乐开始,便可以认为是进入了丧仪的整个程序。在葬仪的主程序中,一般不会有流行音乐的切入,流行音乐是在正式的葬仪之外,在款待乡民时才会演奏,虽然这是葬礼一个不可或缺的程序,却不是在正式仪式之中。正式丧仪的每一个程序是必须演奏传统曲牌的。乐人们通过当下的传媒所获流行音乐,而并非刻意学习,这反映出乡村音乐班社能够跟上时代的一面。民间班社的老艺人讲,以前葬礼各个程序中所奏的曲目比现在要丰富得多,有些传统曲目已经失传,能够保留下来的也不过是原先的几分之一。的确,这就是传统的变化,但这依然属于体系内的变化,可以视为内容的简化,但程序还是不会少的。
以上我们所讲的是奏乐收钱以此为生的音乐班社的情况。在河北、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还有以“会社”形式存在的奏乐群体。这个群体一般说都有某种宗教、民间信仰或者祭祀意味的背景,诸如专为迎神赛会、祭祀药王、祈雨、民间葬礼奏乐而存在。这类作为民俗活动主体的乐社虽然其中不乏技艺高超者,却都有着各自的营生而非专业乐人。他们演奏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传统乐曲,绝不演奏流行音乐。正是这些世代传承的民间礼俗、民间信仰支持着乐社的生存,也使得乐社所演奏的乐曲依附着民间礼俗而得到有效的传承。
乡村社会的礼俗也在变异之中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就人类学的视角说来,无论是“变迁说”还是“跃迁说”都是讲“变”。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要像美国那样,由较少的农业人口以规模产业化生产养活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使大多数农村人口脱离其生存的土地而城市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只要是乡村社会依然有相对稳定的家族聚居环境,那么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礼俗就不可能很快消失,这与城市文化中快速变异的情况形成较大的反差。还有,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与乡村一致的民俗文化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前些日子的一个夜晚,在我居住的社区内,楼下传来唢呐、笙及锣鼓的演奏,跟着一队抬花圈的人流,这是小区内一户人家在办葬礼。在距北京市北四环(城市中心地带)仅有十公里的地方,传统班社就有活动的空间。我的学生讲,他所居住的小区(五环以外)每逢初一、十五总会听到有唢呐乐队在小区边上的奏乐声。
传统音乐与礼俗共生存,这在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种现象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以为,在中国乡村以家族为主的社会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中国,这种传统礼俗中广泛用乐,礼俗、乐俗共生的现象是短期内很难变化的,只要这种相对稳定的乡间社会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礼俗与乐的共生现象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要大变,那也是乡间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的事情。
当下的中国乡村,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涌向城市,并创建出大量的新城镇。这些曾经的农村人口在生活方式改变之后,开始逐渐融入到城市文化中来,他们的后代显然也不会认同以往的礼俗,而礼俗的延续却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没有这种相对稳定性,也就意味着功能性改变。在贵州山区,由于大量的劳动力涌向珠江三角洲,侗族大歌的传承链条开始出现了断裂,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空间的改变导致传统礼俗变异或消失是毋庸置疑的。当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势头迅猛,但多数人只是孤身外出,父母、妻儿在家,他们的“根”依然在乡村,当下乡村社会血缘关系的家族稳定局面还没有被打破,传统的文化心理依旧。虽然这些进城务工者会将他们在城里的所见所闻带回到乡间,但正如我们在许多乡村所见到的那样,许多受到过高等教育、已经在当地各级政府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经常会乘着富康、桑塔那等回乡奔丧,在祖宗的神位前、在撕心裂肺的唢呐音乐声中虔敬地叩首,当下乡村社会礼俗的生存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值得深思的是,当下诸如贵州等一些相对贫困或者剩余劳动力多的地方,外出打工者成群结队,致使一些民俗的传承后继乏人。而像山东等相对发达地区的乡民们反而坚守故土,传统民俗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失传。所以说,只要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人群占据全国人群的比例不会一下子减少到一个相对小的水平,那么礼俗就会与这一群体共生共存。
所有的礼俗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在这些礼俗之中,民间信仰、宗教、祭祀等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认识的,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认识这一点,如果我们仅仅按照当下城里人的观念,认为音乐就是在音乐厅里的“艺术”,则很多问题难以解释。民间信仰支撑着如此众多的礼俗,礼俗是民间信仰的载体,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的主导部分,恰恰是依赖于这种载体而生存。每个县里数以千百计民间乐人群体的存在更是至关重要,没有这个群体传统音乐文化将得不到很好的承继。如果不是有如此众多的民间礼俗的存在,融会于其中的传统音乐将迷失自我。民间信仰、礼俗、音乐传统形成了相互依存、共生关系的链条。
所谓活在当下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并传承下来的音乐文化。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农耕文化时代印记。就其音乐形态和类型来说,学者们有多种分类,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这种分类有时界限也不是那么严格,会有交叉的现象。我们所讲主要是指民族器乐,这种音乐形式在当下的音乐传统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更强、更广。民歌和说唱,更多侧重于娱人的层面(按:只是说侧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某些歌舞和戏曲的表演,无论是其自身的内容还是其服务对象,均与民间信仰和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歌舞就是在民间礼俗中专用,有些戏曲则在迎神赛社、开光、唱老爷戏时所用。如果从社会功能性的层面来说,与民间信仰、祭祀礼俗最为密切的还是以器乐为要。这也就是我们以器乐为例的道理了。
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音乐主要是一种欣赏与审美的艺术。一位大学教授看到我们在乡村中拍摄到的民间音乐班社对着一座坟丘和灵牌吹奏《百鸟朝凤》和《一枝花》等乐曲的时候,他的表情近乎惊讶:真没有想到这么美妙的乐曲会在这样的场合、面对这样的对象演奏!然而,这是每天都在乡村社会中发生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举出贵州的乡民们对着祖茔吹芦笙;河北安新的某音乐会社大年三十到烈士祠为烈士奏乐;雄县赵岗村正月十四至十六花灯会,传统音乐连续三日分别为人、为神、为鬼演奏;山西民间迎神赛社乐户们在神庙中专为敬神表演戏曲;雍和宫中祭祀所用的乐舞等等,这些的确不仅仅是为人欣赏和审美所用。也许有人会讲,只有“学者们”才会去探讨这其中的“意义”,但这就是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
我们绝非是要让中国乡间社会的传统音乐文化处于一种凝滞的状态,也不是说中国乡间的礼俗就不会变化。相反,中国当下的乡村社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如果你能够深入乡村,就会看到传统的延续与变化并存,但这种变化并非是突变型的,这还是因为传统的厚重,民间礼俗依然在影响着乡民的生活。尊重传统,使其自由健康地发展,中国传统礼俗的生存土壤、生存空间不被人为地破坏,传统就一定能够延续。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传统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性,对民众实施民族性、民族文化及非物质遗产保护意识的教育,那么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传统的根脉也一定会得以传承。传统音乐在乡村与民间礼俗共生,这并非说乡村社会中的音乐传统就不用发展,也不是说乡村的音乐文化传统拒绝外来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音乐是一种所谓的“时间艺术形式”,在一定的时空过程之中存在,要有活的载体才能够得以传承,人的群体传承才能够使音乐传统最具生命力,所谓“死音活曲”就是这个道理。发展要有新的创造,但这种发展显然是在传承的基础之上的。
音乐传统依附于民间礼俗而延续,保护民间礼俗,也就是真正意义上保护我们的音乐传统。保护传统与当下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并不矛盾,作为城市文化,人们已然习惯了将音乐仅仅作为欣赏和审美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将脱离了礼俗、脱离了仪式的传统音乐精雕细刻搬上舞台,但其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却是要保护的。作为“礼俗”者,是传统文化的积淀,虽然其形成与生产、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却是属于观念的层面,形成之后可以独立存在,不再完全受生产方式的制约。既然礼俗可以不因社会发展而消失,只要这种功能性的存在,我们的音乐文化传统也一定能够传承发展,要认知传统音乐文化,应该走到乡村社会中去,民间礼俗就是其生存、发展、延续的载体,我们说传统音乐文化与民间礼俗文化相互依附共生、共存就是这个道理。
本文曾为2005年6月韩国首尔(汉城)“亚洲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注释:
①所谓“过周年”、“过三年”、“过十年”,是指家中长辈去世之后,在一年、三年、十年的时候由晚辈举行祭奠仪式的礼俗。
②钦定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仪礼之属·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一百十五“违礼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