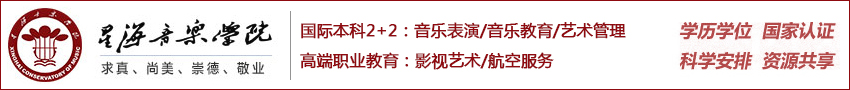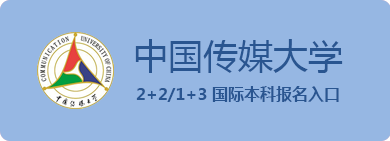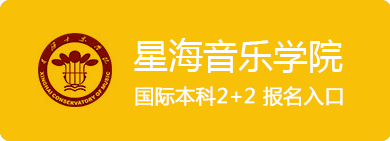播音主持自备稿件:《梦如花开》
忽而,就是冬了。
风,显见得凛冽了。太阳,温情而魅力。天,或晴朗的惹人怜爱,或阴霾的像在人的头顶扣了个锅盖。树,挥剑斩断了与叶最后的缠绵,枝杈骄傲的指向天空,倔强的可爱。整个春天和夏天乃至秋天都在窗外啁啾着梳理羽毛的鸟儿,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北方的冬天,内敛到慵懒甚至颓废。
我猜想最出色的画家也没法描摹出时间确切的形状来。然而,春来了春花开了,冬来了雪花飘了,还有那棵曾经陪我们玩耍的小树长高变粗了,而当初几只土坷垃就可以轰轰烈烈打一仗的我们也做爸爸妈妈了,我们的孩子也开始依依呀呀的唱着青春的歌了。这样的变化,让你清清楚楚感觉到时间就藏在春花的花蕊里,时间还涌动在封冻的泥土里,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而你,只能被它挟持着一路向前。
时间匆匆地流,梦一寸一寸地醒,失落有时候会像打翻了的调色盘,晕染出些错综晦暗的色彩来。每逢这样的时刻,就拉开记忆的抽屉,从过往的岁月里翻找些微笑回来——旧照片中我青春的眉眼,母亲生前用过的丝帕、父亲留下的烟嘴,那年那月他写给我的青春稚嫩的情诗,儿子出生时穿的小衣裤,看一眼,摸一把,日子便从容温润起来。
偶尔家里只有自己的时候,我会穿上藏了许久的红舞鞋,在合心的旋律里“鲜衣怒马”一回;也会换上各式旗袍,走走猫步,在镜子前“妖娆”一次。
这个时候,心尖都是软的,矫情也好,做作也罢,只快乐给自己看。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就是舞台上的名伶,水袖、猫步,婀娜了身姿,委婉了唱腔,鲜活了笑颜,而岁月,是衬托我的红红的幕布呵,是渲染我的迷离的灯光。
都说人生如戏,生活中我一直都是台下看戏的人,我心甘情愿的为我的亲人、朋友的精彩演出而快乐的鼓掌。此时,我给自己做一次演员,准备为自己的精彩鼓掌,怎会不倾情演出呢?听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想梦有多长,戏也该有多长吧。
突然想,今生,以梦为马吧,爱着,憧憬着,信马由缰着,挥鞭疾驰着。
恍惚觉得,心中有一朵花,带着风声似的“噗”地就绽开了一瓣,又绽开了一瓣。那花儿,怕是我悠长悠长的梦吧。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