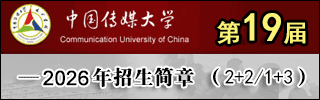我出生时,由于父母闹离婚,我被送到了乡下,让一个长得像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哑巴女人当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哑娘。
在我去哑娘家之前,哑娘出生三个月的孩子夭折了,于是,我成了哑娘和她的丈夫驼背叔的精神寄托。他们把我当成亲生儿子,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了我。驼背叔会吹唢呐。那时,每逢村里有红白喜事,驼背叔都会被请过去。只要驼背叔的唢呐一响,周围的喧嚣立刻停止了。男人们忘记了抽旱烟,女人们忘记了纳鞋底,孩子们不哭不闹了,纷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驼背叔的手指轻轻抖动着,或悠扬,或哀婉,或激昂的曲子便从手指间汩汩流淌出来。《百凤朝阳》鸟语花香,《风搅雪》气势磅礴,《十面埋伏》扣人心弦,《哭墓》让人断肠……
每次吹完,红白喜事的主人除了给驼背叔一点钱外,还会送上在当时极为珍贵的肉夹馍——雪白的馒头,油汪汪的肉,看了就让人流口水。驼背叔舍不得吃,把肉夹馍揣在怀里,还给我。看着我香甜地吃完,驼背叔和哑娘总会笑得很开心。
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哑娘把土炕烧得暖暖的,我依偎在哑娘的怀里,边看着哑娘纳鞋底,边听着驼背叔吹唢呐。驼背叔的唢呐总能把我的心带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
在我四岁那年,驼背叔忽然得了一种怪病,死了。我清晰地记得,驼背叔临终前,眼解挂着一滴泪。那滴泪在秋阳下抖动着,闪烁着,年幼的我示能从那滴泪里读出什么,直到现在才明白,那滴泪里满含了牵挂和不舍。
驼背叔走后,村里人都劝哑娘把我送回去,趁年轻改嫁个好人家。哑娘紧紧地抱着我,拼命地摇头,时不时地用满是惊恐的眼睛向四周望一望,仿佛怕别人把我从她的怀里抢走。
没有驼背叔的日子里,我和哑娘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难。哑娘惟一能挣钱的活计是做豆花。每天深夜,在昏暗的灯光下,哑娘推着沉重的石磨,一圈圈地转着,看着洁白的豆浆汩汩流出,磨完后,哑娘不顾得抹去沁满额头的汗珠,又把豆浆装入大瓦缸,端上锅,生起火,这时,她才能稍稍喘口气。
天不亮,哑娘便领着我出门了。哑娘不能叫卖,只好拿起驼背叔留下的那把唢呐,用唢呐代嘴叫卖。由于底气不足,哑娘总把唢呐吹得很刺耳,那刺耳的唢呐声伴随了我整个童年。沉睡中的人们听到唢呐声,就披着衣服,惺忪着朦胧睡眼,把一张张毛票递给哑娘,换取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豆花。
村里的孩子看见哑娘,总跟在她后面起劲地喊:“哑巴婆,吹唢呐,嘴巴鼓得像蛤蟆……”哑娘没有听力,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不时地回过头冲他们笑一笑。
我渐渐懂事后,哑娘成了我的耻辱。每次和同学们在一起玩时,总有人用手做出吹唢呐的样子,发出怪叫。这时,其他人就哄堂大笑。我拼命捏紧了拳头,脸涨得通红,不知该转向哪里。
我回到家,大声向她喊:“你为什么是个哑巴?为什么!你送我回我自己的家,我再也不要呆在这儿了!”
哑娘听不见我在说什么,但她似乎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了什么,默默地站在一边。泪,像从伤口流出的鲜血,无声地顺着哑娘的脸颊静静地流淌着……
以后的日子里,我很少搭理哑娘。我把同学们对我的嘲弄全化成了对哑娘的仇恨。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考上初中,去县城读书。那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有一个哑娘了。
终于,小学毕业了,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我住进了学校,一个多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哑娘都会打量我许久。当她伸出手,想摸摸我的头时,我会把冰冷的目光投向她。哑娘伸出的手就怯怯地缩回了,她的脸上有孩子般的不知所措和难过。
初二那年冬天,我感冒了,周末没有回家。星期天早上,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唢呐声。是哑娘的唢呐声!我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难道是哑娘来了吗?
许久,我走出宿舍。屋外,飘着大朵大朵冰冷的雪花……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