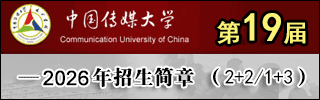在南京,在大屠杀纪念馆,一个巨大的头颅,一张巨大的嘴,在呐喊。呐喊声,在无涯的时间和空间凝固了。一个被日本人活埋的中国人,一个人,喊出了一个民族的痛。被埋在泥土下的躯体在反抗,在挣扎,在竭尽全力爆发。血气上涌,眼眶通红,生命在呐喊中,变得轻盈、飘逸,远离灵魂。
在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埋进泥土,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活埋的时候,会想些什么?
那些木然的,甚至欣喜若狂的挥舞铁锹,用泥土涂抹这幅图的所谓的“人”,他们,挥动着恶之臂膀的他们,还能被称为人?
我无法透过一副骨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老的,少的,漂亮的,英俊的,只是看到了骨骼,完整的,白花花的,亮得刺眼的骨骼,人的骨骼。一副,两副,许多副,他们排着队,整齐的,凌乱的,在我的眼前闪耀。
一个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人告诉我,日本兵让俘虏自己挖一个坑,然后,面朝土坑跪下。“砰”的一声枪响,人,一个倒栽葱,进了土坑,正好把土坑填满。然后,请下一个,用铁锹,用泥土,把坑抹平,让一个生命的痕迹,从此,在这块土地上,彻底消散。
1937年12月13号之后,一百多个,甚至更多个日子里,旧都南京的大街上,走动着来自另一国度的人,这些人嚣张、霸道,腰间挂着钢刀和头颅。这些在腰间晃动的头颅,大张着嘴,呼吸着人世间最后一口空气。惊愕摆在脸上,无论多么用力的呼吸,都无法摆脱死亡的缠绕。呐喊,无声。哭泣,无泪。几个,有时是十几个,几十个,悬挂在一个腰间的头颅,有着一色的表情:剧痛后的麻木,面具一样。
在南京,在活埋者的头颅前,在万人坑的骨架前,我常常感觉到做为一个弱者的无助。我常常替他们挣扎着,呐喊着,逃跑着,可如果把我,放到这样一段日子里,除了挣扎、呐喊、逃跑,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的想象力,如此贫乏。有一个人,或许,是一个作家,为我复原了一幅图:泥屑从头顶纷纷飘落的时候,一位母亲,把自己弯成一个弓,用身体,为婴儿,挡住了这个世界强加给他的噩运。
从被活埋的数十万骨架中,突然看到这样一幅图,惊悚之中,一股暖意上升。透过这根月牙一样残缺的脊梁,我分明看到了人性的圆满。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