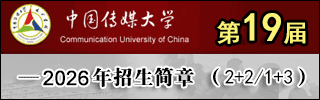男:沿太行山西路一直向上,有一个名叫秀色的村子。秀色山高路陡,树木也欠繁茂,只有几十户人家,可秀色有名。
女:秀色的有名,不在于它的山高路陡,不在于它的村民稀少,也不在于它这别致的称谓,秀色的出名,在于它缺水。
男:吃水,要走一百里的山路下山去背,背回来的水是要上锁的。在秀色,值得上锁的东西只有水。三几寸长的铁钥匙,挂在一家之主的腰间,显示着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在秀色的神圣不可侵犯。
女:方圆百里的村寨,那些当娘的,吓唬闺女时就说,小丫头再不听话,长大把你嫁到秀色去。
男:众人哄笑起来。秀色的村长张宝便说,论风水呀,别处还比不了我们秀色。
女:风水风水,得有风有水。你秀色呀,还缺着风水里的一大项呢。
男:除了没水,我们什么没有啊?
女:哟,这连 水都没有,它还能有什么呀?
男:一句话,噎得张宝羞愧难当,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那么该找水脉吧,该打井吧,该上县里、上省里请打井队吧。从前那些年,这些事都办过。本县的打井队一听秀色就犯怵,来都不肯来;外县的打井队好不容易请来了,但只二十天,他们便熬不住了。村里人使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能留住他们。
女:十多年过去了,秀色依然没有水,而那句“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的咒语,依然压在秀色人的心头。
男:村长张宝又去了县水利局,新来的局长人称李技术的,专注的听了他的讲述,决定亲自去那里看看。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勘察,他料定秀色有出水的希望。于是带齐人马,上秀色打井。
女:二十多天过去了,井是越打越深,人是越来越瘦啊,可还是不见有水。村里的气氛,渐渐慌乱了起来,莫非,这莫非是又到了从前经历的那关口?再不见水,这群人又该走了呀。
男:打井队的人都住在村民们家里,李技术住在张宝家。张宝家有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叫张品,是秀色姑娘里出众的人物。她知道,再不见水,她的青春就灭了。她知道青春是什么,更知道青春在秀色的位置是次于水的。
女:这天晚上,张品望着正屋里上了锁的水厨,对娘说,叫我砸了它吧。娘问她干嘛。张品低了头说,洗洗。娘明白了,却不上手。张品亲自砸了铁锁,将水挥霍一空。
男:李技术从井上回来,进了屋,一下子见到张品,忙背过脸去说,你,你的衣裳呢?快穿起衣裳。
女:今天晚上,我没有衣裳。
男:别胡来啊,没有衣裳也要穿起衣裳。
女:胡来?我这是胡来?
男:不是胡来你为什么这样?
女:为给你看看。我使尽全家半个月的水,就为这,你还敢说胡来?
男:快走,快走。好,你不走,你不走我走。
女:你往哪去?
男:往山下走,下山,回家。
女:回家?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吧,我早就看出来了。白搭,就是把全村人的心都挖出来,也换不来你们给打一口井。白搭呀,该给的都给了,没给的,就剩我们这些闺女了呀。
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
女:张品一下子扑进李技术怀里,双手紧紧箍住他的腰。
男:放手啊你。你怎么这样,这样没有廉耻。
女: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指望谁有廉耻?
男:这一夜,他们不再有话,就这样僵持着。天亮了,李技术揉揉通红的眼往外走。
女:你去哪?
男:打井。
女:第二天,李技术从张宝家搬了出去。打井队在井边搭了帐篷,吃住都在帐篷里。他们疯了似的打井,头发不剃、胡子不刮,身上酸臭扑鼻,山鬼似的。
男:冲击钻,狠狠的刺向井深处。每刺一下,李技术在心里说,这一下,是为张品;这一下,是为张品;这一下,是为张品的;这一下,还是为张品的。
女:九九八十一天,打井队没人下山回家。九九八十一天呐,九九八十一天,他们终于把井打出了水。
男:村民们先是对这井中的泉水又惊又怕,生怕这不过是土炕上的一场大梦。
女:然后,然后他们才放开肚量畅饮,他们让这久违了的干凉的水给醉得东倒西歪呀。
男:那是个初夏的艳阳天,那时秀色人最得意忘形的日子。
女:这时候,李技术弄明白了一件事。在那个羞耻的晚上,羞耻的本不是张品,羞耻的该是他本人呐。
男:共产党的打井队,若是给老百姓打不成井,那么最后渴死的不是自己,又是谁呢?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