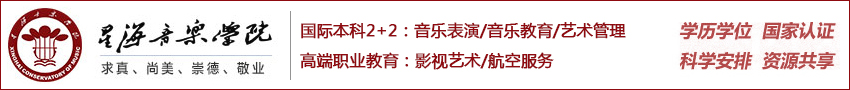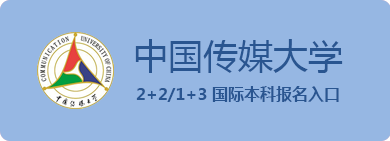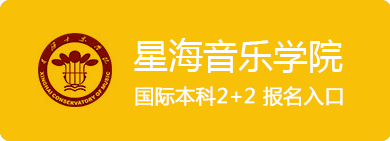播音主持自备稿件:《远方的夜》
黄昏是打开夜的一道门。那道门在旷野中伫立,蝙蝠在它的额前忽东忽西毫无规则地。
飞翔。无言的黑影,让黄昏变得神秘和亲近。随后,黄昏就慢慢阖上眼睑,成长为黑夜,单纯和透明。
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人们吃罢晚饭,就搬张凳子聚在村口,用芭蕉扇拍着蚊子。拉拉家常。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只有开口说话,人们才能分清对方是谁。庄稼地从村头往远处延伸,玉米稞子遮住道路。向东走过一段土路是个缓坡,爬上去能看见远远的灯火。孩子以为是星光,大人说那是矿上的灯光。除了这些,再没什么可看。这几盏灯火,成了孩子想象的出口。
透明的黑暗在我面前伸展,像一大滴露水,富于弹性和张力,把梦包裹和融化。那黑暗清新,散溢着泥土的芬芳,干净得没一点渣子。三两个萤火虫在远处飞舞,大人说拍拍手。它就能冲你飞来。我们就拍着手,嘴里一通乱喊,果然看见一只萤火虫越飞越近,最后绕过树木,飞进我家的院墙。我们跑进院门,见那只萤火虫飞得有一人高了,就一把打在地上,然后拾起来倒捏着头,露出它发光的腹部,在黑暗中抡起胳膊,萤火就滑出一圈一圈的光。我晃着它跑出院子,用它来吸引更多的萤火虫。后来,我看见更多的萤火,它们照亮了一条道路。
我对夜寄予幻想。
那时我已长大,自己住三间老屋。夜像家乡的老屋,老屋的气息宁静安祥。屋后面是小路和庄稼地。后墙上开两个小窗,像老屋的两个耳朵。我能从这两个耳朵清晰听见庄稼叶子的磨擦,或过路人偶尔走过时的脚步与对话。几只壁虎在窗外趴着,伺机捕获被灯光吸引的昆虫。如果有雨,就能听到庄稼叶子更动听的演奏,那声音据说曾被音乐家写入乡村音乐经典。院子里有棵梨树,风雨大的时候令人担心,半夜里能听见梨子落地的声音,或砸碎在磨盘上的声音。它们使夜显得富有。
但是我越来越失去黑夜。生活的碎片被灯光照耀,反射出彩虹,辨不清面孔
那是午夜或凌晨,铁链锁着大门,我没带钥匙,只好翻门而入。大门被弄得哗哗作响,整条街都能听到。有一双眼睛从窗户后面看见我,认出我,但并不说话。大楼上一个窗口睁开,有人彻夜不眠,等早晨来人接班。一排路灯在我面前伸展,是一些声控灯,不管我走路多轻,只要走到跟前,它就打开,为我照亮道路,同时还照亮我的脸,我的表情,以及地上的影子。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