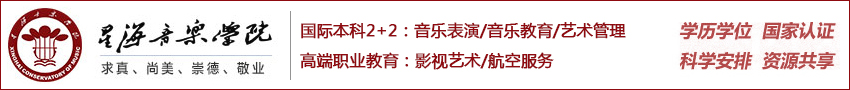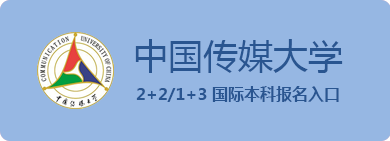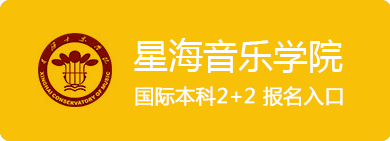播音主持自备稿件:《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
在故乡的清晨,我望见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与故乡的麦地融为一个点。我叫不出他的名姓,连带着辨不出是哪块麦地最终收容了他。只慢慢知晓,在无数个稀松平常的日间,老去的乡人们,扛锄提镰,一个个走向了自家的麦地。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在村子里走了一辈子。黄牛跟过,犁车跟过,余晖跟过,霜雪跟过,拧巴的日子跟过。末了,一身佝偻跟着,霜鬓跟着,皱巴的皮包骨头跟着。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被无米的炊叫住,被灌风的窗牖叫住,被饥饿的驴叫住,被绕膝的子女叫住,被贫苦饥寒的家叫住。但是他不能停下,黑魆魆的麦田,需他去翻种着仅够过活的春华秋实。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在贫苦的这一头耕种,在过活的这一头耕种,在生存的这一头耕种,身子骨瘦削了起来,粮囤鼓了起来,撅起另一头的家。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早已遗忘他的父亲将锄头架在他瘦弱肩头时的模样,也早已遗忘,第一株早夏的麦子躺在他提镰收割下的模样。无人让他记着,他也无需记着,年岁里,他会长成他父亲的模样,来年他自己耕种的麦子也会长成父亲耕种时的模样。
一棵麦子衍生出一片麦田,一个乡人衍生出一个村庄。两者磨合着相互成全,这是麦田养活着的村庄,也是村庄耕养着的麦田。而没有谁比麦穗更了解乡人,它知晓乡人手掌的纹路,五指的粗细,脚掌的厚度,甚至于,它透悉乡人脊背上的汗腺,瞳孔里的血丝。它不置一言,顺从地生长,倒下,再生长,再倒下。直至这个乡人耗干了气力,宛若游丝的睡去。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常常忘了自己的名姓,却分明记得自家麦地的一分一厘。田埂偏了几分,邻地欺了几厘,也锱铢必较,争让回来。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在年复一年的耕种中,养活一群群麻雀,蝗虫,蚂蚱,蝼蚁…养活整个村子的面貌肌理,却时常在遭遇荒灾时,养不活自家的几口人。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任岁月如何松动他的肩头,扳开他的手掌,都卸不下他的这身行头。只有他自己的一口气,争上来,就又是一天,争不动了,便气散灯灭,永远的撇下这些过命的物什。而躺下去,便再也无人能把他叫住,任它衣锦加身,子辈恸哭,他只想静默地躺在自己耕种的麦田里,守着耕了一辈子的麦穗。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在麦田里耕尽了一辈子,在磨盘里磨尽了一辈子,在打谷场上碾尽了一辈子。无人知会他生命另外的意义,也无人知会他麦地外的模样,一个人,耕大一个家,任子女后辈一个个的去乡高飞,便是他几乎全部的生命意义。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是村口的春生爹,是村西的大柱爷,是我的祖父,是祖父辈的他、她、他们,是最后一批与土地血脉相亲的农人。
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两个扛锄提镰的乡人,三个扛锄提镰的乡人…数以万计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在自家的阡陌上,耕出一个伟大意义上的农耕文明,而这文明却在工业化进程中将他们一个个抛下。
当大机器轰隆隆的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扛锄提镰的乡人,土地与我们的血脉或许也必将化浓于水。只是在未赶上之前,我望着祖父和整个村子,只觉他们的背影渐而高大起来,由点汇聚成这个庞大的世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
扫码关注,实时发布,艺考路上与您一起同行